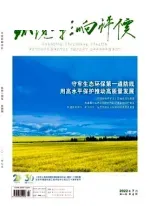湘南東湘橋錳礦廢棄地植物資源調查與重金屬富集植物篩選
高陳璽,李 川,彭 娟,蘇 迪
(重慶工商大學 環境與生物工程學院,重慶 400067)
在現代工業中,錳及其化合物應用于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截至2007年底,我國錳礦查明資源儲量79 293.5萬t,其中基礎儲量22 443.7萬t,資源量為56 849.8萬t。查明的資源儲量主要集中在廣西、湖南、云南、貴州、遼寧和重慶,六省(區、市)合計資源儲量為69 485.8萬t,占全國錳礦查明資源儲量總量的87.6%[1]。雖然錳礦資源豐富,但湘南地區在錳礦廢棄地生態恢復及其研究方面仍然欠缺。礦業廢棄地是指因采礦活動所破壞和占用的、未經一定治理而無法使用的土地,包括排土場、尾礦壩、廢石堆、采空區和塌陷區等[2]。礦山廢棄地土壤結構性差,極端p H值,重金屬含量較高,有機質含量及植物必需的養分元素缺乏,很不利于植物生長和其他生物活動,生態環境恢復十分困難[3-5]。但某些特殊的金屬型植物(metallophytes)由于自然選擇的作用,往往能在重金屬污染嚴重的土壤中良好地生長[6],且這些植物在重金屬污染土壤上能富集重金屬,用于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治理。因此,研究采礦廢棄地上的植物并篩選后加以有效利用,可以彌補超積累植物缺乏的不足,為植物修復技術的普遍應用提供必要物質保證[7]。通過調查了湘南東湘橋錳礦區廢棄地上自然生長和人工種植的植物,并對主要優勢植物及所在土壤進行采樣、分析和探討,以期為湘南金屬礦山廢棄地的生態恢復和植被重建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地區與研究方法
1.1 自然概況
以東湘橋錳礦區為研究對象。東湘橋錳礦位于距離湖南省零陵區約39 km的珠山鎮。地理位置為北緯26°03′54.16″,東經111°21′56.12″,屬中亞熱帶大陸性季風濕潤氣候區,氣溫較高,嚴寒期短,夏熱期長,春溫多變,寒潮頻繁;春季多雨,夏秋多旱;光照充足,無霜期長,四季分明。大部分地區年平均氣溫17.6~18.5℃,無霜期286~311 d,日最低氣溫0℃以下的只有8~15 d,多年平均降雪日數4~11 d,極端最低氣溫在-4.9~8.4℃。日平均氣溫≥10℃的積溫達6 450~6 800℃;多年平均日照時數1 384~1 688 h,太陽總輻射量101.5~113千卡/cm2;多年平均降水量1 280~1 530 mm。珠山鎮屬零祁盆地的一部分,地勢低平開闊。原始植被以亞熱帶常綠、落葉闊葉混交林為主,具有植物豐富,蓋度高的特點。
1.2 研究方法
分別于2011年9月、2011年10月和2011年11月對東湘橋錳礦區進行了植被的實地調查和采樣。選取樣地的范圍基本覆蓋了整個礦區的不同類型,包含了礦渣堆積區、尾礦區、恢復區等區域。首先,記錄大小樣地生長的植物種,包括自然生長與人工種植的植物,并對其豐富度進行了統計。采集礦區每個區域的主要優勢植物,包括自然定居和人工大面積種植的植物。為提高樣品的代表性,在采集植物的根、莖葉時均采自較大范圍內多株植物,并采集一定的幼嫩部分和成熟部分,組成混合樣,采集量1~2 kg,且在對應的取樣植物根部周圍進行土壤取樣,以獲取土壤Mn背景值,取樣深度為0~20 cm。將采回的植物樣品用自來水將表面的泥土沖洗掉,再用去離子水清洗3次;晾干后用切碎,裝在信封中,在80~90℃殺青30 min后,在60℃的烘箱中烘至恒重(大約3 d),測其水分含量。將烘干樣品粉碎,過100目尼龍篩,裝在聚乙烯塑料袋中,儲于干燥器內以備測定。準確稱量通過100目篩烘干至恒重的植物樣品1.000 0~5.000 0 g植物樣品采用濕法消解法(濃HNO3+和H2O2)消解,冷卻后取出消化液,過濾、加去離子水定容到10mL。土壤樣品采用HNO3-HF-HClO;消解,定容并搖勻作為待測液。消解后的樣品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A-7020型)測定Cu、Cr、Cd、Pb、Zn、Mn的含量。
1.3 數據處理
數據分析用SPSS11.5和Excel2003完成。
2 結果與分析
2.1 植物資源調查
調查的所有樣地共記錄到植物32科52屬54種,詳見表1。為典型的亞熱帶植物類群,以菊科、禾本科、薔薇科居多,菊科7種,占所列物種的12.96%,禾本科和薔薇科均為5種,各占9.26%。54種植物中,自然定居46種,占85.19%,人工種植8種,占14.81%。自然定居物種分布范圍較廣,在未開采區、開采區、尾礦壩、恢復區和礦渣堆均有分布,大多為經濟價值低的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人工種植物種主要分布在恢復區,以果樹和蔬菜作物為主。山茶科的翅柃,菊科的蒼耳,桃金娘科的大葉桉,商路科的商路,禾本科的狗牙根和芒草,薔薇科的金櫻子和粗葉懸鉤子,漆樹科的鹽膚木,大戟科的算盤子和白背葉,百合科的菝葜,莎草科的莎草,在廢棄時間1~3年的錳礦區廢棄地比較常見。大風子科的柞樹,竹科的翠竹,茶科的茶子樹,薯蕷科的薯蕷,柿樹科的柿在廢棄時間3~5年的錳礦區廢棄地比較常見。其它所列植物在恢復期5年以上的錳礦廢棄地比較常見。蘿卜、胡蘿卜、甘薯、豇豆、茄子、辣椒為附近居民的人工種植蔬菜,種植土壤為礦區高錳含量的土壤。礦區植物中草本為30種,占總植物種的55.56%,喬木與灌木為占24種,占總物種數的44.44%。物種以優勢種與常見種居多,少部分為偶見種。從調查中發現錳礦區經過多年的開采,原有的常綠闊葉林徹底被破壞,現正處于向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演替的草灌叢初級階段。

表1 錳礦廢棄地上的主要植物種類
2.2 植物對重金屬的富集能力測試
選取礦區廢棄地恢復區主要優勢植物18種(自然生長16種,人工種植2種),測定其各自所在土壤中的重金屬含量(詳見表2)和植物中的重金屬元素質量比(詳見表3)。依據實驗所得植物地上(莖葉)與地下部位(根)及土壤Mn含量,得出植物富集與運轉Mn能力的大小(表3)。總體而言,植物體內Mn質量比最高,趨勢為ω(Mn)>ω(Zn)>ω(Pd)>ω(Cu)>ω(Cr)>ω(Cd)(ω表示該種金屬的質量比,mg/kg)。從ω(Mn)來看,較高的有蓼草、商陸、白背葉、懸鉤子、翅柃、柞樹、算盤子、陰香、薯蕷,而且地上部分的值大于地下部分,均表現為葉> 莖>根,說明這些植物長期生長在含Mn比較高的土壤環境中,其本身可能具有或已經對Mn形成耐性,并具有較強的從根部向地上部運輸的能力,適合錳礦廢棄地的生態恢復。

表2 錳礦區土壤中各種重金屬質量比 mg/kg
2.3 篩選結果與討論
生物富集系數(bioaccumulation coefficient,BC)是指植物體內某種重金屬元素與土壤中同種重金屬質量比的比值。富集系數越大,富集能力就越強。如表3所示,礦區植物對Pb、Zn、Cu、Cr的富集能力較弱,富集系數BC均<1。對Mn富集較強的白背葉、商路、懸鉤子、蓼草,富集系數分別為1.62,1.07,1.24,2.75。這些植物的 Mn富集系數均>1,且植物地上部分 Mn質量比>10 000 mg/kg的臨界標準,表現出較強的富集Mn的能力。

表3 礦區主要優勢植物的重金屬質量比及富集系數 mg/kg

續表3
Mn是植物生長必需的微量元素,正常土壤中生長的植物Mn質量比一般在20~500 mg/kg范圍內變動。一些生長在富錳礦區和低錳土壤上的植物 Mn質量比為1 000~5 000 mg/kg[8]。而通過對18種優勢植物進行富集能力測試可知,湘南東湘橋錳礦區的白背葉、商路、懸鉤子、蓼草富集系數均>1,且植物地上部分 Mn質量比>10 000 mg/kg的臨界標準,顯示出了超強的Mn富集能力,考慮到白背葉和懸鉤子的葉片絨毛吸附,尚不能認定為超富集植物,蓼草、商陸是Mn污染土壤植物修復的理想物種,特別是蓼草,其葉片對Mn的富集系數達到了2.75。白背葉、算盤子和商路對Mn的吸收和吸附能力強且在錳礦恢復初期的廢棄地分布范圍廣、生長較快、數量較多,并能形成局部小群落,而且能適應土壤中重金屬元素較多的環境和廢棄地的貧瘠、養分不均衡、干旱等不良因子,可考慮作為先鋒植物對廢棄地土壤進行修復。而薯蕷雖然沒有達到植物地上部分Mn質量比>10 000 mg/kg的臨界標準,富集系數僅為0.35,但富集能力較強且生物量大,為纏繞草質藤本,可用于固定礦區尾礦渣等松散容易水土流失區域的土壤。云實雖為礦區廢棄地偶見種,但考慮到云實生物固氮作用,在礦區廢棄地修復后期,可運用于改善土壤土質。
根據GB 2762-2005中關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標準,辣椒中Pb質量比不應超過0.1 mg/kg,Cd質量比不應超過0.05 mg/kg,Cr質量比不應超過0.5 mg/kg,蘿卜中Pb質量比不應超過0.1 mg/kg,Cd質量比不應超過0.1 mg/kg,Cr質量比不應超過0.5 mg/kg。而通過對人工種植的經濟作物辣椒和蘿卜的實驗監測,發現其食用部分重金屬均超標。例如,辣椒果實中Pb、Cd、Cr的質量比分別為14.7,0.8,2.1 mg/kg,蘿卜根中Pb、Cd、Cr的質量比分別為13,0.8,3.8 mg/kg。故礦山恢復早期不宜直接種植食用經濟作物,以免礦區重金屬元素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危害健康。
通過對湘南東湘橋錳礦區植被資源的調查與分析,發現典型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在過去幾十年開采過程中徹底被毀,當前形成的為典型的亞熱帶植物類群,正處于以多年生灌草叢群落為主的演替初級階段,隨著土壤條件逐步被改善,大量物種將陸續出現,最終演替為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植被破壞后的演替可視為原生演替[9]。原生演替的物種主要通過土壤潛在物種庫待環境改善后萌發成為植株,以及礦區周圍生態系統物種在風、水、動物取食等自然力量及人類耕作等人類活動下被帶到污染區擴散生長[10]。對受重金屬污染嚴重的礦區而言,由于自然選擇的結果,使得這些植物已經能夠很好地適應特殊生境,耐受干旱、貧瘠,以及重金屬的脅迫[11]。湘南東湘橋錳礦區屬于Mn中-高污染區,該礦區形成近半個世紀,存活下來的植物都能正常完成生活史,因此,湘南東湘橋錳礦區所調查的54種植物均可作為錳礦廢棄地修復的植物資源庫。
從湘南東湘橋錳礦區所調查的54種植物中,選取18種主要優勢植物,對其富集與運轉重金屬能力的分析,結果發現植物體各組織吸收與富集重金屬含量的不一致性。從表2和表3可知,鹽膚木、辣椒等植物地下部分Mn含量高于地上部分,表現出一般植物所具有的特征;而蓼草、商陸、白背葉、懸鉤子、翅柃、柞樹、算盤子、陰香、薯蕷等植物地上部分Mn含量高于地下部分,表現出其特殊的富集重金屬特征。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在于:(1)重金屬Mn主要通過根吸收進入植物體內,因此有些植物根部重金屬Mn含量高于莖葉;(2)白背葉、商路等物種吸收的重金屬Mn在其體內由地下部分向地上部分轉移率較高,從而使得莖葉中Mn含量高于根部;(3)錳礦區附近冶煉廠排放的金屬顆粒物塵降吸附于植物葉面,從而導致莖葉也具有較強的Mn富集能力[12]。調查中發現,懸鉤子、白背葉植物葉片表面粗糙有絨毛,極易吸附空氣中的重金屬顆粒等特點,且在實驗清洗步驟中難以清洗干凈可能是導致其莖葉中Mn含量高的重要原因。
從表2和表3的篩選研究中還發現,18種優勢植物的富集重金屬Mn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如在相同土壤環境中的蓼草等地上與地下部位Mn含量差異明顯,而芒草等地上與地下部位Mn含量差異較小,體現了物種富集重金屬能力大小的差異性。
另外,從篩選試驗結果可知,采于重金屬高濃度土壤中的植物重金屬含量明顯高于重金屬低濃度土壤中植物,表明土壤濃度與植物吸收重金屬的能力正相關。
3 結論
對湘南湘南東湘橋錳礦區的植物資源進行調查,調查的所有樣地共記錄到植物32科52屬54種。從54種植物資源中選取礦區廢棄地恢復區主要優勢植物18種。通過測定其各自所在土壤中的重金屬含量和植物中的重金屬元素含量,計算植物的生物富集系數,篩選對礦區Mn具有超富集能力的植物。結果表明,對Mn富集較強的白背葉、商路、懸鉤子、蓼草,富集系數分別為1.62,1.07,1.24,2.75,可以用于對錳礦區廢棄地的金屬富集。而礦區種植的辣椒果實、蘿卜根中Pb、Cd、Cr的含量均超過GB 2762-2005中關于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標準,因此礦山恢復早期不宜直接種植食用經濟作物,以免礦區重金屬元素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危害健康。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為廢棄錳礦區植物修復中超富集植物的選擇提供技術支持。
[1]王爾賢.中國的錳礦資源[J].電池工業,2007,3(2):184-188.
[2]李永庚,蔣高明.礦山廢棄地生態重建研究進展[J].生態學報,2004,24(1):95-100.
[3]SHU Wen-sheng,YE Zhi-hong,ZHANG Zhi-quan,et al.Natural colonization of plants on five lead/zinc mine tailings in Southern China[J].Restoration Ecology,2005,13(1):49-60.
[4]WONG Ming-hong.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e degraded soils,with emphasis on metal contaminated soils[J].Chemosphere,2003,50:75-78.
[5]YE Zhihong,SHU Wensheng,ZHANG Zhiquan.Evaluation of major constraints to revegetation of lead/zinc mine tailings using bioassay techniques[J].Chemosphere,2002,47:1 103-1 111.
[6]ERNST W H O,SHAW A J.Heavy metal tolerance in plants:Evolutionary aspects[M].Florida:CRC Press,1989:21-38.
[7]張 溪,周愛國,甘義群,等.金屬礦山土壤重金屬污染生物修復研究進展[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0,33(3):106-112.
[8]劉 恒,薛生國,何哲祥,等.錳超富集植物種質資源及耐性機制研究進展[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1,34(6):98-103.
[9]張 玲,方精云.秦嶺太白山4類森林土壤種子庫的儲量分布與物種多樣性[J].生物多樣性,2004,12(1):131-136.
[10]孫書存,陳靈芝.東靈山地區遼東櫟種子庫統計[J].植物生態學報,2000,24(2):215-221.
[11]易 鋒,王宏鑌,高建培,等.砷礦區植物對重金屬的吸收和富集特征[J].安全與環境學報,2011,11(4):14-22.
[12]李有志,羅 佳,張燦明,等.湘潭錳礦區植物資源調查及超富集植物篩選[J].生態學雜志,2012,31(1):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