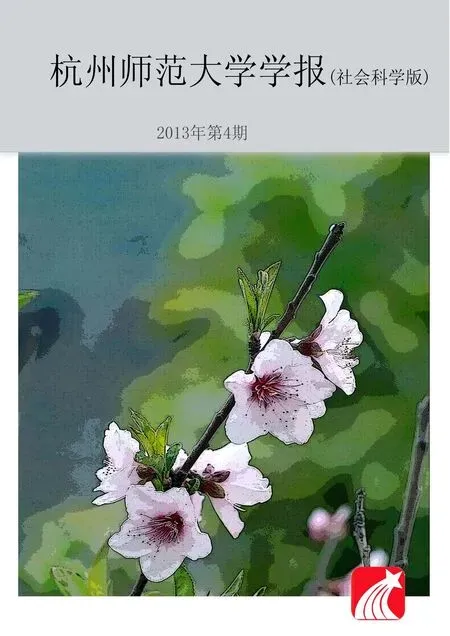反思與再造:宋代士人對禮治與制禮的討論
姚永輝
(杭州師范大學 1.人文學院;2.國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反思與再造:宋代士人對禮治與制禮的討論
姚永輝
(杭州師范大學 1.人文學院;2.國學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宋代官修和私修禮儀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對禮治的深入討論,大概包括史鑒和內涵闡發兩種取徑,前者側重于從歷史事實中發掘禮治之于國家統治的意義,后者則側重于闡發禮的內涵與外延,雖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禮的功能和實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閣的經典運用于現實社會等問題。依時而制禮是經典從文本通向實踐的前提條件,如何訂立切合時代需要、貴本而親用的禮文是積極推行士庶禮儀的士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宋代士人在檢討此前禮儀制作得失的基礎上,對禮儀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開了討論,尤以朱熹的觀點為重,提出整體改造、上下有序、吉兇相稱,考訂節文度數、推明其義等諸多準則或方法。
宋代;禮治;制禮;朱熹;司馬氏書儀
一 從“家”到“天下”:禮是秩序整治的通用手段
費孝通將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比喻為如同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就是丟石頭在水中所形成的同心圓性質,而儒家所謂人倫,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1](PP.25-26)因此,從個人到家庭、家族、宗族,再到國家,就形成了一套具有伸縮功能的差序格局。宋代士人相信禮治是貫通并維系差序格局中各等次秩序的根本途徑。如果說在禮法隳頹、事功需要極為迫切的中唐時期,“因人以立法,乘時以立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2](P.118),還多少顯得有些無力迂闊,那么至北宋真、仁時期,隨著政權的穩固和內政改革開始預熱,就確實具有了現實的可能。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六月,剛被朝廷任命仍知諫院的司馬光就在《謹習疏》中論及國家治亂興衰的根本措施在“禮”。反思歷代政治,讓司馬光相信“禮”之于國家治理的效用不可小覷,“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于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余俗未絕于民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即便是對于天下莫與之敵的曹操,也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不敢公然廢漢自立,正是由于心有所懼,才“畏天下之人疾之”。然而,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風俗日壞,入于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及至唐代,“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鉞”,“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涂炭”[3]。司馬光以“禮”為治國之本的觀念一以貫之,后來在主持《資治通鑒》的編撰中,又以更加鮮明的態度強調“禮之為物大矣!用之于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于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于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絕非僅僅只能維持幾席之上、戶庭之間之不亂[4](PP.375-376)。家、鄉、國、天下,司馬光認為禮治在上述不同層級具有相異的功用,它們的作用總和構成理想的國家秩序。
除了司馬光等注重通過史鑒論議“禮”之于治理國家的意義之外,還有許多士人試圖從“禮”本身的內涵闡發。李覯以其《禮論》7篇與《周禮致太平論》51篇而贏得大名,后人多將其以禮治國的思想與王安石聯系起來論議,并認為王安石的《周官新義》正是對其思想的發揮。在李覯看來,禮兼涉“人道”與“世教”,是儒家修齊治平之根本手段,“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矣”[5](P.5),并將禮分為“禮之本”(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支”(樂、政、刑)、“禮之別名”(仁、義、智、信),通過問答的方式,逐一闡明觀點、問疑辯難。[5](PP.5-6)此外,李覯又在《周禮致太平論》中,從內治、國用、軍衛、刑禁、官人、教道等方面闡述統治者如何從《周禮》中獲取治國之方。這恰好與后來王安石以《周禮》大行其道的路徑相合。李覯的觀點偏向于外在的措施,周敦頤所開啟的“禮,理也”[6](P.99)的論證則是向內尋找“禮”之于治國依據的路徑。周敦頤所說的理還僅僅為陰陽之理,張載、二程所說的“禮即理”,則強調“禮”具有“天經地義”的意義,如張載認為“禮不必皆出于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7](P.264),二程也說“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偽貌飾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圣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8](P.668)。
北宋時期大部分討論側重于論述禮治之于國家統治的合理性,南宋《儀禮經傳通解》的編纂,則將禮治從家到天下的不同層級的理想構思與禮學著作融合為一體。朱熹與其弟子主編的《儀禮經傳通解》是醞釀多年的大工程,其主體構思是以《儀禮》為本經,“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9](PP.687-688),相當于集儀節與禮義為一體、融合古今闡述的合本。《儀禮經傳通解》在篇章結構上打破了漢晉以后“吉、兇、賓、軍、嘉”的分類模式,以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的模式進行編排,除了學禮、喪禮、祭禮三個方面的禮儀在施禮范圍上有其特殊性之外,似乎可以說,《儀禮經傳通解》以家、鄉、邦國、王朝這樣的施禮范圍來劃分禮儀類別,與朱熹承繼《大學》“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模式有著內在的聯系。[10](P.130)
二 禮儀文本制作的檢討
依時而制禮儀文本是經典從文本通向實踐運用的前提,如何訂立切合時代需要、貴本而親用的禮文是積極推行士庶禮儀的士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檢討前代的禮文和當時禮儀推行狀況就成為首要任務。宋人的反思與檢討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禮文繁瑣,多不適用。
禮,時為大,古禮零碎繁冗且未因時損益是彼時禮儀文本制作的最大問題。朱熹認同“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11](P.2177)。碩果不食、古禮難行,將禮儀文本化繁為簡,掇其綱要最為關鍵,因此,“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11](P.2177),“令人蘇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11](P.2178)。
第二、背離禮緣情而作的精神。
在北宋士人對禮儀文本制作的反思中,蘇軾或可成為代表。蘇軾認為三代之后,“豪杰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然而禮廢樂墜”,“相與咨嗟發憤而卒于無成者”,其原因并非是乏才學,而是“論之太詳,畏之太甚”。禮之根本,在于緣情而作,因人情之所安而為之節文,人情隨時而變,禮文也應因時損益,執人情之所無定而為定論,才是制禮的核心精神,而彼時儒者所論禮文卻因人情之所不安而作,當然極難在現實中推行[12](P.49)。蘇軾除了抱怨禮文未因時而變之外,更強調“禮緣情而作”卻被當時論禮者所忽略的事實。宋代士人的禮論中,對禮緣情說有太多的闡述。此前的研究多從思想上梳理子思、孟子至道學一脈的發展流變,而較為忽略禮儀改革的需要。事實上,彼時朝野涉禮之論對緣情說的強調和關注,一方面,在于以先秦至秦漢時代的言論證明當世禮治的合情合理,使從中唐以后逐漸擴展蔓延的禮為畏途之說得以消解;另一方面,能拉近束之高閣、不明其義的禮文與民眾現實生活的距離。上述兩者都為禮文改造提供了基礎。
第三、禮學專門之家乏見,其余多陷于迂闊。
禮儀文本的制作需要得到禮學論證的支持,然而在宋代士人看來,彼時的禮學遠不足以提供參考。宋代三禮學,《周禮》最盛、《禮記》次之、《儀禮》最末。《周禮》有王安石的倡導,著述達百種之多;二程雖然欣賞張載在關中的禮俗教化活動(將傳統的禮學向實踐方面轉向),但同時也認為“舉禮文,卻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為風后世,卻只是明道”[8](P.146),故相對而言,討論《禮記》較多,尤以《中庸》篇的闡述為重點。除此之外,如李格非的《禮記精義》、真德秀《大學衍義》、衛湜《禮記集說》、魏了翁《禮記要義》、方愨《禮記解義》,司馬光、張九成、楊時、晁公武等人的《中庸》相關論說在當世都較為有名。
相比之下,最能為禮儀文本制作提供參考的《儀禮》之學卻堪稱冷門。《儀禮》之學的衰頹,在宋儒看來,主要是因為禮學專門之家的缺失和王安石的科考改革。“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11](P.2184),“六朝人多是精于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11](P.2227)。六朝以后,朝廷禮典的編撰雖然較盛,《開元禮》更是一代禮文的典范,但《儀禮》之學卻問津者不多[13](PP.338-347)*彭林分析了正史禮樂志中涉禮部分的內容編排,認為漢代以后,從目錄上看,重視儀而不重視禮,沒有理論的依托。。及宋,王安石科考改革,將原來與六經三傳并行的《儀禮》,罷去,士人更是讀《禮記》,而不讀《儀禮》[11](P.2187),“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卻尚自記得。自荊公廢了學究科,后來人都不知有《儀禮》”[11](PP.2225),宋初的禮官均有專門之學,自王安石罷開寶通禮科,禮官的專業性大大降低,“不問是甚人皆可做”[11](P.2183),因此,朱熹認為王安石廢《儀禮》而取《禮記》,完全是舍本而取末的做法[11](P.2225)。偶有涉獵禮學考證者,亦多陷入繁瑣且乏見地的考證,“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溺于器數而陷于“迂闊”[11](P.2177)。
三 禮儀文本改造的準則
宋代士人在上述檢討與反思的基礎上,對禮儀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開了討論,以朱熹的觀點較為全面。
第一、整體改造、上下有序、吉兇相稱。
改造禮儀,是自上而下、吉兇相稱的龐大工程。儒家的吉兇兩套禮儀系統,在區別中構成整體,“今吉服既不如古,獨于喪服欲如古,也不可”[11](P.2188);另外,禮由尊卑降殺而成,對下的改造必須參照上而成,比如冠制尊卑,以中梁為等差,宋時天子用二十四,如果以三、二、二、二、二的標準降殺,至庶人則竟用十二,“甚大而不宜”,最好的方式是“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升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裹髻”[11](P.2188)。若僅改庶人禮,而不改天子和品官之禮,就不能構成禮儀的等級序列,也就失去了制禮的基本意義。因此,在上者的理解和支持對禮儀的推行尤為重要,“圣賢不得其位”,則“此事終無由正”[11](P.2188)。
第二、綜合散失諸禮、考訂節文度數、推明其義。
在宋代士人,尤其是理學家看來,禮儀文本的改造非唯儀節的連綴,還要各有其理、各有其義,即禮儀文本應是儀節與禮義精神的綜合體。因此,作為禮儀文本的改造者,應首先綜合散失諸禮,錯綜參考,推敲其節文度數,“一一著實”,再在此基礎上“推明其義”,體會禮書的精密義理,也就是修煉內功。只有這樣,才能見得禮文深意,不至于“溺于器數”,“一齊都昏倒”[11](P.2186),只有建立在對古禮的深入認知的基礎上,才能在改造中知其取舍。比如,古禮稱情而立文,就喪禮而言,莫大于哀,哀情是判斷是否盡禮的根本原則,因此,朱熹認為,在對喪禮儀文的改造中,“初喪”環節可以不必要求過嚴,“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11](P.2285),所以只要具哀戚之心,類似這些部分都可依照今俗而行,刪減古禮。
第三、掇其綱正、略去瑣細。
制禮者要避免“溺于器數”就要區別禮之小與禮之大,區別變禮和經禮,在掇其綱正的基礎上,再往內里填充細節。“圣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11](P.2179)。朱熹曾以五服為例,向賀孫說明,“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粗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紐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11](P.2186),“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垛,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11](P.2180)
第四、減殺古禮、切于日用。
禮,時為大,因時而制禮,才能切于日用,否則不過是徒添具文。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于損周之文,從古之樸。古禮難行,制禮者必須參酌古今之宜,而彼時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為后人“自去減殺”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的底本。[11](P.2185)
第五、既要有所本,也要有所創新。
制禮者,須參酌古今。從古禮處領悟禮義精神和掌握儀節流變的脈絡,從今俗處選擇為人情之所安、切于日用,同時又有裨于風化者,編入禮書之中。無論是古禮、抑或納入禮書中的今俗,必然都要有所本,“皆有來歷”,最切忌的就是“出于私臆”[11](P.2179)。張載制禮,就因為多有杜撰,不為朱熹欣賞,相比之下,《司馬氏書儀》則是參酌古今的佳作。有所本的同時,也要具有敢于改變、不因循守舊的創新精神,“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做”[11](P.2179)。
四 結 語
據現有文獻,宋代的私修儀典以書儀、家禮、鄉約為主要體裁,包括司馬光《司馬氏書儀》、舊題朱熹《家禮》,呂大忠《呂氏鄉約》,朱熹《增損呂氏鄉約》、袁采《袁氏世范》、陸游《放翁家訓》《緒訓》、趙鼎《家訓筆錄》、劉清之《戒子通錄》、葉夢得《石林治生家訓要略》、李宗思《禮范》、高閌《送終禮》、周端朝《冠昏喪祭禮》、龐元英《嘗聞錄》等。宋代士人圍繞著“禮治與制禮”的討論與私修儀典的修撰同步,事實上,朱熹等提出總結的上述原則已在部分禮書中得到較好的實踐。司馬光《書儀》正是秉承“嚴守禮義”與 “因時制范”兩大原則,才在宋代眾多的禮書中脫穎而出,并成為《家禮》及其他南宋私修儀典內容的重要來源。《書儀》包括儀注和詳細的禮義說明兩部分內容,在對儀節的古今損益中,既有保留,同時也因時因地變更古禮,并闡明保留或者變更的理由。*參見拙文《從“偏向經注”到“實用儀注”:南北宋私修儀典體例的變化——以喪儀為例的分析》,待刊。胡叔器曾問及二程、張載、司馬光所作禮書的優劣,朱熹評價說:“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溫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11](P.2184)
宋代士人對“禮治與制禮”的討論,最終指向都是如何將代表著儒家理想的禮儀滲透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從而實現對社會秩序的重整。如果說北宋司馬光的《書儀》還帶有“經注”的性質(包括儀注和詳細的禮義說明),那么至南宋《家禮》時,就已完全偏向“儀注”,即簡省對禮義的闡釋,突出具體儀節的操作細則,極大提升了儀典的實用性,所以,我們常常在文獻中可以見到民眾使用這些儀典的事例。相比之下,宋代同樣備受矚目的官修儀典《政和五禮新儀》,雖然首次制定了庶人冠、婚、喪儀,然而基于辨上下、別等差的國家禮典性質,在制作方法上秉承“以多、大為貴”和“降殺以兩”的原則,并未精心考慮實用性,或根據儀文不適合民間使用的情況而做出修改調整。因此,盡管政府在禮儀推行的過程中,采用了強制性的措施,仍然在推行幾年后被開封府申請停止。這說明,在禮俗教化的問題上,“折中與融合”遠比“強權或強制”有效,事實上,這也符合先秦至秦漢儒家之于“因時制禮”根本原則的闡述,在時代變遷中有所損益才是“禮作為規范人們言行的手段”得以延續的先決條件。
[1]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張說.張燕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M].四部叢刊本.
[4]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5]李覯.李覯集[M].王國軒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1.
[6]周敦頤.周濂溪集:叢書集成新編(第60冊)[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7]張載.張載集[M].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
[8]程顥,程頤.二程集[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
[9]朱熹.朱子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王啟發.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編纂及其禮學價值[C]//炎黃文化研究:第3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11]朱熹.朱子語類[M].黎靖德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蘇軾.蘇軾文集[M].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13]彭林.從正史所見禮樂志看儒家禮樂思想的邊緣化[C]//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
《樂學集》第二輯印行

我刊2012年度“人文振興計劃”項目“學報青年作者系列研討會”研討內容6月結集印行。2012年我刊共舉辦6次作者系列討論會,分別為:“照片與文字背后的日常生活”、“建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的評估與管理”、“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小說創作”、“西方社會的啟蒙觀念與現代中國的思想”、“民國想象:知識的轉變與典范的確立”、“國學在當代:作用與途徑”,共計15個主題發言,65人次參與討論,內容涉及文學、哲學、歷史、藝術等諸多領域,為校內青年作者的學術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也為學校的學術積淀作出了貢獻。
ReflectionandRewriting:TheDiscussionofRuleofRiteandMakingRitualbyIntellectualsinSongDynasty
YAO Yo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With the discussion on rule by Confucian rites in So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and intellectuals were dedicated to rewriting all kinds of ritual books. In order to apply Confucian rites to the populace’s daily life and readjust the social order, the intellectuals explored it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ate control and discussed the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Confucian rit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times, rewriting ritual book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pply classical texts in social practice.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promoting Confucian rites in the populace had to answer how to rewrite ritual books in a feasible and practical way. The Song intellectuals discussed this issue and put forward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ir reflection on previous ritual books.
Song Dynasty; rule of rite; making ritual; Zhu Xi;Shuyi
2012-08-15
姚永輝(1980-),四川瀘州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國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傳統禮儀和宋代社會文化研究。
B244
A
1674-2338(2013)04-0034-05
(責任編輯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