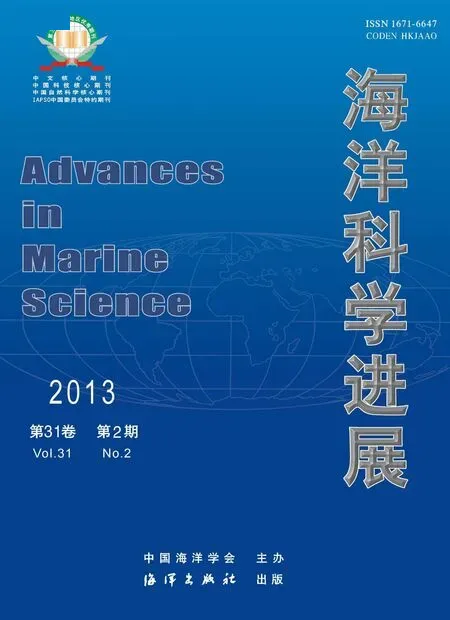黃河三角洲YDZ1孔沉積環境分析
李谷祺,陳沈良*,彭 俊,陳小英,劉 鋒,陳廣泉
(1. 華東師范大學 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62;2. 東華理工大學 核工程技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3. 青島海洋地質研究所,山東 青島 266071)
黃河是中國的第二大河,長5 465 km,流域面積為7.52×105km2,以多泥沙,河道善淤、善決、善徙著稱于世[1-3]。晚更新世以來,黃河三角洲地區經歷了3次海侵過程, 公元前6000年左右前海平面達到最高峰,海侵達到最大邊界,公元前6000年左右以后基本保持穩定狀態[4-7]。公元前6000年左右至公元1855年之間,黃河河道頻繁擺動,分別在黃驊、蘇北、利津和無棣四個區域入海。1855年以后,黃河在銅瓦廂決口,奪大清河由東營入渤海,帶來巨量泥沙[1]。不同時期形成的三角洲葉瓣疊覆起來,形成了復雜的黃河三角洲沉積體系。因此,對黃河三角洲垂向沉積層序的研究要比其他大型河口三角洲困難很多。
粒度是沉積物的基本性質之一,沉積物粒度特征是反映沉積環境,特別是沉積動力條件明顯的標志之一。粒度分析是經典的沉積學研究方法,可以通過平均粒徑、分選系數、偏態和峰態等粒度參數來識別沉積環境類型,推斷沉積物擴散搬運過程,解釋沉積動力作用[8]。粒度分析在河口海岸、淺海陸架、潮汐汊道和潮流沙脊等多種海洋環境中得到廣泛應用,所得結果令人滿意[9-12]。地質歷史時期中,沉積物往往都是多種物源或者沉積動力過程的混合體,環境敏感粒度組分的意義在于能夠從多峰態頻率曲線中分離出那些對沉積環境中水體能量變化敏感,能夠指示沉積環境中不同能量水動力的粒度組分[8]。通過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對沉積環境進行解釋的研究在陸架邊緣海地區應用較多[13-14],但在黃河三角洲地區應用較少[15]。因此,通過對黃河三角洲五號樁附近YDZ1孔沉積物進行粒度分析,提取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并結合其平均粒徑在垂向上的變化特征和ASM14C測年數據,探討黃河三角洲的沉積特征和沉積環境變化過程,為三角洲地區的資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區域概況
黃河三角洲五號樁地區位于東營市河口區仙河鎮東北部,為1953-1976年黃河自神仙溝和釣口河流路行水入海而形成的區段(圖1)。該地區岸線向東北方向突出,潮汐類型主要為半日潮,以旋轉潮波為主,大陸氣候影響強烈,風暴潮頻發,是黃河三角洲遭受強烈沖刷的區段。

圖1 YDZ1孔位置圖Fig.1Location of drilling core YDZ1
2 材料與方法
YDZ1孔位于黃河三角洲五號樁附近(圖1),坐標為118°54′27′′E,38°01′05′′N。2009-04進行鉆孔巖芯取樣,鉆孔進尺31.66 m,獲取巖樣28.68 m,取芯率為90.6%。在實驗室將巖芯剖開后進行樣品沉積特征描述,并在有泥碳或貝殼處采集樣品用于AMS14C測年,樣品描述完成后以5 cm為間隔進行分樣,共獲取沉積物樣品610個。
將樣品充分混合均勻后,取適量放入燒杯,注入10 mL蒸餾水,加入1~2滴質量濃度為1.11 g·L-1的H2O2去除有機質。用超聲波清洗機振蕩后,加入1~2滴質量濃度為104.7 g·L-1的HCl,使其充分反應,然后將燒杯注滿蒸餾水靜置24 h后抽去上層蒸餾水,加入1~2滴分散劑用超聲波清洗機振蕩,使沉積物樣品充分分散后進行粒度測試。測試在華東師范大學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完成,測量儀器為Mastersizer 2000型激光型粒度儀。粒級標準采用尤登-溫德華氏等比制φ值粒級標準。
14C原始樣品送到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14C樣品制備實驗室進行樣品制備,然后將樣品送到北京大學加速質譜實驗室完成測年。該14C測量專用AMS系統為美國NEC公司進口設備。
3 分析結果
3.1 沉積物類型及其粒度組成
根據Shepard沉積物分類方法,YDZ1孔沉積物樣品的組成類型主要有5種:砂、粉砂質砂、砂質粉砂、粉砂和粘土質粉砂(圖2)。沉積物以粉砂占優勢,體積分數超過50%,砂體積分數次之,粘土體積分數最小(表1)。由圖2知,在13.50~24.10 m粘土體積分數高,平均值為22%,明顯高于全孔沉積物粘土體積分數的平均值。在1.80~3.60 m和24.10~31.66 m處粉砂體積分數低,其中1.80~3.60 m平均值為41.17%,24.10~31.66 m平均值為31.77%,遠低于全孔沉積物粉砂體積分數的平均值。砂體積分數變化與粉砂相反,在1.80~3.60 m和24.10~31.66 m處砂體積分數高,其中1.80~3.60 m平均值為51.72%,24.10~31.66 m平均值為61.15%,遠高于全孔沉積物砂體積分數的平均值。

表1 YDZ1孔沉積物粒度組成組分統計Table 1 Particle compositions in the sediments of core YDZ1
3.2 沉積物粒度參數的垂向特征
粒度參數的計算方法有圖解法和矩值法,其中圖解法計算易行,結果穩健[10]。對YDZ1孔樣品采用Folk-Ward圖解法計算粒度參數,YDZ1孔沉積物粒度的參數垂向序列變化如圖2所示,圖中虛線為各參數均值線。
1)平均粒徑(Mz):反映沉積物粒度組成的總體粗細狀況,代表粒度分布的集中趨勢,可以解釋沉積物物質來源與沉積動力環境。YDZ1孔沉積物平均粒徑的粒級范圍為2.80~7.93 φ,平均值為5.32 φ。1.80~3.60 m和24.10~31.66 m處平均粒徑大,表明沉積動力強。在24.10~29.00 m處平均粒徑變化幅度小,推斷沉積動力環境相對穩定單一。在13.50~24.10 m處平均粒徑小,沉積動力弱。總體分析來看,平均粒徑自上而下的分布趨勢為大-小-大,相應的沉積動力環境變化趨勢為強-弱-強。
2)分選系數(σi):表示沉積物的分選程度,多物源供應、不同動力交叉作用等都是沉積物分選變差的原因。YDZ1孔沉積物分選系數的變化為0.82~2.26,平均值為1.70,分選性中等-很差。24.10~31.66 m之間,分選系數明顯減小,說明鉆孔沉積物此段主粒級較突出,分選性偏好。總體分析來看,分選系數自上而下的分布趨勢為小-大-小,和平均粒徑的垂向分布趨勢相反。
3)偏態(Ski):表示沉積物頻率曲線的不對稱性,反映沉積過程中能量的變異。YDZ1鉆孔沉積物偏態值的變化為0~0.69,平均值為0.4,正偏和極正偏顯著。在1.80~13.50 m和23.50~31.66 m處偏態值大,在13.50~23.60 m處偏態值小。總體分析來看,偏態值自上而下的分布趨勢為大-小-大,和平均粒徑的垂向分布趨勢相似。
4)峰態(Kg):反映沉積物粒度頻率曲線中峰凸的程度。YDZ1孔沉積物峰態值的變化為0.71~2.22,平均值為1.41,平坦-中等峰態占35.6%,尖銳-很尖銳峰態占64.4%。在1.80~3.60 m和24.10~31.66 m處峰態值大,峰區窄、高,在13.50~24.10 m處峰態值普遍小,峰區寬、矮。總體分布來看,峰態值自上而下的分布趨勢為大-小-大,和平均粒徑的垂向分布趨勢相似。
綜上所述,YDZ1孔沉積物粒度參數的垂向序列變化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平均粒徑增大,分選性變好,偏態程度增加,峰態變窄;平均粒徑變小,分選性變差,偏態程度降低,峰態變寬。平均粒徑與偏態以及平均粒徑與峰態之間呈正相關性,平均粒徑與分選系數之間呈負相關性。

圖2YDZ1孔粒度參數垂向分布序列Fig.2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grain-size parameters in the sediments of core YDZ1
3.3 YDZ1孔沉積物環境敏感粒度組分的提取
由于物源和沉積動力的復雜性,因此沉積物粒度頻率分布曲線多呈多峰態的特點,如何從多峰態的頻率分布曲線中分離出單一粒度組分并探討其所指示的沉積學意義,成為古環境研究的關鍵[8]。目前對沉積物粒度分布進行多組分分離的數學方法包括Weibull分布擬合、端元粒度模型和粒級-標準偏差法[13-16]。應用粒級-標準偏差法在中國南海、長江口以及黃河口沉積物分析中都得到了成功的應用[13-16],因此對YDZ1孔樣品采用粒度標準偏差法來獲取環境敏感粒度組分。

圖3YDZ1孔粒級-標準偏差圖Fig.3Curve of grain-size vs standard deviation of core YDZ1
圖3中YDZ1孔沉積物有2個明顯的標準偏差峰值,分別對應粒級為0φ和3.25φ,其中0φ處標準偏差值為9.29,3.25φ處的標準偏差值為4.78。經分析,610個樣品中只有5個樣品在0φ處有體積分數,僅占整個樣品數的0.82%,而1.00 φ處也僅有17樣品有體積分數,占整個樣品數的2.8%。所以0~1.00 φ粒級組分不具備普遍意義,不予考慮。因此選取2.75~3.75 φ粒級組分為YDZ1孔沉積物樣品的環境敏感粒度組分。

圖4黃河三角洲YDZ1孔沉積序列Fig.4Sedimentary sequences in core YDZ1
3.4 三角洲沉積環境的劃分
在距今約1.8萬a整個黃河三角洲處于末次盛冰期,海面降到最低位置,海岸線處在東海大陸架前緣,渤海不復存在,三角洲地區為廣闊的平原,地貌營力為河流和湖泊。隨著氣溫升高,海平面上升,在距今約1.2萬a海平面升至現在東海水深110 m的位置,在全新世初期本區主要的地貌營力仍是河流和湖泊。直到距今約6 000 a,我國東部沿海全新世海侵才達到最盛時期[2]。根據YDZ1孔沉積序列(圖4),在24.00 m處自下而上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迅速減小,沉積動力顯著減弱。沉積物中粘土、粉砂、砂的體積分數,以及各項粒度參數均出現明顯的變化,沉積物由粉砂質砂向砂質粉砂和粘土質粉砂過渡。根據AMS14C測年數據,YDZ1孔在22.91 m處AMS14C年齡為(8 645±35) a B.P.,在27.05 m處AMS14C年齡為(13 355±50) a B.P.,因此將24.00 m處推斷為海侵層的底界。在13.50 m處自下而上,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達到最小值,并且逐漸增大,沉積物粘土體積分數迅速減少,沉積物由粘土質粉砂向粉砂和砂質粉砂過渡,沉積動力增強,結合15.19 m處AMS14C年齡為(5 550±40) a B.P.,因此推斷13.50 m處為海侵層的頂界。通過上述分析,將YDZ1孔沉積序列自上而下大致劃分為第一陸相層(0~13.50 m)、第一海相層(13.50~24.00 m)和第二陸相層(24.00~31.66 m)。
由YDZ1孔沉積物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曲線(圖4)知,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粒級范圍為3.00~3.80 φ,均值為3.43 φ,屬于粉砂質砂,粒徑偏大,敏感粒度組分對應的沉積動力因素較強。圖4中,1.80~3.60 m和24.00~31.66 m層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大于3.43 φ,其余層位則普遍小于3.43 φ。YDZ1孔24.00~29.00 m層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值較大,約3.30 φ,變化幅度非常小,說明水動力強并且沉積環境穩定,此層位為陸相沉積層,水動力因素以徑流為主,不受海流、波浪、潮汐等海洋水動力因素影響;YDZ1孔13.50~24.00 m層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偏小且變化幅度大,說明水動力較弱并且沉積環境復雜,此層位為海相沉積層,水動力因素以海流、波浪、潮汐為主,徑流影響弱,由此推斷YDZ1孔沉積物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對應的主要沉積動力因素為徑流,沉積環境為河流相。
第二陸相層位于24.00~31.66 m,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大,顆粒粗,沉積動力強,沉積物為灰黃色粉砂質砂和灰褐色砂互層, 結合31.09 m處AMS14C的年齡為(13 985±50) a B.P.,處于末次盛冰期的晚期,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陸源河湖相沉積。
第一海相層,在22.10 m處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分布最分散,沉積環境復雜,且22.10~24.00 m沉積物類型自下而上由砂質粉砂向粘土質粉砂過渡。推斷此段時間內,海平面上升至YDZ1鉆孔位置,海侵過程開始,受到潮汐、波浪和沿岸流等海洋動力作用的影響,形成了復雜的沉積動力環境,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陸相層向海相層過渡的潮坪相沉積。在14.40~22.10 m處,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小,粘土體積分數較高,沉積物主要為灰黑色粘土質粉砂,并伴有貝殼碎屑,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全新世海侵期間形成的淺海陸架相沉積。在13.50~14.40 m處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為全孔沉積物中最小,顆粒細,粘土體積分數高,沉積物為粘土質粉砂,應為河流懸移質泥沙輸運到淺海陸架波浪作用深度以下地區沉積所致。沉積動力環境弱,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前三角洲沉積相。
在第一陸相層中,以1.80 m和3.60 m為界,將第一陸相層細分為3層:1)在1.80~3.60 m,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增大,水動力增強,沉積物以砂質粉砂和粉砂質砂為主。根據現代黃河三角洲的形成演變過程和鉆孔的地理位置進行分析,1953年黃河在小口子進行人工截灣取直,由神仙溝獨流入海,1964年黃河人工扒開羅家屋子左堤,從神仙溝向北改道由釣口河入海[2]。因此,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陸相河流沉積。2)在0~1.80 m處,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小,粘土體積分數增大,沉積物以黃色粉砂為主,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1964年黃河從神仙溝向北改道,神仙溝廢棄后形成的泛濫平原相。3)在3.60~13.50 m處,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粒級大致分布為3.40~3.60 φ,沉積物為黃色砂質粉砂和灰黃色粘土質粉砂、粉砂互層,沉積物類型對應砂質粉砂、粘土質粉砂等不同組合,反映了自黃河1855年后入海口改道變遷過程中形成的三角洲前緣、三角洲側緣交替沉積的過程,推斷此層沉積環境為三角洲前緣相。
4 結 論
1)黃河三角洲YDZ1孔沉積物類型主要有砂、粉砂質砂、砂質粉砂、粉砂和粘土質粉砂。沉積物平均粒徑粒級范圍為2.80~7.93 φ,分選性中等-很差,偏態以正偏-極正偏為主,峰態為平坦-極尖銳。自上而下,沉積物平均粒徑、偏態和峰態表現為大-小-大的變化趨勢,分選系數表現為小-大-小的變化趨勢。
2)用粒徑—標準偏差方法獲得YDZ1孔沉積物的環境敏感粒度粒級范圍為2.75~3.75 φ,粒徑偏大。根據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垂向分布特征,推斷YDZ1孔沉積物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對應的沉積動力因素為徑流,沉積環境為河流相。
3)根據粒度參數變化的規律性以及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平均粒徑的垂向分布特征,結合分樣時的特征描述和AMS14C測年數據,將黃河三角洲YDZ1孔的沉積相序大致分為3個大相7個亞相:(1)第一陸相層(0~13.50 m),其中0~1.80 m為泛濫平原相,1.80~3.60 m為河流相,3.60~13.50 m為三角洲前緣相;(2)第一海相層(13.50~24.00 m),其中13.50~14.40 m為前三角洲相,14.40~22.10 m為淺海沉積相,22.10~24.00 m為潮坪相;(3)第二陸相層(24.00~33.66 m),為河流相。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QIAO S Q, SHI X F. Status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n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J]. Advances in Marine Science, 2010, 28(3): 480-416. 喬淑卿, 石學法. 黃河三角洲沉積特征和演化研究現狀及展望[J]. 海洋科學進展, 2010, 28(3): 408-416.
[2] GAO S M, LI Y F, AN F T, et al. Form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M]. Beijing:Science Press, 1989. 高善明, 李元芳, 安鳳桐, 等. 黃河三角洲形成和沉積環境[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89.
[3] CHENG G D, XUE C T. Sedimental Geology on the Yellow River Delta[M]. 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7. 成國棟,薛春汀. 黃河三角洲沉積地質學[M]. 北京: 地質出版社, 1997.
[4] XUE C T, YE S Y, GAO M S, et al. Determination of depositional age in the Huanghe Delta in China[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09, 31(1): 117-124. 薛春汀, 葉思源, 高茂生, 等. 現代黃河三角洲沉積物沉積年代的確定[J]. 海洋學報, 2009, 31(1): 117-124.
[5] XIN C Y, HE L B. Depositional process in the Huanghe Delta since late Pliocene[J].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of Huanghai and Bohai Seas, 1991, 9(1): 33-41. 辛春英, 何良彪. 上新世以來黃河三角洲地區的沉積作用[J]. 黃渤海海洋, 1991, 9(1): 33-41.
[6] LIN C M, JIANG Z X, DONG C M, et al.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model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J].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1993, 17(3): 5-11. 林承焰, 姜在興, 董春梅, 等. 黃河三角洲沉積環境和沉積模式[J]. 石油大學學報, 1993, 17(3): 5-11.
[7] CHEN X Y. Coastal erosion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modern Yellow Delta under land and sea interaction[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8. 陳小英. 陸海相互作用下現代黃河三角洲沉積和沖淤環境研究[D].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 2008.
[8] SUN D H, AN Z S,SU R X,et al.Mathematical approach to sedimentary component partitioning of polymodal sediments and its applicatons[J].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2001,11(3):269-276. 孫東懷,安芷生,蘇瑞俠,等.古環境中沉積物粒度組分分離的數學方法及其應用[J].自然科學進展,2001,11(3):269-276.
[9] LIU D Y, LI W R, PENG S S, et al. Current applicaton of grain size analysis in Chinese loess paleoclimatic study[J]. Periodic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 40(2): 79-84. 劉冬雁, 李巍然, 彭莎莎, 等. 粒度分析在中國第四紀黃土古氣候研究中的應用現狀[J].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 2010, 40(2): 79-84.
[10] JIA J J, GAO S, XUE Y C. Grain-size paraments derived from graphic and moment methods: A comparative study[J].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2002, 33(6): 577-582. 賈建軍, 高抒, 薛允傳. 圖解法與矩法沉積物粒度參數的對比[J]. 海洋與湖沼, 2002, 33(6): 577-582.
[11] XU J X. Grain-size characteristics of suspended sedi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China[J]. Catena, 1999, 38(3): 243-263.
[12] SAITO Y, YANG Z S, HORI K. The Huanghe (Yellow River) and Changjiang(Yangtze River) Deltas: A review on their charateristics, evolution and sediment discharge during the Holocene[J]. Geomorphology, 2001, 41(2-3): 219-231.
[13] XU F J, LI A C, WAN S M, et al. The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grain-size populations in the mud wedge of the East China Sea during the mid-Holocene[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09, 31(3): 95-102. 徐方建, 李安春, 萬世明, 等. 東海內陸架泥質區中全新世環境敏感粒度組分的地質意義[J]. 海洋學報, 2009, 31(3): 95-102.
[14] SUN X Y, LI G X, LIU Y, et al. Response of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grain size group in core Fj104 from mud area in the North of East China Sea to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evolution[J]. Periodic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8, 28(4): 11-17. 孫曉燕,李廣雪, 劉勇, 等. 東海北部泥質區敏感粒度組分對東亞季風演變的響應[J]. 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 2008, 28(4): 11-17.
[15] DING X G, YE S Y, GONG S J, et al.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grain-size population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ZK1 drilling core in Yellow River Delta[J]. Global Geology, 2010, 29(4): 575-581.丁喜桂, 葉思源, 宮少軍, 等. 黃河三角洲ZK1孔巖心環境敏感粒度組分及沉積環境分析[J]. 世界地質, 2010, 29(4): 575-581.
[16] ZHOU L C, LI J, GAO J H, et al. Comparison of core sediment grain-siz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Yangtze River Esturay and Zhousahn Island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sediment source analysis[J]. Marine Geology and Quaternary Geology, 2009, 29(5): 21-27. 周連成, 李軍, 高建華, 等. 長江口與舟山海域柱狀沉積物粒度特征對比機器物源指示意義[J]. 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 2009, 29(5): 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