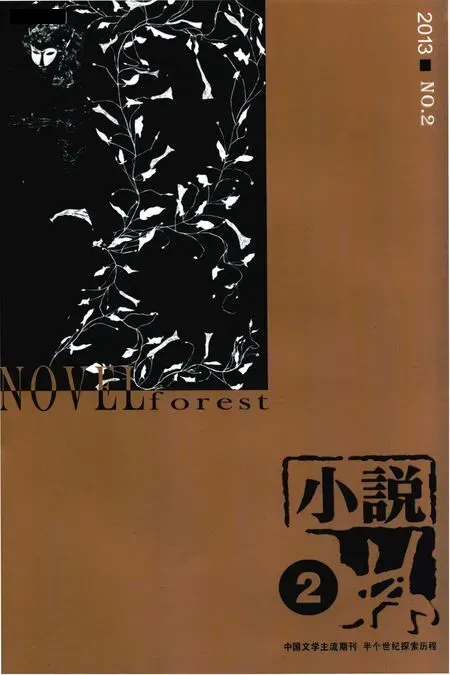隨隨便便說王胄
◎秋 野
隨隨便便說道一個人,不僅對這個人不敬畏、不尊重,還顯露出說道者的淺薄和無知。但我沒辦法,本來就不深沉和沒什么學識的我,在談起一個不遠不近,不薄不厚的朋友時,只能選擇隨便說說。
其實這樣隨便說說也是有著原因的。
王胄在向我們朋友說起某件事或某個人或某個問題之前總是說:我只是隨便說說啊。之后還是這句:我只是隨便說說啊。
王胄要我們朋友向他說說某件事或某個人或某個問題之前,只是改變一下人稱和語氣,說:你隨便說說嘛。之后稍有變化說:你只是隨便說說嘛。
這是我隨便說說王胄的原因之一。我并非刻意效仿他,更沒有半點借他之口語奚落他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認為我這是尊重他的說話習慣和話語權。同時,也使我說起他來沒那么多的顧慮和忌諱,不帶有任何負擔。
我選擇隨便說說王胄的原因之二,是因為我不擅長講故事,不能把情節和細節串聯成一條主線,弄不清頭尾關系,分辨不出一個人的突出個性和特點,也不知道先說一個人的什么,后說一個人的什么。于是,只能隨便說,想到哪里說到哪里。
先從哪里說起呢?盡管不知道從哪里說起,還是要思考一番的。此時,我面對而坐的窗外,正下著今年夏天最強最大的一場暴雨,雙層玻璃窗也沒能阻隔暴烈的雨聲。突然一聲炸雷作響,差點把窗戶的玻璃擊碎。于是,我恐慌地站起把窗簾匆匆拉上。再坐下時,我忽然想起兩年前的一個晚上。
一樣是夏天,一樣是一場最強最大的暴雨,我坐在現在坐的窗前。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半天,我無動于衷,因為那天的雨聲像今天一樣暴烈。倒是在另一個房間的妻子喊我,說:親愛的,你怎么不接電話呢?我這才看見電話機上來電顯示屏閃著光亮的數字。說起來有些不可思議,當我拿起話筒時,窗外暴烈的雨聲突然小了。繼而,很快又消失了,頓時屋里屋外一片安靜。這時候的安靜真好,讓人的心也突然放了下來。
我問:哪位?電話那邊一個似乎等得急不可耐的聲音說:老王,王胄。我忙說:噢,王胄兄呀。王胄說:你怎么不接電話?我說:外邊雨聲太大,沒聽見,你那沒下雨嗎?王胄說:巴掌大的小城,怎能沒下?接著就說:我問問一個人。我說:誰呀?王胄說:此人姓朱,人稱朱總,你認識的,上次聽你說過你和他一塊吃過飯呢。你還說那頓飯是你今生至此,吃的最豪華最昂貴而且最排場的一頓飯嘛。
王胄的話讓我匪夷所思起來。
……家父一個老戰友的兒子,在我們小城官居要位,我就不說他的名字了。一日,電話約我去他辦公室談件從前之事。事不大,三言兩語就談個清清楚楚。我正要起身告辭,他辦公桌上電話響了。他看出我的意思,一手去接電話,一手伸出來示意我暫且坐下,不急于告辭。沒留意他對著電話說什么,只見他放下電話果斷地對我說,不走,停會兒我帶你去參加一個場子。我不解地問他什么場子。他說飯場。我誠惶誠恐,忙說,不不,我去不合適吧。他說,很合適,正好你在他們面前是個陌生人,他們不至于明目張膽地要我怎么樣。我一時更覺糊涂,又不便多問什么,就下意識地點點頭。他見狀,不再含蓄,說,就是幫我應付一下場面,免得我經受不住他們有些人軟硬兼施的誘脅,犯下錯誤。聽了,我仍似懂非懂。時間到了,他的專用座駕把我倆拉到咱們小城一家最好的飯店。在一前一后兩名服侍生的引導下,走進了88888房間。房間里包括我和他一共十一個人,其中站著五位是穿著開衩旗袍的服務員。坐在桌上吃飯的五個人,每人身邊站著一個服務員,隨時為客人點煙、夾菜、遞茶。還剩一位長發女孩,優雅地坐在墻角,專注而輕盈地彈撥著一架古箏。電動旋轉的餐桌上,煙是九五至尊;酒是茅臺;菜嘛,大都是我沒吃過沒見過的。介紹我時,父親戰友的兒子平淡的語氣只說四個字:一個兄長。餐中,那位坐在父親戰友兒子身邊的皇家花園的朱總,仿佛對父親戰友的兒子有說不完的話,每當他一手遮嘴巴對父親戰友的兒子耳邊悄悄私語時,父親戰友的兒子就用眼光恰當地向他示意我的存在。好幾次,能看到朱總臉上掠過對我的一絲厭惡。餐后,又坐在父親戰友的兒子的座駕上,我說,這是今生至此吃的最豪華最昂貴也最排場的一頓飯啊!父親戰友的兒子說,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吃的不是飯……說著,他欲言又止,一副無奈的樣子。當下我就想呢,當官比當老百姓難多了,一個什么鳥朱總就能讓父親戰友的兒子這般為難和無奈,感慨難言,若是在省官和京官面前,父親戰友的兒子又該如何是好啊……我只是隨便說說啊。
我說:王胄兄呀,你今天是怎么啦,是不是叫雷聲嚇著了?
王胄說:雷聲怎么會嚇著我呢。
我說:那你就是魔幻轉移了你和我。
王胄說:你說什么?
我說:認識那個什么朱總的恰恰是你自己。是你曾經告訴我們說,你今生至此吃的最豪華最昂貴最排場的一頓飯,就是一個叫朱總的人請的。難道你失去記憶了不成?
電話那端半天才傳來王胄的聲音,他抱歉地說:你看你看,我怎么暈成這個樣子,抱歉抱歉。唉,都是下午讓那個朱總給氣的,把自己都顛倒成不是自己了。
王胄租房居住已經好多年了。上個月才在皇家花園小區購得一個小套房,結果發現公共分攤面積有誤,房屋高度也與出售書上不相符,而且小區內原規劃好的花園也蓋上物業辦公小樓。王胄和部分購房者便去找皇家花園開發商理論,可找了半個月都找不到開發商,惹得購房者義憤填膺。很快,這件事被市電視臺社會焦點欄目記者得知,馬上扛著攝像機跑到皇家花園。在一群購房者中,由于王胄年齡適中,形象端莊,且說起話來層次分明,條理清晰,百分之六十的鏡頭給了他。焦點欄目播出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也就今天下午,開發商朱總讓人找到王胄,并單獨會見了他。王胄沒想到開發商就是朱總,朱總更不記得他是何人。朱總一開口兩個條件任王胄選取其一:一是開發公司免費為王胄裝潢房屋;二是為王胄每平方米降價三百元。目的是要王胄從此閉嘴。王胄不接受,只要求退還購房全款。朱總轉臉離去,丟下一句話:絕不可能。回到出租房屋里,王胄讓小莉炒兩個菜,悶頭喝了半斤酒。剛喝完酒,天就黑了,然后就下起了這年夏天最強最大的一場暴雨……酒后又惱又氣,亂了記憶,錯了對象。
后來,我曾開玩笑說:王胄兄呀,當時你應該提示一下那位朱總。王胄說:提示他什么?我說:提示他是他請客,你才得以吃了你今生至此吃的最豪華最昂貴最排場的一頓飯呀。王胄說:荒唐,吃那頓飯是一種恥辱!
我曾經不止一次想,對于那頓飯,王胄可能的確感受到是一種恥辱,并有意想淡忘掉。否則,他也不至于把自己都忘掉,移花接木,錯亂于我身上。有朋友聽說這件事后說,莫非王胄兄真的老了?
雖然王胄在我們這個朋友圈里年齡最大,但在我看來,王胄并不老。人老不老,絕不能僅看年齡和身體狀況,重要的是看心態,當然還要看思維方式,反應敏捷程度,以及思想和觀念。
王胄說:什么事不能一概而論,我只是隨便說說啊。其實判斷一個人老與不老,并不需要你說的那些條件,只要看他排放小便的揚程高度就行了,當然了,人過五十就沒什么揚程了,那就要看排放小便的力度,大則不算老,小則真就老矣。說到我自己,確實是老了,確實是老了,我自己清楚的。我隨便說說啊。
盡管王胄說自己確實老了,但我仍堅持認為他并不老。
時間不遠,幾年前的事。王胄背著小莉擅自花了一千多塊錢買輛山地自行車,隨之又花了一千多塊錢,購置了服裝、鞋子、帽子、眼鏡、腰包、水壺等一套戶外用品,打算逢雙休日跟著一幫驢友去山間野外呼吸新鮮空氣。沒想,剛參加兩次就被小莉發現了。小莉看見王胄跟在一幫二三十歲的青年男女驢友后面,是那么顯眼又不協調,跑步追上王胄,并一把把他拽住。小莉說,你是誰呀?王胄咧嘴笑笑。小莉又說,你二十歲還是三十歲呀?王胄仍咧嘴笑笑。小莉接著說,你也不看看像你這個年齡的人誰還干這事呀?王胄不好意思地說,我強身健體還不是為了你嘛。小莉說,我不要你的強身健體,我要你的命!王胄說,生命在于運動嘛。小莉似乎失去了耐心,轉身就走。于是,王胄慌了,調過車頭緊追上去。
我認識王胄時,他才四十多歲。身材修長,言談微中,舉止端正,風度儒雅,看上去甚是年輕。那時候,人們見面相聚談論最多的是改革,因為改革關系著每個人的許多方面。王胄在糧食局做檔案管理員,輪到他說話時,他就不免談到糧食系統的改革。具體到改革細節他倒沒怎么多說,只簡單地說糧站讓私人承包了,糧站不再以買糧食為主了,糧食系統職工失寵了。他著重談了對改革宏觀上的認識,讓我們聽出別有見地。記得一次他說,我只是隨便說說啊。為什么國家要改革,眾所周知,改才能生變,革才能出新。歷史告訴我們不改革就不能前進,實踐告訴我們強國富民先決條件是堅持改革堅持發展。但是,怎么改?怎樣革?有些改革完全可以如中央領導說的那樣,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只有膽子大步子快,改革的成效才更為突顯,讓國家受益,讓老百姓得利。對有些改革呢,就不能太急,欲速則不達嘛,必須要穩定,要科學,要合乎世事情理,要堅持中國特色。對這些不能一味強調速度的改革,有一比喻,就好比一個人要去一個目的地,他可以選擇走著去,也可以選擇跑著去。如果他選擇走著去,當然要多費一點時間,但他途中不會感到疲勞,會輕松到達目的地,而且到達目的地也無須休息,可以接著繼續做他要做的事。如果他選擇跑著去,人在快速奔跑中帶起的風會很大,迎面之風可能就會吹亂他的頭發,吹酸他的眼睛,吹糙他的臉,雖然他會很快到達目的地,但他準會汗濕衣背,會氣喘吁吁,會腿腳熱脹,當然也就會停下來做一番休息。可見速度有其弊也有其利,關鍵是如何選擇。所以說,對改革的復雜性、艱難性必須要認真對待……我只是隨便說說啊。
朋友們都說王胄很有理論水平。王胄說談不上什么水平,我只是隨便說說嘛。我說你要是認真地說呢?王胄笑笑,沖我會意地搖搖頭。分別時,王胄悄悄對我說,改天我們單獨閑聊閑聊。我以為他還會和我談改革,就說改革的話題太大了。他馬上說,改革不是國家的唯一大事,也不是你我生活的唯一話題吧?我不能不點點頭。
說實話,這時候因為我和王胄剛認識不久,對他并不是多么了解,而且我也沒想過要去對他加深了解,僅僅視他為一個普通朋友而已。我一直認為,朋友可以多,但不需要人人都成為知己。所以,多年以來,直至今天,我和王胄仍保持著一種不遠不近,不薄不厚的關系。
我第一次和王胄單獨閑聊是在一個酷熱難耐的下午。因為我所在的單位經費困難,因為我身無職務,所以辦公室沒能安裝空調。一臺破吊扇高速也是低速,低速也是低速,連彈落在桌上的煙灰都吹不動,可想人坐在里邊的滋味了。同事是個年齡稍大、體態稍胖的女士,胸罩都濕透了,躁怒地說,奶奶的,不上這個班了,回家。我想我不能像她不敬業,仍堅持坐著。可坐著坐著,我也坐不住了,就想我也不敬業一回吧。出了辦公室,剛走到街邊,迎面碰上王胄。王胄問我大熱的天干嗎去。我說找不熱的地方呀。王胄說去我辦公室坐坐吧,正好我們可以單獨聊聊。我問有空調嗎?他說怎么會沒空調呢?我說你不是說你們糧食系統現在的日子舉步維艱嗎?他說那是基層和農村糧站。我說原來我忘記你們是市局了。王胄笑笑說,聽你說話便知你是個很有趣的人。
然而,沒想到王胄自己是個更有趣的人。他的有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有趣,讓我只能品味,不能解讀。
畢竟是個市局,王胄自己獨享一間辦公室。屋內似乎有些雜亂,仔細一看,亂就亂在報紙、雜志和資料堆放得很亂。兩幅不同書體的書法作品掛在左右墻上,左邊是草書“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右邊是行書“風住塵香花已盡,物是人非事事休”。
接過他遞給我的茶杯,我說:王胄兄你可謂是一只眼里田園景,一只眼里萬事休啊。
在不進位加法和進位加法的口算測試中,各年級被測所用時間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如表1所示.為了便于分.析,分別以add11、add12、jadd11、jadd12表示“一位數加一位數”、“一位數加兩位數不進位加法”、“一位數加一位數進位加法”和“一位數加兩位數進位加法”.
他謙遜地笑笑,說:讓你見笑了,見笑了。然后,喝了口水,問我:想必你老弟也喜歡這二人?
我說:不敢說喜歡,不討厭。
他似乎來了興趣,說:好好,你能說出個不討厭,可見老弟凡而非凡呀。
我自嘲說:還不煩呢,都燥了,要不怎么跑到你這來乘涼了。
他說:兩碼事。燥可以,但不能躁。其實你老弟心里淡然平靜得很呢。
我說:你不也是嘛,不然,陶李兩家,一男一女,詩詞風格迥異,而且一個重詩,一個偏詞,也不會同時被你請在左右兩邊陪老兄坐班呀。
他絲毫不在意我的調侃,不容置疑地說:不不。我只是隨便說說啊。如你所說,陶李二人風格迥異,這在表象和形式上是存在著的。大凡文學之天才,都具備個人的創造力,一般不甘徒摹他人。又因每個人所處時代和環境各有其情趣風習,形式上不能盡同,這就是古今常說的一人一詩,可見一人之心。但是,縱觀他們的作品,其思想內涵,反映時代景象的宗旨,大致可以說是相通的,而相通亦可達到相同。我只是隨便說說啊。
他談興似乎剛剛進入境界,點根煙繼續說:我只是隨便說說啊。先說陶淵明,我們都承認田園生活是他詩的主題,但在年少時期,包括青年時期,這種主題是尚未確定的。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影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他是抱著“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大志,是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的。但是,時代沒能成就他。于是,他就拋棄了時代,不為五斗米折腰,在絕望中,賦《歸去來兮辭》,不再與世俗同流合污,與統治階級決裂,選擇了實踐“性本愛江山”的志趣,走向田園,走向桃花源……再說李清照,自不必說,愁是她作品的主題。三十歲之前,可以說李清照是不知愁滋味的,盡管她寫過“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等諸多作品,但那僅是對趙明誠相思相念中的一份寂寞,一份苦楚,如果說是愁,也只能說是一種幸福的情愁,并非思想和靈魂深處的愁。真正的愁是遭受到困難、逃亡、被丟棄、被欺騙一番苦難的經歷之后,深深品嘗了苦難和艱難,她愁的主題才得以形成和發展。客觀地說,從開始的情愁到家破人亡的家愁,再到江山淪陷的國愁,這紛繁的愁緒令她一步步地走上一種高度,再走向人生的終點,真乃萬古愁心啊……我們回頭看看陶李二人的人生經歷,不難發現有著許多相同之處。人生的軌跡,其實也就是他們創作的軌跡。陶淵明并非早年就一心憧憬世外田園的,李清照也沒想過自己會愁傷一生。這樣說吧,陶淵明酣酒自醉也好,李清照殫精竭慮實現著丈夫未完之愿也罷,他們晚年的人生,總歸是一樣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失意多舛伴一生,自古文人命相同……扯遠了,只是隨便說說啊。還望你老弟賜教。
然后,他兩手托腮,專注地盯著我。雖然一臉謙恭,但仍遮蓋不住勃勃興致,等待聽我如何對陶李兩人的評述。沒想到我的開口讓他倏然散去臉上的謙恭和勃勃興致,他搖了搖頭,頹然失神,仰靠在椅背上半天無語。
我說:想必王胄兄當年讀大學時,定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呀。
半天無語之后,他面無表情地問我:你怎么認為我就是讀的中文呢?
我說:難道不是嗎?
他說:非但不是,且無關聯。
我說:讓我猜猜你應該學的什么?
他無趣地笑笑,說:別猜了,你猜不到。
我問:那你學的什么專業?
他說:獸醫學。
我問:怎么改行了?
他說:因為害怕。
我問:害怕什么。
他說:牲畜。
我終年一貫不笑的臉上,嘴角突然被兩腮牽扯得幾分生疼。少頃,我自感失禮,便說:老兄你真會開玩笑。
他說:不是我開玩笑,是命運開了我的玩笑。
隨后,在得知他的家族歷史片斷后,我想,被命運開玩笑的何止他自己呢?又想,人生的境遇和經歷難道也會遺傳嗎?自然是不會的。不會遺傳,聽起來,就顯得多少有點耐人尋味。
講述自己家族歷史興致和談趣,遠遠沒有他說起陶李兩人那么強烈和濃厚。靠在椅背上的王胄似乎有些漫不經心地說:只是隨便說說啊。從哪談起呢?就從我爺爺那代說吧。你知道的,過去我們淮城不叫淮城,叫淮縣。我爺爺是淮縣最早一批加入國民黨黨員的三個人之中的一個。入了國民黨后不久,他的抱負和理想突然大了,認為淮縣城小地偏,不能施展他為黨國效忠的抱負,于是就南下去了南京。沒承想,連長江都沒過去,就被駐守在浦口的一支軍隊強行拉去變成了一名軍人。握筆的手總歸不習慣握槍,兩年后,他又回到淮縣,老老實實在縣城國立小學當名校長。我父親十九歲那年,突然從師范學校回到家中與我爺爺道別。爺爺問他要干什么去。父親說他要去革命。爺爺說你要革命就先革我的命。父親說我不能革你的命,今后有人會革你的命。后來爺爺真的就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革了命。淮海戰役打響前夜,父親順便回家看看,趴在爺爺墳上泣不成聲,天亮時才離去。1950年,父親回到淮縣就任新中國淮縣第一任縣長,一干便是十幾年。1966年秋天,從十九歲就開始干革命的父親,被一批沒超過十九歲的革命小將批斗至昏,醒來后迷迷糊糊跳進一口千年古井里,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革命……說遠了,說遠了,我只是隨便說說啊。
王胄自己也點了一支煙,接著說:你可能想知道我為什么害怕牲畜是吧?其實原因很簡單。1969年,我下放在趙縣一個叫趙家溝的村莊,那里距淮城八百多公里。站在村口,生產隊長趙老七打量我半天說,乖乖,一個恁么小的學生能干啥呢?干脆你就跟著馬瘸子喂牲口吧。說完,就把我領到生產隊的牛屋里。當時,趙家溝生產隊共有黃牛八頭,驢三頭,馬一匹,分別拴在幾個石槽上。馬瘸子是個木訥的人,晚上睡覺之前,我只聽見他說過兩句話。一句是叫我吃飯,三個字:吃飯吧。一句是叫我睡覺,兩個字:睡吧。當天夜里,起來小便,本來就暗淡的煤油燈,被窗口進來的風吹得忽明忽暗,黑暗中,我竟迷迷糊糊踩到一頭驢的尾巴上。這頭正睡覺的驢馬上站了起來,后腿連甩三下,不僅把我踢倒在地,驢蹄子還狠狠地踩了我的小腿兩下。我疼得咬牙咧嘴,卻不敢哭出聲音。馬瘸子把我扶到床鋪上,然后拿過一根繩鞭,在那頭驢身上足足抽了十幾鞭,抽得那頭驢嗷嗷亂叫。第二天,我就被人抬到生產隊長趙老七家的偏房里,二十多天不能走路。從此,我不僅再沒敢走進過生產隊的牛屋,而且處處遠離牲口,包括一切四條腿的動物,心理上永久落下一種恐懼。這一年,我剛滿十六周歲。……時間到了1976年春天,有一天生產隊長趙老七去公社開會,散會時,無意中聽見公社書記和另一個生產隊長說到推薦知青上大學的事,趙老七就蹲在墻拐角沒走。等開會的人散盡,趙老七站起來就去了公社書記屋里。一進屋,趙老七就說,書記,你咋忘了俺們莊上還有一個小王呀,這個孩子十六歲來俺莊上的,已經待了八年了。其他莊上的知青被推薦上學的,當兵的,都走的差不多了,今年也該讓他走了吧。書記說,他的家庭歷史不好,不能推薦。趙老七說,啥歷史不歷史的,一個爹娘都沒有的孩子還講啥歷史呀?書記說,政策有規定。趙老七說,政策上不是明明白白講叫貧下中農推薦嗎,為啥俺貧下中農真推薦了,又不行呢?書記說,老七,不能這樣理解政策,你雖說是隊長,可也代表不了廣大群眾。趙老七說,那咋樣才能代表?說完,見書記半天回答不上來,轉身開門走了。下午,趙老七又來找書記,進門后從腰里掏出三張紙遞到書記桌子上。書記看看三張紙上滿滿的,有鉛筆寫的名字,有鋼筆寫的名字,更多的是一個個紅手印。趙老七說,這是俺們莊上大人小孩一百一十三口人的名字和手指頭印子,算不算群眾推薦?書記,你開開恩吧,八年了,這孩子一天也從沒離開過俺的莊上,要是再走不掉,叫俺們莊上老少爺們咋有臉跟人家孩子說話呀?書記再沒說話,從抽屜里拿出一張表遞給趙老七。趙老七回到莊上,興奮得像個過年的孩子。他把表遞給我時,我瞟了一眼推薦表,上面寫著一所農校的校名,專業一欄是育種。然后就聽他說,熬出頭了,熬出頭了,晚上,我喊幾個老少爺們兒陪你喝幾盅。錄取通知書下來那天,我發現錄取專業變成了獸醫學。當時容不得我有半點想法,哪有要飯的嫌饃涼的呢?離開趙家溝那天,一個莊上的大人小孩都站在村口送我,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失語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說到這里,王胄突然而止,只見他站起來,緩緩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并站在那里許久沒有轉過臉來。我無法看見他丟給窗外的表情,只看到他的兩肩微微哆嗦,一股熱風吹亂了他的頭發,他雕塑一般的身背遮蔽了我的目光。
重新回到椅子上,他說:畢業那年,正趕上撥亂反正,我才得以回到淮城。十年過去了,淮城幾乎沒什么變化。但是我變了,幾乎沒人認識我。我找到父親生前的一個戰友,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王胄。他不相信地搖搖頭,搖著搖著,就一臉老淚縱橫……我告訴他我不想從事獸醫,我害怕牲畜,其他任何工作都行,只要有碗飯吃。他說那就去糧食局吧。于是,我就去了糧食局。
夏日里的這次單獨閑聊之后,半年多的時間內我再沒見過王胄。
第二年春天的一天,王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要請幾個朋友喝酒,叫我務必參加。電話里能聽出他的聲音有點變聲,是激動的那種微微顫音。沒等我問何故,他便把電話掛了。我打電話問另外一個朋友,朋友說,王胄結婚了,請我們喝喜酒。我愣了愣問,再婚?朋友說,頭婚。我說,這些年委屈他老兄了。朋友說,他自尋的,這些年他一再堅持要找個年齡小的,小的誰愿跟他呢?拖到這個年紀,再小又能怎樣,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王胄的喜酒,嚴格上講稱不上喜酒。包括他和新娘在內,十來個人,只擺了一桌飯。他本人既沒更新衣,新娘也沒扮新裝。看不見喜字,聽不到鞭炮聲,而且沒有喜糖。
新娘叫小莉,相貌一般,但年齡不大,看上去和王胄相差甚遠,三十歲左右的樣子。面含幾分羞澀,適時沖我們笑笑。偶爾說句話,露出外地口音。
席間,輪到我敬他們兩位酒時,我說恭喜并祝賀啊。王胄一手端著酒杯,一手遮著嘴巴,湊在我耳邊小聲說,勉強稱得上娶個小,娶個小。有人就問王胄說什么見不得人的話。王胄說,我說我今后就幸福了。
然而,讓我和朋友們想不到,王胄婚后的第二個月就出事了。被刑拘三個月后,在他父親那位老戰友的兒子運作下,免于判刑,出來后調到糧庫看大門,保住了一份工作。原來,最近幾年,趁糧食市場放開,體制改革之際,王胄多次被他人拉去參與倒賣糧食,非法牟利數百萬元,他個人共計分得非法收入三十萬元。
得知這個消息后,我很是難以理解。于是,隨便問了另外一個和王胄比較親近的朋友。朋友說:誰能理解他老兄呢?知法犯法,冒著坐牢的風險弄個三十萬,自己卻一分也沒享用,全部給了農村一個村莊改建小學,修橋鋪路了。現在好了,退回非法收入,只有把自己的房子賣了。
我問:什么村莊?
朋友說:誰知道叫什么村莊,在趙縣,過去他下放的一個村莊。
我說:噢。
朋友說:你大概還不知道吧,還有讓人不理解的呢,小莉就是那個村莊的。聽說是個老村長的女兒,丈夫生病死了,幾年都沒能改嫁出去。王胄老兄像欠這個村莊什么似的,什么善事都做,跑過去幾趟,非要把她娶了,不就圖個年齡小嘛。你說誰能理解他老兄怎么想的呢?
我說:王胄老兄是不需要人理解的。
說完這句話,我很快覺得我說了句廢話,其實我應該沉默,或者轉移話題。不知為什么,我突然這樣想。
坦率地說,我不是一個很關心朋友的人。對于王胄,由于我和他年齡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另外,我有著自己的幾個知己,所以,多年以來,只保持著不遠不近,不薄不厚的關系。
就說兩年前他購買皇家花園房子一事,從那個暴雨轟響的夜晚,他錯亂打給我電話之后,我好像從沒問過他最終和開發商交涉的結果。當然,這兩年我和他也沒什么交往,見面的次數寥寥。
半個月前,王胄突然打我電話,說有件事求我一定幫忙,并約定我下午四點在市府廣場文苑長廊面談。見面后,我感覺到他好像突然老了許多,戴頂灰色的破氈帽,穿件肥大而且污跡斑斑的風衣,背也駝了,手也抖了,甚至神態變得幾分黯然。他從包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雙手遞了給我。我接過一看,是一本印制粗糙的書籍,上面印著《清風齋閑話》,以及王胄著。我說,你老兄出書了,祝賀祝賀。說著,我翻開封面,只見扉頁上寫著:王胄自存。我馬上說:你老兄也送我一本拜讀呀。
他一手搓著臉,不好意思地說:只印了兩本。
我不解,問:怎么就印兩本,在什么地方印的?
他說:在網上,有個速印網,想印多少都行。考慮到都是些不能示人的拙文,就印兩本,一本我自己玩玩,一本送給趙家溝小學了。接著,他又說,本來自己閑玩的,有天拿給家父那位老戰友的兒子看看,他叫我找人給寫個書評影響影響。他現在調到政協去了,政協有個文史委員會,下面有個雜志,可以刊登一下。所以,我想請你老弟幫忙,勞駕寫篇書評。
我說:實話說吧,王胄老兄,我從不寫書評,因為我寫不了,其他都可以湊乎寫。
他說:要么你就從別的方面寫寫吧。
我說:從哪方面呢?
他想了想說:真不好寫嗎?
我也想了想,說:要不然我就寫寫你這個人吧。
他忙點頭,說:行行,怎么寫都行。
我一邊翻翻手里的《清風齋閑話》,一邊就問:老兄怎么想到為自己出本書了?
他取下頭上的破氈帽,抓了抓頭皮,說:我隨便說說啊,說出來你別見笑。我自年少起,就想做個文人,但并不是陶淵明、李清照還有我爺爺,他們這類的文人。而是“五四”前后,或者說清末民初時期的那種所謂的舊文人。我覺得他們的生存狀態適合我的性情。那時的文人大都有著一種共同的情趣和標簽,或者叫嗜好。就是,起個號,打個轎,刻個稿,娶個小。……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我只是隨便說說啊。
我終年一貫不笑的臉上,不禁又笑了一次。
笑著笑著,我忽然對王胄產生了一種陌生感——站在面前的這個年逾六十的人是誰,是王胄嗎?如果是王胄,那么,王胄又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
這時,王胄說:讓你見笑了。
我片刻才回過神,說:哪能呢。我笑你老兄現在已經全部實現了你所追崇的那種文人境況。你看,號叫清風齋;轎嘛,現在變成了出租車,你可以隨時隨地去打;自己的書也刊印出來了;小嘛,在多年前就娶到手了。你終歸如了意愿呀。
他一邊點頭,一邊說:勉強勉強。
我問:要我怎么寫你呢?
他說:隨便寫寫,隨便寫寫。
我說:好吧,我就隨便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