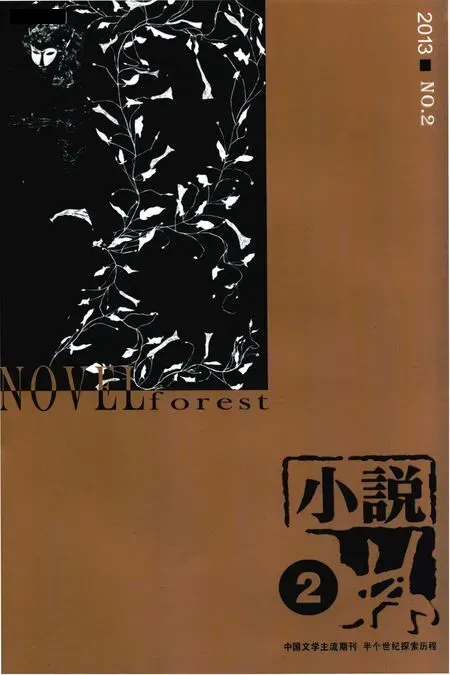向白茶的求知
◎蔣雪孩 蔣耀波
1
2011年5月22日,我寫下了下面這篇名叫《望境中的白茶》的文章——
我一直覺得,安吉白茶首先是一種可以用來“看”的茶。
仔細想來,我“以視覺貫穿嗅覺和味覺”的體驗,亦是從安吉白茶開始的。
雖然我早已有了去親近白茶的愿望,但我與它之間的關系并不熟絡,可能是白茶本身喜靜,便是青澀也將自己表現得出塵而又云淡風輕的緣故吧。這種“性格”難以單純地用“好”或是“不好”來評價,所以我只好如它一般默默,一切順其自然地經由目光的延伸而緩緩進行。
在杯底積了薄薄一層的,是尚未經過沖泡的白茶,透過其嫩綠或草綠的干癟外表,我確定我感到了某種雖輕微卻極確切的蠢蠢欲動,它們正急切地渴望著水的初擁。
此時的水應是有講究的,八十攝氏度到八十五攝氏度是能最好發揮白茶之佳味的區間。而似乎從采茶之時起,白茶便難以脫離“嬌貴”二字了。即便如今白茶的種植、采擷與炒制的技術均已精進,但人們傾注于其中的心力卻仍是不言而喻。白茶的“白”,與制作工藝無關,完全是其自身的特性。初看時,茶葉的芽竟也色如白紙;過段時日,綠色漸次滲透葉脈,而后向側脈擴散。但炒制過后其色又呈現淡綠。不得不說,這個過程就已經可以算是奇景了。
在將熱水傾入茶杯之前,我深深望著手里杯中的細秀茶葉,其羽形玉色并不顯張揚,甚至是略顯清癯的。但我想我與白茶每一次的相遇與注視都是緣分,即便從不深入,只延續已足夠好。
終于,幼嫩的芽葉開始在一片氤氳中隨著水柱的倒入翻騰沉浮,一切落定后只見無數細微的白毫似精靈般躍動著充盈了杯內的各個角落。我忽然想到了印度作家阿蘭達蒂·洛伊的一本小說——《微物之神》。和書的內容無關,僅僅是“微物之神”那四個字罷了。而也就是在那個思索的瞬間,我仿佛從面前未泡開的白茶內發現了猶如未舒展開的神性所在——它會撐破杯子沖出來嗎,我隱隱失笑地這么想著。
我定定地看,看面前的白茶。鼻間有鮮爽的清香悄悄探進,但面前的所有似乎都停留在了某個不甚真實的時刻。其中應是流露出了“畫意”,所以每個即便在活動著的過程也好似變成了一次次單幀的定格。我意欲去那“畫意所在之處”,為何一杯茶能予人如影隨形般的入境之感、一種極易融入的當場構成的姿態?這個疑問本身都莫名其妙,我只得繼續看下去。
在那未曾轉移的凝望中,一個個芽葉漸趨飽滿,芽色在滲透了星點鵝黃的淡綠茶湯中愈顯蒼翠。不如說它們正各自被召喚,逐一賦予生命。若非如此,一葉葉白茶又怎么會似獨舞和雙人舞那樣,于有限的杯中空間內翩躚旋轉并緩緩墜向杯底呢?如果漂浮是為了讓飽滿從頭到腳充斥,那么之后的沉降,象征的應是渴望皈依與安逸實感的誠心吧。
白茶的滋味讓我想起不久前去安吉時遠眺過亦深入其中的竹山。那是一種清朗卻也溫潤的韻味,以玉來比應是最合適的形容之一,但安吉白茶的內涵顯然還會由于“竹”的元素而平添幾分別樣的美。僅從味覺和嗅覺來判斷,獨特的甘甜與潤澤中混合了與眾不同的清冽之感,大段的柔美夾雜著隱隱的蒼勁。存在于一個事物中的矛盾總是讓人備覺誘惑的迷人特質。
白茶適合在任何心境和狀態下飲用,這點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喝畢白茶后,心里不管存了些什么,最后都會隨著沉入杯底的茶葉而變得凈且淡,還會留下幾分安然的欣喜,享受難得純粹的沉迷。而若真心想了解白茶的性格,還需動用除“品”以外的另一種媒介。
觀、瞅、睨、瞥、瞪、瞟、眺、望……它們是各種“變異”的“看”、“不單純”的看。它們之間因距離、位置、情感等諸多因素而互相區分著。但當我面對白茶一杯和竹山一座時,我竟都喜愛用“望”這個字眼。
我知道不管我身在何處、面向何方,眼睛都行走在最前方,亦走得最遠。而我能夠通過眼睛或是心靈望進的又是什么呢?逝去和將要逝去的風景嗎?
若能望見宋徽宗趙佶伏于案前,寫著其《大觀茶論》里的“白茶篇”就好了。“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雖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過四五家,生者不過一二株。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而為常品。須制造精微,運度得宜,則表里昭徹,如玉之在璞,它無與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不及。”
趙佶寫著《大觀茶論》中的文字時,手邊或許也擺著一杯剛沏好的白茶;還可能在茶農采茶制茶的時候,他驅開陪同的侍衛與群臣,獨自饒有興味地站在一旁,時而詢問幾句,而更多的時候都在若有所思。
趙佶一生極盡奢侈,但能詩善書、酷愛藝術,還于他在位時將畫家的地位提至中國歷史上最高處。他更將作畫作為科舉的一種考試方法,以詩為題的做法也在有意無意中激發出了更多的新想法。他最被人熟知的莫過于“踏花歸去馬蹄香”一題。當時博得頭籌的作品是一人騎馬遠去的背影,雖然馬蹄下并無踏碎的花瓣紛飛,但環繞飛于馬蹄周圍的各色彩蝶已能說明一切。如此試題創意和情趣兼具,考驗了應試者對題目主題思想的理解是否深刻,表現力與畫功幾乎都排在其次了。趙佶能將“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為工”作為評價一幅作品成功與否的標準,其藝術上的造詣可見一斑。
宋徽宗得意于收復燕京、藝術造詣很高;卻最終失意在被金人所俘,畫作被擄,身心受盡折辱,客死他鄉。趙佶曾在被囚禁且不久于人世前寫下這樣的詩句:“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
他逝去前的目光,是在遙望故鄉的嗎,那個他肉身終究無法到達、靈魂卻在尋找的過程中迷失了方向的遠方?我倒是希望他的靈魂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各種畫作中去,畢竟那里埋藏著的是他曾守望過的夢想。
遠望漫山的翠竹,它們離我百米之遙,但只要目光到達,我們之間就沒有距離;近望簇擁的白茶,我卻只得執拗地去尋找某些我已感覺到、但又看不到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心靈是隨視覺而舒展的。一個望”字,不只是眼睛的移動,更是心靈的動作,既有綜覽、又有集中,那之中更孕育著我們所追求的超越與自由。
若能望見竹海深處的“茶圣”陸羽白衫飄逸的身影就更好了——說茶寫茶,怎么繞得過陸羽這棵“母樹”呢?
安吉東北方向不遠處的湖州市妙西鎮杼山,是陸羽在塵世的最后一個也是停留時間最長的歇腳之處。天寶末年,陸羽為躲避安史之亂,一路輾轉到湖州。陶淵明在《歸園田居·其一》中有“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的詩句,陸羽在其第二故鄉湖州生活的日子也持續了三十余年。其間傾注了陸羽畢生心力的三卷十章、全文七千余字的《茶經》亦是在三易其稿之后于湖州完成的。陸羽享年七十一歲,去世后安葬于杼山。
陸羽一生鄙權貴、輕財富,《全唐詩》里更有對其“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的描述。只有這樣的人,才更容易深入無人之境,沉浸在以茶為名的自然的懷抱之中。
陸羽陸鴻漸之名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姓,羽為名,鴻漸而為字。
看到了嗎?一只白色的大鳥收起了羽翼,像白鷺又像是白鸛,停在望山觀茶并賞竹的時日里,于竹林和白茶香氣的環繞間陶醉著,流連忘返,再不遠離。
我喜歡竹的翠色,它清明而透澈,在放松觀者感官的同時,更帶來了對萬物生機的莊重確認感。“望”亦是“問”,是“探”,對人、對己、對物、對人生。人們從來愛把問題拋給無言之物,待它們不言自明。跟從愿望的腳步,萬物仿佛在不停生長。只要愿意,它們就可以從腳下涌起,再向進一步的遠點緩慢而堅定地鋪陳開去。
白茶是睿智的,它自己首先在沖泡的過程中放慢動作,繼而讓關注著它的我也有機會停下來,先用心靈與眼睛探路,再開啟一段新的前行,一段經過“增殖”的旅行。我似乎又回到了沖著鏡頭笑的那個時候,背景是那片似不曾變過的竹山;我轉過身去,目光掠過陽光與陰霾,遠望之遠處即是天。心靈的天性和氣質都在那里,充滿不必用任何言語標榜的坦然和自由。
“望境”這個詞在各種地方已出現多次,但它用在這里顯然還是很合適。應該是所謂的“山”和“茶”在“望”和“被望”中給了我自然與心的新啟示吧。
中國古代畫學中有所謂的“三遠”之說,“高遠”者,從山中看山壑,觀山高,此上下關系;“深遠”者,從前山看后山,窺山背之景,此前后關系;“平遠”者,從近山觀遠山,望遠景,此遠近關系,亦代表了溯望、俯望、瞻望三種姿態。據說,望境就藏在這些“遠境”中,更有著向往遠方的意味。
我想象中的望境在某種程度上出自距離,心望得悠遠、心處得曠達便好了。這種遙遠更像內里的延伸,即使外表不動聲色。就像“望”可以奠定一個人視界和思想的高度,但很明顯你并不用長那么“高”。
有意思的是,人們總是借“望”來表達某些期盼之情,而不必把什么都說出口。
一天,我翻看著自己從兒時到現在的各種相冊,偶然又發現了那片翠綠的遠山。合上相冊時,我的手邊正好放了一杯剛沖泡沒多久的白茶。
同以往一樣,我默默望著它。而這如此熟悉的每一次,又都像我們初次見面的場景。
是需要我去遙望的時日漸緩了嗎?
2
老蔣2004年去了安吉,接待他的是安吉縣的領導們。
屋內相聚時席間觥籌交錯、人聲酒影;屋外考察時襯著群碧相應的青山翠竹,進到百姓家里去亦別有一番風味。
離開安吉之前,老蔣特地把安吉縣環保局的一位徐姓局長叫到了一邊,在留下自己家庭住址的同時還拿出了三千塊錢,名曰“茶資”。
“我們有禮物送的。”那個人不好意思地推托著。
老蔣早料到會收到如此的回應,笑道:“知道有禮物,但肯定沒有那么‘多’,也不會有那么‘好’。”
兩人這時相視而笑,老蔣接著說:“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好的白茶的‘標準’。”
老蔣的安吉之行結束得有些匆匆,但從那以后,每年都有上好的白茶從安吉寄到家里,就像某種美好的延續。
老蔣在許多場合都不止一次地提及到“標準”這個詞。
什么是標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目的”——從這個目的里衍生出的就是“與其他事物區別”的規則,亦是用來判定“處于此范疇之下的事物好不好”的依據。可以說,一個人對某物某事乃至為人處世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位置和視野——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喝好茶,讀經典”。
對于“經典”的“標準”是什么,必須要做到心中有數。比如一包好茶,作為標準,它一定是某種“特殊”的東西,擁有獨有的形狀,獨到的色澤,獨特的味道。
但很多時候,“標準”的概念都是模糊難尋的,它本身就如同一個寶藏,人們猛然投身進入時并不知道哪一塊才是最有價值的,所以只得在用心記取原樣生活的同時通過各種各樣的體驗來豐富自我。源源不絕的學問和規律,從來都和生活一樣活潑,所謂“標準”的“標準”也在這里。
老蔣特別強調“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講與國家主權密切相關”的觀點——在全球規則確立的過程中,中國不僅要有發言權、話語權,還要有“霸權”。這“霸權”就是在規則的制定上擁有自己的并為別人所共同遵循的“標準”。這些話我聽著有點“大”,我一時不十分清楚,還是留給他自己去進一步展開好了。
3
一年前寫下的《望境中的白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讓我頗為自得。倒不是覺得自己寫得有多么“好”,主要原因還是覺得那種能通過寫一篇文章而認識一種茶的體驗使我深感滿足。
現在的時間點已經在《望境中的白茶》的基礎上加了一年多,而很多事的發生幾乎都是不顧時間的機緣巧合。最近老蔣的朋友才送來一泡上乘地道的福鼎老白茶,產于2007年。據說福鼎白茶才是“白茶之源”;而在喝到這款茶之前,我對福鼎基本上是完全陌生的。
小小的紫砂罐子里鋪滿了因滿身白毫而顯出灰湖綠色的茶葉,一根根體態完整、健壯而飽滿。這款已歷經千余天時間洗禮的茶的外形和它的名字“白毫銀針”倒是十分般配,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它交流一番。
剛燒開的水冒著蒸氣,需要靜待一會兒,不那么沸騰了,才有資格同杯底的白茶接觸。
老白茶的顏色青中微褐,就連茶湯也是這個樣子。它的香味并不是特別濃郁,或許是把氣質靜靜隱藏在歷史的身側以至于常人不可得見的緣故吧。一根根茶葉在水的浸泡下脫卻了絨毛,逐漸飽脹的樣子終于讓它過分沉郁的外形多了幾分鮮活。
茶湯慢慢滑進口里,帶著某種莫名纏綿悱惻的滋味,或者說那即是縱是我思考到脫力也難得接近的歲月——但若真是那么不可揣度,又何以想此時此刻那樣無比接近?
“怎么樣?”老蔣也泡了一杯,問我的時候表情好像也受到了杯中茶的影響有些深不可測。
“味道很奇特,不如說……有點兒奇怪。”
這泡白茶十分正宗是事實,但我還是說出了最直接的感受。說不出是“落差”還是什么,可能這就是人們太過于偏重“改良”的結果吧——的確在或多或少的改變中迎合了大多數人的口味,但某種更為重要的、足以成為支撐之骨骼或靈魂的東西,反而被弱化了。
目前市場上有很多冠以“白茶”之名的茶葉,其絕大部分是不屬于白茶類的白茶,真實身份是“白葉茶”,它們的加工工藝屬于綠茶類,選用的是白葉茶品種的芽葉,經過殺青、造形加工制作而成——包括安吉白茶,這種浙江名茶的后起之秀,同樣是在這樣的工序下完成的。
所以一年前的那篇《望境中的白茶》,倒真的像是經過我進一步“藝術加工”的“白茶”,可能大多人眼里的白茶也是這樣。美是足夠美了,但并不能夠作為可以因此而“不清不楚”、“似是而非”的借口。
在對待福鼎白茶的態度上,老蔣提出這么兩個詞:“扶正固本”和“正本清源”。
“扶正固本”,原意指中醫治病的主要治則之一。扶正就是扶助正氣;固本就是調護人體抗病之本。通過“扶正固本”以促進生理機能的恢復,以達到正復邪退治療疾病的目的。
“正本清源”是個和“改革”息息相關的詞語,意表從源頭上清理、從根本上整頓。早在班固的《漢書·刑法志》中就出現過;到了近代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論中國改革之難》中,也有“于此而欲為正本清源之法,則唯有力行精神教育之一策”的句子。
老蔣把它們列出來,也就給了我一個“方法論”。對于身為“白茶之源”的福鼎和福鼎白茶的陌生讓我深感羞愧,但同時我也很慶幸。既然明白了“源”在哪里,“循源而行”就好了;而我通過接下來將對福鼎和其白茶的研究,又能掃清一個知識的盲點。
4
人們把在聯合國的所有會議、官方文件,以及有關記錄、事務中可以使用的語言稱為“聯合國工作語言”。在此范疇下的語言有六種:漢語、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
聯合國工作語言選定的主要根據為該語種的影響力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通用程度,所以首先應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國,即英、美、法、俄和中國所使用的語言。由于西班牙在十五十六世紀的強力殖民擴張,主要分布于歐洲、美洲和非洲的不少國家都用其作為官方語言,所以西班牙語也入選了這一語言團體。1973年時,鑒于阿拉伯語在中東以及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廣泛影響力,阿拉伯語也被確立為聯合國工作語言。
茶也有自己獨特的“語言”。現代的中國茶大致可以概括為兩類:基本茶類和再加工茶類。而我們更為熟悉的,則是“六大茶種”的分類,即綠茶、白茶、黃茶、青茶,黑茶和紅茶。在茶葉的加工中,新鮮茶葉都是需要經過酶化的,如果按照各種茶的茶多酚氧化聚合程度進行劃分,由淺入深就出現了以上的六種,也就是茶葉的“六大語言”了。
我們在茶葉店總能見到令人眼花繚亂的茶葉名稱,其實這種多樣化是各種產茶地及茶商刻意造成的:有的根據茶葉形狀的不同而命名、有的則結合產地的山川名勝來取名、更有茶的命名是根據傳說和歷史故事而成,大紅袍、鐵觀音就是最好的例子。
雖然茶葉的分類標準有顏色、發酵程度、采茶季節、萎凋程度等多種,但它們之間的共通的本質都是沒有變的。
“如此說來,碧螺春、普洱、毛蟹等等都可以算是‘茶語言’里的‘方言’了。”老蔣笑稱。
越是這樣,我才越發現白茶是最不能繞開的,它自成一種顏色,有亟待被人探尋與了解的知識和故事,
“可以叫不出名字、辨不出味道,但萬萬不能‘黑白不分’。”
5
福鼎依山傍海,福鼎白茶就是在優美風光的滋養培育之下自由生長的。
福鼎白茶產于福鼎太姥山,陸羽《茶經》中所記載的“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福鼎太姥山。
太姥山位于福建省東北部,挺立于東海之濱,三面臨海,一面背山。北望雁蕩,西眺武夷,三者成鼎足之勢。太姥山上的巖石為粗粒花崗巖,屬地質史距今約九千萬年至一億年的中生代白堊紀的產物。由于地殼的變動,海洋上升,東西南北與近水平三組互相垂直的向節理發育,形成了太姥山一條條縱橫交錯的峭壁、山峰、山洞。又經千百萬年的風雨剝蝕,流水沖刷,慢慢形成了今天突兀的奇峰怪石。
太姥眾峰有“云橫斷壁千層險”的奇譽,太姥中高度由五百米到九百米之間的山峰眾多,其中奇險者甚多,但總有人為在險處探勝而摸索進山,畢竟那極目千里、氣象萬千的絕美風光足以讓人忘卻一切繁亂瑣事,投身到山景碧空的懷抱中去——其中覆鼎峰因狀如覆鼎故得此名,更有意思的是福鼎縣名也由此而來。
鐘靈毓秀的太姥山孕育出的正是福鼎聞名遐邇的優良茶種——福鼎大白茶,其芽葉上披滿白茸毛,是制茶的上好原料。由于人們采摘了細嫩、葉背多白茸毛的芽葉,加工時不經殺青或揉捻,直接萎凋曬干或用溫火烘干,使白茸毛在茶的外表完整地保留下來,使得茶葉呈現出純凈的白色。福鼎白茶屬輕微發酵,其生產已有二百年左右的歷史,由于最早由福鼎首創,因此又稱福鼎白茶。
宋人沈括亦在《夢溪筆談》中稱南方茶樹“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余”,現在想來應該說的就是生于福鼎大白茶樹上的白毫銀針——芽頭肥壯,挺直如針,遍葉白毫,一眼望去光澤如雪,甚是動人。
白毫銀針因產地和茶樹品種不同,所謂銀針”分南路和北路,所謂“北路銀針”便產于福鼎。白毫銀針具有外形優美,芽頭壯實,毫毛厚密,富有光澤,湯色碧黃等特點。
雖然白茶、紅茶和綠茶的發源地都在福建,但白茶對產地的“依賴性”使得其一直對福建“情有獨鐘”。
常有人認為白茶論清爽不及綠茶,論醇香不比烏龍,這也是為什么白茶的飲用人群不如前幾大類茶廣泛,但白茶的真正價值并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白茶入藥極好,根據民間長期飲用和實踐及現代科學研究證實,白茶具有解酒醒酒、清熱潤肺、平肝益血、消炎解毒、降壓減脂、消除疲勞等功效,尤其針對煙酒過度、油膩過多、肝火過旺引起的身體不適、消化功能障礙等癥,具有獨特的保健作用,在國際享有極高的口碑,可謂“墻里開花墻外香”。
福鼎白茶品種繁多,“白牡丹”亦為上品。白毫銀針采自大白茶樹的肥芽,而白牡丹則取大白茶樹短小芽葉新梢的兩葉一芽,而因形似花朵而得“牡丹”之芳名。此外貢眉”、“壽眉”等品種的存在也使得福鼎白茶的品種日益齊全,不負“白茶之源”的盛名。
福鼎市始于乾隆年間,距今已有將近三百年歷史,是閩越和甌越文化的發源地之一。由于中原文化傳入較早,故自秦漢以來,福鼎所在的區域在閩浙地區已經逐漸開始構筑起多元的文化體系——道、佛,儒教和具地方特色的畬族文化共同發展。
真應該找哪個暑假去福鼎看看,賞太姥、品白茶。我看過不少太姥山的照片,它常與陽光一同出現,所以更顯得明亮而寧靜。極目遠眺可以望見安然卻也不那么安分的城鎮;遠處是湛藍的大海和零零星星的寂寞小島。細細軟軟的云飄浮在晴空之上,隱約可以從山林間看見古剎寺廟的輪廓,或許沾著露水的晨鐘聲也會蕩漾出古舊但輕靈的調子。
很多地方在尚不能馬上去親眼觀看或親手觸碰時,只能通過某些媒介,進行自欺欺人卻也更自得其樂的深交——有時僅經過了這一個步驟,你竟已經開始了依戀,好似認識已久;待到真正見面時,說的第一句話卻是“好久不見”。
于是我只好慶幸一件事:不論哪里的“白茶”,倒是都生在了好地方。
6
還是聽聽杯中白茶的傾訴吧,不論遠山、竹海,城市還是別的什么,都幻化成芽葉上的那一根根細密的絨毛,最終它溶在水里進入你的心靈和腦海,帶動著你去靠近它的力量簡直可以被稱作“慣性”——因為你發現自己對一個事實再清楚不過:不管是你需要的還是你應該得到的,它全部都會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