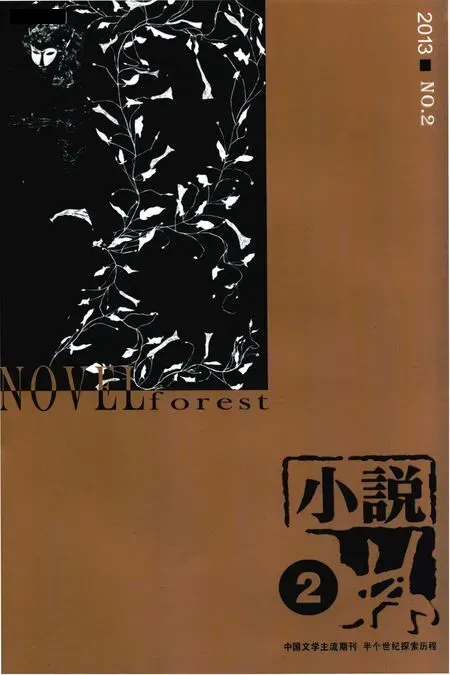開電梯的人
◎王先佑
1
小桂所在的位置,剛好對著大梅沙的海濱浴場。從透明玻璃望出去,海灘上擠滿了一個個活動肉團,像是海量水餃,正處于下鍋之前的興奮中。廚師也許是位畫家,包餃子之前,他可能剛剛才丟下畫筆,手上還遺留著五彩的顏料。太陽離海面約摸還有一丈高,陽光已經沒有了正午時分的那種驕橫跋扈,虛弱得像是床上剛泄過的男人——陽光無力地從半空里掉下來,掉到海面、沙灘、椰子樹以及酒店門前的馬路上,讓小桂記起了余暉脈脈、波光粼粼之類的詞語。他按下電鈕,海濱浴場在眼前移動起來。
電梯里的空間夠大。小桂對面的墻上掛著三口鐘。中間那口鐘,時針過了六點,分針指在二十的位置——這間酒店的鐘真他媽多,大堂前臺掛了五六口,除了北京時間,還分別顯示紐約時間、東京時間、巴黎時間、開羅時間還有什么時間。休息區、餐廳,也都至少有兩口以上的鐘,連大堂的洗手間都有鐘。小桂想,搞這么多鐘,有病呀?來這樣的地方,住這樣的酒店,不是來消遣,就是來燒錢,不用那樣分秒必爭,連拉泡屎都得算計著時間吧?真他媽窩心。
確實,只有那種腦袋灌進了大梅沙海水的人才會真正把這樣的培訓當成一回事。十多天前,在看到松松垮垮的培訓日程時,小桂就這樣想過。那個時候,他從臺灣回來沒多久,還不知道誰將會去大梅沙,但他幾乎可以確定他不會有這樣的機會,因為他剛剛跟著一個優秀員工旅行團去過臺灣。老板對他說過,能夠跟團去臺灣,是一份天大的福利——既然是福利,那就沒道理所有的好處都被他一個人獨占。否則,即使上帝點頭了,老板也不能同意。如果不能做到哪怕是表面上的公平,老板以后還怎么安排人干活?小桂想。
小桂眼里的老板,其實只是他們編輯部的總編。這個總編的名頭,多少有些唬人的成分。一份企業內部報紙,每周一期,編輯記者全部加起來,也不超過二十個。在需要介紹老板的場合,小桂每次說出總編這兩個字,心里就暗暗發笑,覺得自己是在拉大旗作虎皮,但,總編這個名號,讓小桂覺得自己臉上多少也有些光彩,而老板對這樣的稱呼似乎很受用——既然老板都不說什么,小桂當然懶得去認真。在編輯部,大家只認總編,不認老總。公司太大了,老總離他們太遠了,遠得好像只是一個虛擬的符號。
小桂不知道老板怎么想的,反正在接到協會通知的第二天,老板就把他叫到總編室,告訴他,今年上面批得嚴,這次參加培訓的名額只有一個,他留給小桂了。小桂有些意外,他控制住了喜悅,充分表達出了吃驚。這……有些不大好吧?小桂說,語氣里流露出忐忑,還有替老板分憂的意思。有什么不好的?你是首席記者,該照顧的時候,我自然會照顧你。好吧,就這樣,好好放松幾天。老板最后這句話有點像催淚彈,正好扔在了小桂的敏感部位。他鼻腔有點發酸,低著頭,輕輕帶上了門。
參加這種培訓,公司當然得交錢。小桂記得,去年的培訓,有兩個同事參加。那個時候,小桂剛剛調過來,這樣的好事自然輪不到他。去年是每人一千,今年就變成兩千了,培訓費漲得比酒店的電梯還快。費用雖然漲了,去的人還是兩個——這點錢,對小桂所在的公司來說,連九頭牛身上的一根毛都算不上。小桂還是臨出發前才知道參訓名額變成兩個的。他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也許是上面改了主意,多批了一個;也許是老板又額外申請了一個。和小桂一起來的是小北,小桂屬龍,小北比他整整小一輪,也屬龍。臨出發時,辦公室有人說他倆是雙龍赴會,小北看上去挺開心,小桂卻高興不起來。
2
小桂一直想不通,老板怎么會讓小北也去參加這次培訓。在小桂眼里,小北不過就是個打醬油的角色。辦公室有兩位專職攝影記者,小北是其中之一。在編輯部,所謂的專職攝影記者,還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除了攝影,別的基本不會,而編輯部有很多同事的拍照水平在他倆之上。這樣,小北他們便多少有點顯得可有可無。這樣說也許有些夸張,因為編輯部是采編一體制,其他同事既是記者又是編輯,偶爾客串一下攝影還可以,但要是遇上大型活動就有些抽不開身。此外,小北他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陪老板打斯諾克。編輯部里有三個閑人,最閑的是老板,此外便是小北他們兩個。閑得蛋疼時,哪怕是在上班時間,老板也會帶上他們當中的一個,直奔球館而去。黑格爾說,存在就是合理,說的就是小北。
攝影記者小北沒少挨老板的訓。老板一直對他們的作品不太滿意。公司內部有好幾家媒體,除了報紙,還有雜志、電視、廣播,以及好幾個網站。平時,大家各做各的策劃,各搞各的選題,看上去像是大路朝天各管一邊,暗地里卻都憋了一股勁兒,總想爭個高下。公司的大型活動,他們都是有報道任務的,同樣的報道,誰能做得更出彩,當然得看誰更有料。在這樣的戰事中,有小桂撐著,文字報道老板一點兒也不擔心,他擔心的是攝影圖片。那一次周杰倫來公司搞義演,動靜弄得很大。活動結束,文字稿出來了,寫得牛氣沖天,但老板把兩位攝影記者的圖片庫翻了個底朝天,愣是挑不出一張能上頭版的大照片。實在沒有辦法,老板只能低聲下氣向雜志那邊求援。事后,老板在辦公室指著小北的鼻子,說,你們的相機配置這么高,電腦配置這么高,大腦的配置能不能提高點,嗯?
小桂不高興,并不是因為小北。把小北換成任何其他人,他都會不大高興。說白了,是他不希望在培訓會上看到熟人。有些時候,熟人越多意味著束縛越多。小桂不希望這樣,他想要裸奔——即使秒秒鐘都在裸奔,也只是三天時間。三天過去,再穿越回以前的生活,有誰知道他曾經裸奔過?深圳很小,但世界很大,那些看過他裸奔的人,那個時候,誰他媽的又知道他們在哪里?
整天忙著采訪寫稿,小桂和小北單獨相處的時間很少,但這并不妨礙他對小北的了解。小桂對小北的了解,是從微博開始的。這么說吧,如果把小北比如成一個女人,那么微博就是進入她身體的通道。平時上班,如果不需要拍照,也不需要陪老板打球,小北的工作就是寫微博、看微博、評微博、轉微博,好像沒有微博,他在辦公室就會待不下去一樣。小北有一部蘋果五代的手機,配一張3G手機卡,這樣的裝備,玩起微博來當然方便。小北的微博里,有文字,有圖片,也有視頻,天馬行空,無奇不有。他曾經上傳過一張圖片,黑色背景,中心位置有兩個隔著約摸一公分的小橢圓。大家都很好奇,有人猜是動物的眼睛,有人說是印象派畫家的作品,還有人說是巨人的鼻孔,結果他們最后全都大跌眼鏡——小北說,這是他內褲上的破洞。過一段時間,小北又發上來另一幅杰作:一坨顏色棕黑、彎彎扭扭像冰淇淋的東西,還特別注明是實景拍攝。馬上有網友評論,問小北這會兒是不是在冷飲店,或者是咖啡屋,或是西餐廳,而最終答案卻是:在廁所。小北的微博劍走偏鋒,擁有很多粉絲。小桂想,如果放屁也能拍成照片,小北一定會把蘋果塞進肛門守株待兔。
3
生活中的小北,一點兒也不像在微博中那樣無厘頭,這是小桂在和小北同居一晚后得出的結論。主辦方訂的是雙人房間,小桂和小北住一間。那個晚上,小桂從小北那里了解到許多秘密。這些秘密讓他覺得,這一年多來,他住在一間屋子里,他一直以為這間屋子寬敞、明亮,卻不知道它還有間地下室,光線昏暗、神秘莫測。他從未去過這間地下室,但同事們卻是那里的常客。
吃完飯,小北提議到海灘上走走。兩人赤著腳,提著拖鞋,在海濱浴場長長的沙灘上走了好幾個來回,走累了,又到酒店后面的一間露天排檔吃燒烤。他們聊到小桂不久之前去過的臺灣,小桂說,其實啊,那是個苦差。小北說,你不說我也知道,連續四期報道,三萬字啊,肯定有壓力。小北這句貼心貼肺的話,讓小桂心里立刻涌上來一種說話的欲望。時間緊,任務重,白天跟團到處跑,晚上很晚回酒店,還得加班采訪。這哪是旅游,比拉磨還受罪。小北說,去之前,老板找過好幾個人,都沒人愿意接這活兒。小桂心里一驚,小北接著說,還好,編輯部有桂哥你這個勞模,識大體,顧大局。不過,換個角度想想也挺好的,甭管怎樣,桂哥你總算也是去過臺灣的人了,對吧?
別看咱們老板脾氣大,但對我其實挺照顧的。小北說這話的時候,他和小桂每人剛喝下去三瓶啤酒。小北已有了些許醉意,嘴里包著一口烤茄子,嘟嘟囔囔地說,桂哥,五月份漲工資,你知道我加了多少?小桂搖搖頭。小北伸出一根指頭,說,這個數。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妹的,大公司加起工資來就他媽的爽。桂哥,不是我說你,你這么拼命,還不一定有我拿得多呢,是吧?小桂點點頭,忽然覺得有些不勝酒力,小北和老板在他眼前打起了斯諾克,晃晃悠悠地旋轉起來。桂哥,你做人太實在。送你一句話,低頭趕路,抬頭看天,懂啵?小北說。
第二天早上,小桂洗漱完畢,才發現小北已經不在房間,床頭柜上留著一張字條:我約了妹子,先走了,別讓老板知道。小桂只得獨自去吃早餐。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的房卡袋里,只裝著一張早餐劵;小北的房卡袋不知去向,只剩一張房卡孤零零地壓在字條下面。
一整天,小桂都迷迷糊糊的不在狀態。上午的高端論壇,下午的嘉賓發言,在他聽來都如鳥語。他只記得坐在他前面的美女,朝著他裸露出小半截白白的脊背。這個美女他是認識的,他的兜里還有她的名片。昨天上午報到,他們一起在大堂休息區等候分房時有過交流。小桂記得她叫杜鵑,頭銜是董事長助理兼內刊主編。小桂昨天收到過很多名片,大部分名片上都印著主編或是編輯部主任的頭銜,但他抬眼一望,派出這些名片的,差不多都是像小北那樣小他一輪的大姑娘或是小伙子,一笑就抖落一地陽光的那種,很少有像他這樣老氣橫秋的。還真碰到一個看上去年紀和他差不多的,一看,才知道人家是市政府某機關刊物的主編,“主編”后面還特別加了個括號:正處級。小桂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崔:旋律聲部的概念人人都在提及,但將這樣簡單而直接的思維方式歸為方法論后,卻是如此有效,令人驚訝!您在與帕內拉教授學習之后,還曾與阿爾多·齊科里尼學習演奏,可否為我們介紹相應情況?
杜鵑拿到小桂的名片時,顯得有些吃驚。剛開始,杜鵑臉上的笑容像天上的白云,被風吹得到處飄蕩。杜鵑問,請問您貴姓,在哪里高就?小桂報出公司的名字,還有自己的名字。杜鵑一臉仰慕的表情,說,哦,久仰,久仰,說著雙手捧上名片,我叫杜鵑,請多關照。杜鵑穿著一件綠色深V領連衣裙,兩只乳房在連衣裙里面探頭探腦,這讓小桂覺得杜鵑說這話時的口氣有點像站街女郎,心想,請多關照?杜鵑仍然笑盈盈地看著他,兩只手仍然伸著,說,我在等您的名片。小桂有些尷尬,伸手到包里摸了一陣,掏出來一張卡片,杜鵑接了過去,只掃了一眼,還是笑著,但失去了內容,顯得很空洞。這次,小桂本來是先到會場的,他坐在第四排的中間位置,一長排位子那時還只坐了他一個人。小桂看到杜鵑,朝她笑了一下,杜鵑也回敬了他一個微笑,但顯然她還沒有準備好,笑得看起來很倉促。小桂以為,就算不是自愿,出于禮貌,杜鵑也會挨著他坐下來的。可是情況并不是這樣,杜鵑徑直走到前排,連回頭都不曾有過。還好她沒有把事情做絕,留給了小桂一截美背。
小桂研究了很久,也沒有找出杜鵑的后背有什么破綻。沒有半顆痣,或者痦子,青春痘什么的,甚至沒有一根過長的汗毛,簡直像辦公室里的那塊小白板,白得無可挑剔。
4
小桂不記得自己上上下下了多少趟,只覺得大梅沙的海灘讓他有些頭暈。酒店也就六層,要是有六十層,經歷這么多來回,他可能早就吐了。
有時候,電梯里突然涌進一大群人,拖著行李箱,或者背著雙肩包,戴著旅行社統一的太陽帽,胸前別著一樣的笑臉,能裝二十多人的電梯很快就被塞滿了。外面還有人往里擠,小桂不得不貼緊玻璃,抬頭,收腹。外面的人擠進來了,是個大胖子,電梯報警,胖子于是又倒了出去,電梯門才算關上。這肯定是一群內地客,剛剛從大巴上下來,又被導游趕進酒店。小桂忽然想起了那次的臺灣之行,整個過程就和網絡上流傳的段子差不多,基本上是上車睡覺,下車拍照,停車尿尿。但是,臺灣至少還有個新鮮,還有日月潭和阿里山,深圳有什么?世界之窗,錦繡中華,歡樂谷,華僑城,哪個景點不是人造的?要看海,有海的地方多的是,哪兒的海不比深圳漂亮?吃多了才來深圳看海。小桂想。
很多時候,電梯里的人并不多。有一家三口,大人小孩都穿著泳衣,濕漉漉地穿過酒店大堂,走進電梯。這三個人,一定是海濱浴場沙灘上剛才那一堆堆肉團當中的一部分。女人長得很豐滿,泳衣卻穿得比較節儉,兩只半球露在外面,死死地拽著小桂的視線。男人瞪著小桂,眼神里有些敵意,女人卻似乎不知道發生了什么,還兀自俯下身子伸手擦小腿上的水,一條深不可測的乳線便暴露在小桂面前。這一家三口在四樓下了電梯,剛出電梯,女人的笑聲便傳了進來,掉在地板上,像是落了一地的鈴鐺。還有三個女孩,看樣子像是中學生。其中兩個,長得青春、漂亮,而另外一個,幾乎整個臉龐都被暗紅色的胎記盤踞,如果她不開口說話,你很難發現她的嘴巴長在哪里,看上去十分恐怖。小桂只瞄了胎記女孩一眼,就趕緊把視線轉移到大梅沙的沙灘上。倒不是害怕,小桂是擔心女孩——對一個長得這么奇怪的女孩,每多看一眼對她來說恐怕都是一種傷害。雖然不直接面對,小桂眼角的余光卻沒有離開過她一秒鐘。他看見女孩在和她的兩個漂亮同伴說話,而且聲音很大,語氣很快樂,就如同上帝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她的事一樣快樂。小桂還記得有兩個老外,一男一女,白種人,身上的氣味很重。倆人差不多是抱在一起走進電梯的,從進到出,他們的舌頭就一直沒有分開過。小桂瞪大眼睛,有些驚訝,又覺得過癮。小桂覺得,這些人都很快樂,包括那個臉龐被胎記覆蓋的女孩兒。來大梅沙的人,都是來尋找快樂的,除了小桂。
偶爾,小桂也能在電梯里看到一兩個培訓會上的同行。小桂表情冷漠,他們點頭、打招呼,小桂視而不見。他甚至還別過臉去,把屁股對著他們,看透明玻璃外的海濱浴場,盡管此時那里已經只剩下點點燈火。小桂想,我這是在做什么呢?裸奔?對,就是裸奔。我想裸奔就裸奔。
有時,電梯里只有小桂一個人。上上下下之間,小桂并不感到孤獨。他腦子里天馬行空,想到未來,幾十年,幾年,幾天,甚至下一秒,他就可能會死去,走進那個未知的,虛無的世界。小桂想到更多的是過去。過去,他在沖壓車間做一個小小的計劃員,藍領,每天要忍受沖床開動時的轟隆聲在他耳朵里呼嘯,要上夜班,每過半個月倒一次班。還要天天求人,拜托那些拉長組長做快點,不然完不成生產計劃,后工站缺料。后來,公司辦了報紙,編輯部貼出海報招人。他大著膽子去應聘,帶著一摞可以當凳子坐的作品,終于應聘成功。初進編輯部時,老板找他談話,說他只有高中學歷,起點很低,要多下點功夫,盡快適應從藍領到白領的身份轉變,否則在這個部門會被邊緣化。他聽老板的話,努力學習做白領,拼命工作,拼命加班——沒有加班費拿的那種加班。他漸漸跟上編輯部同事的潮流,把那部用了五年還依然皮實的諾基亞丟給鄉下的老爸,花一個多月的工資去買了部蘋果。偶爾,他也和同事一起去看看電影,打打羽毛球,唱唱K,聚聚餐,泡泡吧,甚至干點別的壞事。他覺得自己很像一個白領了,盡管每個月的工資總是不夠用,有時甚至還需要老婆支援;盡管他仍然租住在那間嘈雜狹窄的農民房。再后來,老板在一次編前會上,把他命名為首席記者;再再后來,也就是今年五月,老板給他漲了五百塊工資。
5
小桂在電梯里待了兩個小時。這兩個小時里,他認識了很多人。小桂發現,要在短時間里記住一個和你毫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一件難事。除了臉,每個人的身上總還有些其他的特征,讓你能把他和別人區別開來。比方說,一個小時之前,那濕漉漉的一家三口又下樓去了。他們穿著衣服走進電梯時,小桂差點沒有認出來。女人換上了長裙,裙子遮蓋住了她身體的其他一些部位,但那兩只豐滿的半球卻欲蓋彌彰,讓小桂覺得似曾相識。緊接著,男人銳利的眼神也喚醒了小桂的記憶。還有那個六七歲的小男孩喊爸爸媽媽的聲音,同樣讓小桂耳熟。電梯下到一樓,男人最后一個走出電梯。
小桂笑了。他本來是想到此為止的,現在反而不想離開了。這件事情,現在變成了一個好玩的游戲,讓他欲罷不能。他關上電梯門,按下6。
兩個小時前,小桂吃過晚飯,那時剛好六點。小桂打算找酒店前臺再要一張早餐劵。前臺值班的還是昨天那兩個服務員,一個穿著紫花襯衣式制服,另一個是黃花。小桂對紫花說,你們昨天只給了我一張早餐劵,能不能再補我一張?紫花問,你住幾天?小桂說,三天。紫花又問,你們是協會的?小桂說是。紫花說,不會呀,協會的房卡袋里都裝了兩張早餐劵,怎么就你是一張呢?小桂轉身看看前后左右,說,你問誰呢?紫花說,當然是問你呀。小桂說,早餐劵又不是我放的,我怎么知道?紫花說,要不你再上房間去找找,看看是不是落在哪兒了。小桂說,房間我翻了好幾遍了,真沒有。紫花說,那我們也沒辦法。小桂說,你什么意思?你以為我想訛你一張餐劵?紫花針鋒相對,說,你以為我們想訛你一張餐劵?小桂一下子接不上來,身上的血全躥到臉上。黃花這時走了過來,說,先生,這樣吧,我先向銷售經理另外申請一張餐劵,但是不能保證可以申請到,等有結果我再聯系你,好吧?小桂動動嘴唇,想說什么又說不上來。
這種團體客,最難纏。小桂聽到紫花在他背后小聲嘟囔。
離開前臺,小桂一下子不知道該去哪里。他怒氣沖沖地走到電梯邊,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干點什么了。
快到九點,電梯里熱鬧起來。酒店天臺有一場協會組織的燒烤聯誼會,人們從不同樓層涌進電梯,目的地都是樓頂天臺。大家都在熱情寒暄,沒有人發現電梯角落里的小桂。小桂在等待,等待那一家三口的歸來。
電梯又到了一樓。進來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那孩子一進門就問女人,媽媽,叔叔怎么還在這里?孩子的聲音這么耳熟,讓小桂一下子認出了他們。不過,還少一個人。小桂按住電梯的開門鍵,探頭朝外面張望。抱歉,先生,麻煩您,我們要上四樓。女人朝小桂嫣然一笑,說。小桂有些疑惑,女人又是一笑。小桂松開手,按下4。他覺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目標,就把目光狠狠地摸向女人的胸脯。
媽媽媽媽,那位叔叔是干嘛的?走出電梯時,小男孩又問女人。你說呢,寶貝?我說啊,他一定是個開電梯的。電梯門關上,小男孩的聲音飄了進來。
6
小桂緩緩走出電梯。酒店樓頂很熱鬧,有人在唱卡拉OK,有人在劃拳行令,似乎還有人在發酒瘋。從海濱浴場吹過來的夜風把他們的狂歡聲一陣陣灌進小桂耳朵里,既真切又縹緲。小桂轉過酒店的回廊,往海灘的方向走去。
快十點了,海濱浴場上仍然人流如織。夜色中,女孩和女人們那些裸露的大腿與乳房更加白得醒目。小桂站在大梅沙的淺水中,悄悄踮起腳尖;他的目光在大梅沙夜色的掩護下,可以很深地插入那些比基尼女郎的雙乳之間,在從她們身邊經過時,他甚至還裝作無意地觸碰她們一下,然后,激動得渾身哆嗦。沒有人在意小桂此刻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他從沙灘上一路走過,從心底涌起的欲望就如大梅沙的海水,一浪接著一浪。小桂覺得自己應該干點什么了。他轉過身來,把大梅沙甩在身后,匆匆向著酒店而去。
房門開了,小桂發現小北也在房間。小北躺在床上,臉上一副虛脫的表情,說,今天見了一個網友,夠浪,招架不住,提前回來了,妹的。小北的意外出現打亂了小桂的計劃。他走進衛生間,電梯里那個女人又出現在洗手臺上的鏡子里,朝他袒露出一對半球。小桂循著女人的氣味走出衛生間,走出房間,又來到走廊中間的電梯邊。
走廊上沒有人,電梯里也沒有人。
裸奔。小桂腦海里再一次冒出這個想法。他走進電梯,關上門,把手伸向了腰間的皮帶。電梯上上下下,小桂痛快得喊出聲來——他終于實現了自己的愿望。電梯外,大梅沙黢黑的天空像是一只巨大的瞳孔,正默默注視著這位脫得精光的裸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