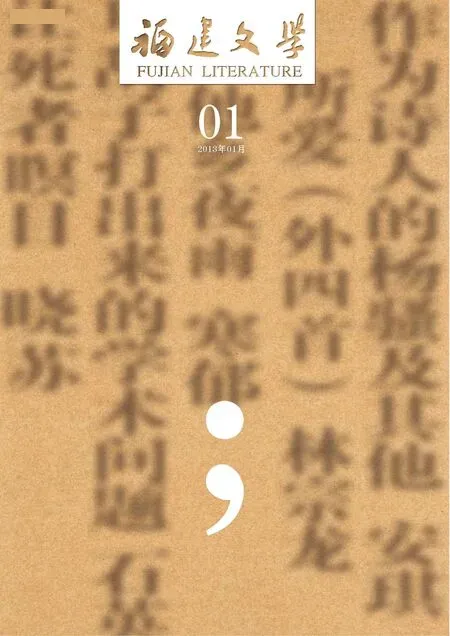貼著人物走的小說
——讀《讓死者瞑目》
□劉 忠
貼著人物走的小說——讀《讓死者瞑目》
□劉 忠
生活中,人們常用“死不瞑目”一詞表達不滿、不舍、不離、不棄等情感。事實上,人活著要面對塵世的無盡紛擾;死了也要接受內心的種種考驗。難怪,國人說,“事死如事生”;西人說,“向死而生”,傳統文化倡導的那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無為虛靜”、“大徹大悟”等人生理想注定是遙遠的絕響,或者是一種現世的安慰,反倒是“怎么生”、“如何死”顯得切實而重要,至少對于國人來說是這樣,重斂厚葬之風延續至今,也間接助長了盜墓之風,成就了諸多文學經典,《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家》、《子夜》、《呼蘭河傳》、《山峽中》、《財主底兒女們》、《四世同堂》、《活著》、《心靈史》……都不同程度地書寫了死亡和葬禮活動,有的甚至還構成了小說的主要框架和情節鏈條。
毋庸諱言,古今中外,死亡都是文學的富礦,有形而下寫實的,有形而上魔幻的,還有介于兩者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小說《讓死者瞑目》僅從繁文縟節的喪葬活動中擷取洗澡、穿衣、瞑目等環節,小中見大,寄寓作者對社會、人生、人性的當下思考。小說構思精巧別致,人物生氣活現,結構開合自如,隨心所欲而又章法整飭,達到了短篇小說的極高境界。
《讓死者瞑目》情節并不復雜,小說中的“我”身兼兩職——接生和送死,“接生”一筆帶過,重心下移至“送死”一維,殯葬業是一個復雜的產業鏈,送死也不容易,要技術,要膽大,還要會揣摩死者的心思,考量人性的良善險惡因素,用當下的時尚話語說,就是臨終關懷。與洗澡、穿衣相比,瞑目因為涉及死者的“心安”問題,顯得異常重要。此后,小說就圍繞“瞑目”展開,起初,依靠手的拉扯和語言的安慰,如喝蜂糖水、子孫通話、妻子懺悔,死者都順利地“瞑目”了;但在村民劉元福身上,食、色、性的安撫卻失效了,“死不瞑目”成為了一個問題。在“離鄉——進城——回鄉”的過程中,劉元福始終放不下土改運動中失去的二層火磚房,始終無法排遣參與對其批斗侮辱專政的人和事,重回被馬自寶分去的自己的火磚房、弄清楚自己的小舅子為什么誣告自己進而使自己劃歸“地主”行列被剝奪房產也就成為劉元福多年來抹不去的心結,這次葉落歸根,救護車護送只剩最后一口氣的他回村,從兩次熄火、死不瞑目、讓死者瞑目等一些列突發事件上,引發人們思索農民對土地的依戀、人性的幽暗和歷史的錯亂。
作家曉蘇是位講故事的高手,不經意間把個“死不瞑目”的故事講得風生水起,饒有味道。就小說而言,讀者關心最多的是作家通過小說“說了什么”,而作家矚目的則是小說“怎么說才是小說”。福柯有言,“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時代,而在于講述話語的時代”。劉元福的人生與時代一起跌宕起伏,土改運動中他被錯劃為“地主”,剝奪住所;新時期,為生計所迫最早走出山村,發家致富,過上小康生活;晚年,在支付了一筆不菲的購房款后,重回當年的住所終老,瞑目西去。從事實層面上看,劉元福的一生和那個時代許多的“地主”命運沒有什么兩樣,是“已然存在”的,不需要作為問答;而從價值層面上看,造化弄人、命運遭際背后的隱秘信息又誘惑著作家追問“何以存在”、“如何存在”等問題。應當說,“讓死者瞑目”負載的不僅有特殊年代的記憶符碼,更有作者對人性惡的深思。如果說,當年馬自寶通過編造、誣陷等不法手段分得劉元福的房子,尚可推諉給“運動式”的左傾時代,那么當下呢?金錢的巨大誘惑又讓馬自寶趁火打劫了一把,這之中,難道沒有“心太黑”的因素?故事的背后是意義,人性的幽暗彰顯的是作家開掘素材、融化歷史硬塊的能力,“讓死者瞑目”何嘗不是對生者的警戒、死者的慰安!
大凡短篇小說作家,講究個惜墨如金,直奔主題,曉蘇似乎不走此路,《讓死者瞑目》雖也精心結構故事,采用人物鏈條的方式推動情節發展,但也不乏精彩的閑筆描寫,比如,開頭部分接生與送死的不同;中間部分“我”的心理活動,都不同程度地豐滿了小說的敘事、人物的性格。從這個意義上,我很贊同“短篇小說作家都是講故事的高手”這一說法,但僅會講故事還遠遠不夠,要讓故事深入人心,就得學會精于場面描寫,做到場景轉換與故事推進互動共生,否則,就會情節艱澀滯重,缺少優秀小說應有的輕逸之風。
當然,作為一個優秀的小說作家,還要做到故事貼著生活走,生活貼著人物走,要讓人物生動起來,立體起來,這也是優秀小說與普通小說的一個重要區別。《讓死者瞑目》中的“我”肩負生死兩端,斂葬中,“我”隨同死者、死者家屬閱讀人生百態、世事變遷,葆有一顆愛人之心,有人說,人死如燈滅,好像是說人一死就沒感覺了。可我不相信這種說法。我們又沒死過,怎么能斷定死了的人就沒有感覺呢?”作為敘事視角和敘事人,“我”不僅起到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同時還參與到人物塑造和意義呈現之中,不時地化解危機、勾連人物,組成一個個看似散漫實則緊湊的場景,實現“讓死者瞑目”的心理祈愿。毫無疑問,作為死者,劉元福是小說當仁不讓的主角,一來是他的人生跨度長、起伏大,他的“死不瞑目”不是源于一般的物質、感官享受,而是精神的、心靈的重壓。二來他的戲份多,是有故事的人,豐富曲折的人生與短篇小說的有限篇幅形成扭矩,考驗小說家的輾轉騰挪功夫,不斷衍生出精彩場景。如果說“我”、劉元福是小說的顯在人物,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馬自寶這個隱形人物則通過朱南山、馬自珍之口開始登場,反客為主,扮演起劉元福命運起伏的關鍵人物,從策劃欺壓剝削長工到參與組織批斗會,從分配占有劉元福房產再到高價賣房,馬自寶的工于心計、狡黠貪婪性格盡顯無疑,小說像剝竹筍似地一步步走進他人性的幽暗面,也為人心的難測、人性的多變作了很好的注腳。一句話,小說因著人物而生動。
曉蘇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生人,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后來又一直在高校工作,至今已出版長篇小說《五里鋪》、《大學故事》、《成長記》、《苦笑記》、《求愛記》,中篇小說集《重上娘山》、路邊店》,短篇小說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燈》、《狗戲》、《麥地上的女人》、《中國愛情》、《金米》、《吊帶衫》、《麥芽糖》等,算得上是成就卓著的“老作家”了,在小說題材、敘事范式、審美呈現、語言表達上已漸成風格。大學校園、鄉村生活是他書寫社會、考量人生的兩個最主要窗口,也是他源源不斷的生活礦藏,溫情的批判、喜劇的嘲諷、理性的自省讓他在融化生活硬塊、穿越人物叢林、抵達理想的彼岸的同時,也會生出許多留念、搖擺、彷徨,甚至是無解,這在他的校園系列和鄉村系列小說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大學生活美好充實,但欲望的旗幟早已經在校園豎起,職稱競逐、利益尋租、權力交換、師生戀情、學術不端等現象司空見慣;鄉土生活安逸靜謐,但現代化的觸角無所不在,鄰里糾紛、人性裂變、情感扭曲、精神蒼白也讓人們頓生惋惜之情。這種復雜、糾纏、矛盾的人物性格、文化心態很難讓讀者將曉蘇的小說歸入到哪一類中去,傳統、現代、鄉土、都市、底層、智性……,無論哪一個詞語、哪一種分類似乎都不能言盡其意,也讓習慣了分類思維、簡化模式的理論家們十分為難,小說《讓死者瞑目》,亦當如此看待。事實上,一部文學史就是這些為難的作家作品組成,他們的存在促使我們重回錯綜復雜的文學經驗,貼著作品行走,循著人物思索。如此,我們才會為小說自身的豐饒多變而欣喜不已,為小說家們的智慧創造而心生期待。
責任編輯 石華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