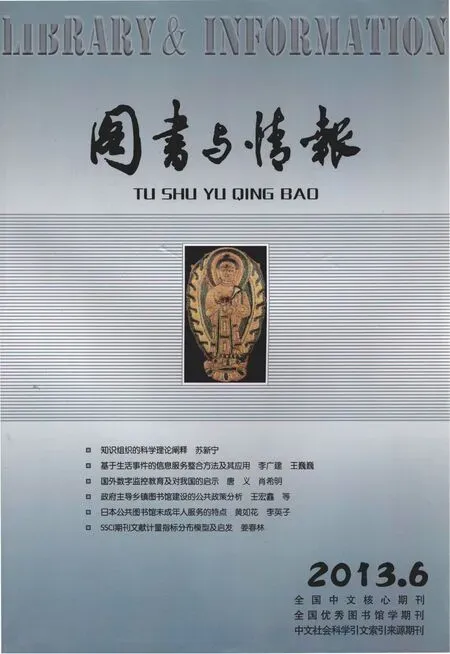有關皕宋樓藏書東去日本的若干思考
吳維麗 張成樑
(浙江外國語學院圖書館 浙江杭州 310012)
藏書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四大私人藏書樓以收藏之富聞名遐邇,即浙江歸安 (今湖州)陸氏的皕宋樓和杭州丁氏的八千卷樓、山東聊城楊氏的海源閣、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其中尤以皕宋樓規制最宏。皕宋樓以其藏書數量之大,收藏宋元刊本之眾而被世人所重。然而,1907年,陸氏皕宋樓藏書被日本三菱財團巖崎氏家族的靜嘉堂文庫收購。皕宋樓藏書流散日本震驚了當時中國學術界和藏書界,成為中日關系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本文試圖從日人來華訪書這一角度來分析思考皕宋樓藏書流散日本事件。
1 皕宋樓藏書
1.1 陸心源與皕宋樓
皕宋樓主陸心源(1834-1894),字剛甫,號存齋,浙江歸安人。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中舉人,歷任廣東南韶兵備道臺、高廉道臺、福建鹽運史等職。陸心源是一名干練的官吏,同時也是一位大藏書家和著名的學者。
與其他清代藏書家相比,陸心源并無藏書世家背景。當時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連年的戰火,使得江南各地的藏書家在動亂中無力自保,藏書樓頻繁易主,藏書紛紛散出。陸心源嗜書,精通版本目錄學,且家室富有,借此時機,廣為購書。陸心源收購了上海郁氏“宜稼堂”藏書48791冊,占皕宋樓藏書的大半。此后,陸心源又購入同縣嚴元照芳椒堂、韓子蘧等家的舊藏。江南數百年藏書精華,一時多流向陸家。陸心源在歸安修筑藏書樓,系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皕宋樓專儲宋元舊刊,十萬卷樓藏明后秘刻,守先閣藏普通刻本和抄本。皕宋樓全盛時期,藏書總量有 5千部,近6萬冊,25萬卷左右。因皕宋樓以藏宋元舊刊著稱,人們常以皕宋樓代稱陸氏所有藏書。古籍中,屬宋元善本最為精湛,宋版書至明代已很珍稀,清代藏書家佞宋成風,“皕”為二百,陸心源以“皕宋”名其樓,意謂內藏宋本二百種之意。據李宗蓮所說,皕宋樓所藏“宋刊至二百余種,元刊四百余種”。晚清時期,能像皕宋樓那樣珍藏如此多的善本,在全國是屈指可數的。
1.2 皕宋樓藏書東去日本
清代是中國私家藏書的鼎盛時期,但清代私家保有藏書的時間不太久,“藏書無三代”幾成普遍規律,陸心源的藏書也未能免此厄運。陸心源臨終時曾有遺言:“訓囑諸子保存好圖書,勿令散失。”然其子陸樹藩未能善守所藏,以118000銀元賣給日本靜嘉堂文庫。清末時代動蕩,陸心源歿后,陸家經濟大不如前。因日商傾銷人造絲的沖擊,陸氏的繅絲廠及連帶的錢莊宣告破產,虧欠甚巨。“除變賣了一些在滬的不動產與動產外,尚有所欠。同時考慮到上海、湖州等地兩個大家庭的開銷,只有出賣心源公收藏的藏書來解圍。”1907年仲夏,舶載至靜嘉堂文庫,共計4172種,43996冊。陸樹藩的售書之舉無疑震驚了國人,陸樹藩被斥為“不肖子孫”。學者王儀通發出了這樣的吟嘆:“三島于今有酉山,海濤東去待西還;愁聞白發談天寶,望贖文姬返漢關! ”
靜嘉堂文庫是三菱的第二代領導人巖崎彌之助創建的私人文庫,以庋藏豐富珍稀漢籍而著稱于世。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明治政府推行“文明開化”政策,引進西洋文明。西洋文化滲透進日本社會的各個方面,文化方面出現了崇西學、輕漢學的傾向,許多古典漢籍被任意拋擲或流入書肆。巖崎彌之助有感于此,開始對傳統典籍進行收儲。1892年前后,巖崎彌之助利用其巨大的財力,開始搜集中國和日本的漢籍,并建立靜嘉堂文庫。收購的皕宋樓藏書構成了靜嘉堂文庫的基本藏書,同時由于皕宋樓以所藏珍本秘籍豐富而著稱于世,靜嘉堂文庫也因此一躍成為日本收藏漢籍之巨擎。
陸樹藩出售藏書已成必然,而結果被日本人所購是有原因的。談及此次書籍交易,不得不提到一個關鍵人物——日本漢學家島田翰。島田作為此次書籍交易的中介人,可謂是“立下了汗馬功勞”。島田于1905至1906年間,到我國江南各地游歷訪學,期間結識了陸樹藩,數次登皕宋樓,見皕宋樓管理不善。島田是一個精通和漢典籍的漢學家,一眼看出這些書的價值,且其又極合日本需要。于是他反復鼓動陸樹藩出售藏書。中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漢籍輸入日本的歷史源遠流長,日本歷來重視漢籍。縱觀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日人來華訪書是一個特殊現象,而島田翰只是眾多來華訪書日人中的一人。
2 日人來華訪書現象
2.1 漢籍與日本
早在公元4世紀的時候,中國文獻典籍已經傳入了日本列島。7世紀至13世紀,漢籍的輸入主要由日本向中國派遣的使團承擔。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后又派遣遣唐使,前后持續約400年。遣隋使和遣唐使肩負著多項使命,購求漢籍一直是他們的重要任務。日本平安時代是貴族文化占主流的時代,這一時期的貴族知識分子,包括皇室在內,以中國文明為榜樣,對漢籍嗜愛如命。日本鐮倉時代、室町時代即13世紀至16世紀(在日本文化史上稱為五山時代)與平安時代相異,文化的主宰者是僧侶階級,漢籍的輸入主要由日本僧侶階層承擔。到了日本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把宋學作為官方哲學,成為長達250余年的江戶幕府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之一。江戶時代的開創者德川家康,既重武治又重文治。1602年在受封“征夷大將軍”之前,在江戶(今東京)建立“楓山文庫”,著力于搜集五山時代掌握在僧侶手中的一部分漢籍,還從中國直接購進漢籍。江戶時代,日本商業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文化開始走向城市民眾。這一時期,主要通過商業渠道輸入漢籍,漢籍的買賣是中日兩國貿易的大宗貨物。直到明治維新之前,公私學塾的學生必讀“四書五經”。
2.2 從傳統日本漢學到日本中國學
與漢籍在日本的流布同步,日本漢學也逐漸發展。日本漢學主要是以儒學作為研究闡述的對象,從漢籍輸入日本之初逐漸孕育,至江戶時代,以宋學為核心的日本漢學終于全面形成。
明治時期,日本漢學經歷明治政府推行的 “文明開化”政策的洗刷,走向了消亡,出現了許多古典漢籍被任意拋擲或賤賣的現象,但在甲午戰爭之后得到了逆轉。甲午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舉國上下加強了對中國的關注,如此泱泱大國竟被一小國打敗,日本國內開始反思漢學,同時一批時代的弄潮兒開始踏入中國,考察中國社會。此時,一全新的學術即“日本中國學”悄然興起。日本中國學與日本傳統漢學最大區別在于其研究方法上,日本中國學崇尚客觀實證,重視文獻分析,把中國當做一個客體即一個相對于本國文化的“他者”來對待。隨著中國學的興起,曾一時被拋擲的漢籍又被視為珍寶。
2.3 日人來華訪書
隨著日本國內對漢籍需求的增加,日本國內原有的漢籍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市面上出現了一些專門經營漢籍的書店,如1901年田中慶太郎在東京開設了第一個專門經營中國漢籍的書店——文求堂,其中出售的書籍是從中國購進的。田中慶太郎在他的訪書記中寫道:“到上海后的第二年,第一次去了北京……當我去一流的書店時,書店并不把我當顧客,大概也是看我不太懂書的樣子,所以,就到那些三四流的書店去,胡亂地買了一些雜書。不可思議的是,我將這些雜書帶回日本后,不管什么都全部賣出去了……到了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爭前后,《說文》等書籍非常熱銷。此類書以前基本沒有輸入,所以,無論是怎樣挑剩的書,都人人爭購,銷售一空。”在供需緊張的背景下,古籍書商往往可以以高額的差價出售從中國購入的古籍,賺到高額利潤。除古籍書商外,還有眾多中國學專業人員來華訪書,他們善于識別文獻典籍,在華購得了不少珍稀善本帶回日本。島田翰就是眾多來華訪書的中國學專業人員之一,為進一步研習中國文獻典籍,到中國江南各地游學訪書。明治維新之后中日國力消長更替,堅實的經濟實力成為日人訪書的堅實后盾。三菱財團以其雄厚財力建靜嘉堂文庫、購入皕宋樓藏書,一方面是保存被拋擲的漢籍,另外一方面是為支持巖崎彌之助的受業恩師重野安繹(1827-1910)的學術研究。重野安繹是當時日本漢學界諸老博士之一,時任靜嘉堂文庫的文庫長。皕宋樓的東移大大便利了日本學者的漢學研究。
日本自古以來重漢學,雖然在明治維新期間傳統漢學走向了衰亡,但隨之興起了日本中國學這一新學術,重新掀起了漢籍熱。日人來華訪書這一歷史現象就是在這漢籍熱背景下產生的。當島田翰登上皕宋樓那刻,皕宋樓東去日本的命運似乎就已經定了。島田一眼便看出藏書的價值,“我邦藏書家,未有能及之者。顧使此書在我邦,其補益文獻非鮮少”,他下定了“必欲此書在我邦”的決心。
3 日人對漢籍的掠奪
皕宋樓東去日本之后,日本軍國主義愈演愈烈,于1927年收購了浙江東海藏書樓全部藏書 (今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庫研究所)及海源閣藏書,1933年收購了涉園藏書等。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文化典籍開始了瘋狂的公開劫奪。如1936年攻占南京之后,有計劃地對這座歷史文化名城進行“文獻掃蕩”。日軍將國學圖書館、中山文化館等70余處文化典籍收藏處作為劫奪目標,劫走文獻80余萬冊。被漢籍熱沖昏頭腦的日本中國學家們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幕后指使者或提供導向者,是日本中國學領域內發生的極為畸形的現象。
4 結語
皕宋樓東散日本一百多年了,至今我們仍感到深深的遺憾,歷史悲劇時刻提醒著我們應該加強文化典籍的保護。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在兩千多年的交往中既有密切的現實聯系,又有歷史的恩怨。中國的典籍,作為文化的載體,把中國文化傳入日本,成為日本文化發展的營養素,卻又因為日本對漢籍的扭曲的熱愛給中國文獻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浩劫,但在中日交流史上漢籍確實發揮了重要的紐帶作用。中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我們相信在以后的中日交流中,漢籍還會繼續發揮著這一紐帶作用。皕宋樓原藏是中國學界的寶貴資料,國人特別是學者無不盼著“文姬返漢關”,但從目前來看,這一愿望似乎難以馬上實現。為了中日兩國世世代代的友好,進一步促進中日兩國學術交流,筆者建議浙江相關部門與日本靜嘉堂文庫聯系,商洽將原皕宋樓藏書復印,交由相關部門保存。若復印本能回 “漢關”,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彌補了皕宋樓東去日本帶來的遺憾。
[1]王增清,藏書樓中奇葩 文化史上悲劇——湖州皕宋樓盛衰記[J].圖書館雜志,1999,(1):42-43.
[2]蔡淑敏,魂牽夢繞話皕宋[J].圖書與情報,2007,(6):108-109,138.
[3]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106-107.
[4]鄭偉章,李萬健.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172.
[5]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6.
[6]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