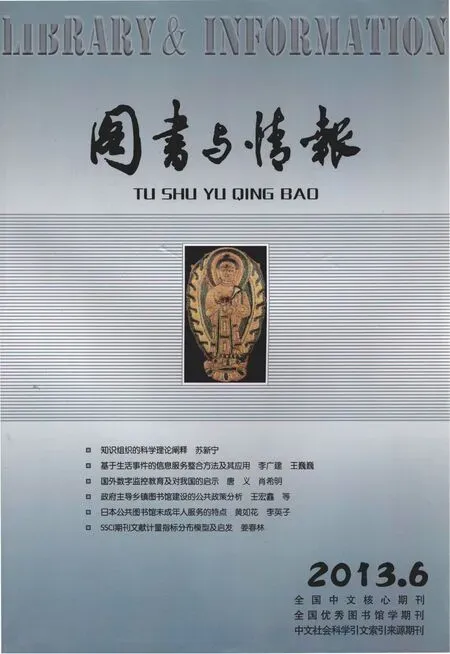基于民族聲樂的高被引論文學術影響力分析
程晗 項亮
(蘭州大學藝術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民族聲樂是我國藝術學科中的一個重要分支。近年來民族聲樂在舞臺及各種媒體上大放異彩,而民族聲樂理論研究卻略顯不足。筆者曾對1998~2010年民族聲樂論文數量進行了統計,從發文數量來看,民族聲樂研究統計結果(共139篇)表明與我國其它人文學科相比,相差甚遠。筆者在本文進一步就1990~2011年民族聲樂高被引論文,分別從發文期刊、作者、被引頻次、論文主題、發文機構等方面進行統計分析,以期對高被引論文的學術影響力進行客觀分析與展示,為今后我國民族聲樂理論研究提供一定的咨詢與幫助。
1 研究方法
本文以CNKI為數據來源,以“主題”為“民族聲樂”、時間為“1990~2011年”進行文獻檢索(檢索時間為2013年1月10日)。考慮到時間跨度較長,為便于分析統計,我們采用11年為一個時間段,即1990~2000年為第一階段,2001~2011年為第二階段,以被引20次以上的高被引論文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統計內容為論文作者、發文機構、發文期刊和論文主題。
2 數據分析
2.1 高被引論文的分布
2.1.1 1990~2000年的相關數據
共檢索出1990~2000年民族聲樂研究論文192篇,其中被引論文111篇,被引次數20次以上的高被引論文9篇。這些高被引論文發表在 《中國音樂》、《音樂藝術》、《黃鐘》、《交響》、《中央音樂學院學報》、《人民音樂》等六種期刊上(見表1)。
2.1.2 2001~2011年的相關數據
共檢索出2001~2011年的民族聲樂研究論文1672篇,其中被引論文843篇,被引次數20次以上論文20篇。這些高被引論文發表在 《中國音樂》、《音樂研究》、《交響》、《人民音樂》、《黃鐘》、《民族音樂藝術研究》等六種期刊上(見表 2)。
2.1.3 兩個階段的論文被引數據分析
我們可以看出,有關民族聲樂方向的高被引論文主要集中發表在《中國音樂》、《人民音樂》、《交響》、《黃鐘》、《人民音樂》、《音樂研究》、《音樂藝術》、《民族藝術研究》等期刊上。其中《中國音樂》始終占據榜首遙遙領先,而《音樂研究》在第一階段沒有入圍的情況下在第二階段以3篇位居第二,進步顯著。這說明這家期刊的刊文質量有所提升。通過查看音樂類期刊排名,我們可以看到,這八種期刊在音樂類期刊的排名中都表現不俗,也全部為北大音樂類核心期刊。這些期刊都是音樂學專業期刊,說明專業期刊在民族聲樂文獻中處于絕對優勢。它們作為國內刊登音樂類優秀科研成果的專業刊物,被眾多學者信賴,吸引了大量優秀稿件,刊發了諸多優秀論文,在音樂類學術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為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音樂》、《黃鐘》、《交響》和《中央音樂學院學報》四個期刊分別為四所專業音樂學院學報(中國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音樂學院不僅在民族聲樂教學中發揮著主力軍作用,而且在民族聲樂理論發展過程中也同樣發揮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表1 1990~2000年發表高被引論文的期刊

表2 2001~2011年發表高被引論文的期刊
對比兩個階段發文量、被引量及高被引論文量。我們不難發現,在第二階段,有關民族聲樂方向的發文量有顯著的提高,第二階段被引文章的數量也有了一個大的飛躍。這些數據的變化趨勢充分顯示了我國民族聲樂理論研究的快速發展。當然,我們也必須同時看到,就增長率而言,發文的增長率高于被引論文的增長率,即“質”的提升落后于“量”的擴張。這說明新增研究隊伍在不斷擴大,但學術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表3 兩階段數據對比
2.2 高被引率
一個學者的學術影響力主要體現在發文數量及被引用率上,而被引用率是衡量一個學者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指標。
2.2.1 1990~2000年的高被引率數據
1990~2000年間發表的論文最短引用周期為2年(許講真的《民族聲樂50年的輝煌歷程》);最長引用周期為14年(金鐵霖的《科學性民族性藝術性和時代性——彭麗媛音樂會之后》),平均引用周期為6.11年。
2.2.2 2001~2011年的高被引率數據
2001~2011年發表的論文,最短引用周期為發文當年(鄭寶華的《中國民族聲樂與美聲唱法之比較研究》,楊仲華、尤志國的《中國氣派 民族神韻 百姓歡迎——論金鐵霖民族聲樂學派的確立》,劉輝的《再論中國民族聲樂的文化定位問題》,李素娥的《“游離”與“扎根”——由“現代民族唱法”與“原生態唱法”問題引發的思考》);最長周期為3年 (楊曙光的 《中國少數民族聲樂藝術的定位與發展》,姚莉莉的《對民族聲樂發展特征的幾點思考》),平均被引周期為1.14年。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第二階段發表的民族聲樂類論文被引用周期比第一階段大大縮短,甚至很多文章在發表當年就被引用,這表明學者對文獻的重視與依賴程度有了提高。
2.3 高被引論文主題分析
民族聲樂是個涉及面十分廣泛的話題,其理論研究領域亦較為廣泛。以上22年發表的29篇高被引論文所涉及的范圍與主題也很龐雜,筆者努力將其進行歸類整理,大致將他們分為六種類別(見表4)。
仔細分析可以看出:在這22年間,民族聲樂高被引論文主要集中在對民族聲樂的發展歷程、文化定位及美學理論方面的探討。無論是對民族聲樂歷史發展軌跡的總結,還是對其文化定位的思考,以及對民族聲樂美學特征的剖析,總的來說都是在總結和歸納民族聲樂的藝術類別和發展趨勢。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在第一階段為數不多的高被引論文中,還存在兩例對成功個人案例的分析論文,這或許也是因為在民族聲樂理論發展的初期,人們對民族聲樂理論認識尚淺,而感性認識更多一些,因此對成功案例的剖析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到了第二階段,對民族聲樂藝術理論性概述、研討類的文章逐漸多了起來。雖然第一階段民族聲樂的理論研究還不夠深入并且發展緩慢,但還是為第二階段以及今后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第二階段所發表的高被引論文無論從數量上還是題材上都更加的豐富多元,其理論水平也在不斷提升。
總之,從表4可以反映出民族聲樂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主要集中在發展歷程、文化定位、美學理論、演唱技術、教育教學和成功案例等六個方面。總體來看,對民族聲樂的研究領域偏窄,挖掘深度不夠。筆者認為今后民族聲樂理論與研究要圍繞其“四性”,即科學性、時代性、民族性和藝術性,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加大投入力度,提升學術水平。
2.4 高被引論文作者機構分析
機構的學術影響力主要表現在發文數量與被引用量兩個方面。而機構的被引數量要比機構發文數量更能確切地反映一個機構的學術水平和影響。
民族聲樂論文被引用20次以上的機構(見表5)中,中國音樂學院擁有的高被引論文最多,但上海音樂學院平均被引頻次最高。這種現象的產生可能與上海音樂學院所擁有的高被引論文發文時間較早有關。同時,可以看出民族聲樂理論研究因為其學科的特殊性,高被引論文主要出自專業性音樂院校(5所),尤其是以民族聲樂為所長的中國音樂學院優勢明顯。其次集中在各類師范類院校和一部分教育學院(9所)。另外還有兩所綜合性院校,兩個文藝團體,一個音樂協會。這表明高等院校教師隊伍是民族聲樂理論研究的主力軍,預計在未來的民族聲樂理論發展過程中,高影響力的論文出產格局不會出現大的突然性變化,但也可以預見到,未來高影響力的論文產出機構將會更加豐富。
2.5 從高被引論文作者的h指數分析其學術影響力
h指數(也叫h-index)是一個混合量化指標,最初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物理學家喬治·赫希(Jorge Hirsch)在2005年的時候提出來的,其目的是量化科研人員作為獨立個體的研究成果。赫希認為:一個人在其所有學術文章中有N篇論文分別被引用了至少N次,他的H指數就是N。如果一位科學家的出版成果以它們被引生命周期的數字進行排序的話,那么h指數就是一個最大值,這個最大值是指每篇論文至少被引了h次的h篇文章。h指數被認為是對先前眾多衡量指標的一大改進。先前的衡量指標都傾向于關注科研人員發表論文的期刊,它們都假定作者的貢獻等同于期刊的平均值,以期刊水平代替了論文水平有失偏頗,而h指數卻客觀地表現了作者個人的實際學術影響力。
經過檢索統計,1990~2011年被引次數達到20次以上的高被引論文的作者共計26人。其中最高值為6,最低值為 1,h值總計為 73,平均值為 2.61(見表 6)。
這些高被引論文的作者多數都是在高校從事音樂教育的專家學者,這種現象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如石惟正、趙世蘭等,他們長期活躍在教學第一線,培養了大量的優秀聲樂人才,有著豐富的教學經驗,這些成功的教學經驗是其產出高質量、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基礎保證,也是這些論文被大量民族聲樂工作者引用借鑒的原因所在。當然,由于本文檢索詞界定在“民族聲樂”一詞,因此,這里作者的h值只是其在民族聲樂一個方面的表現,并不代表其全部學術水平。
總體來看相比較其他人文學科而言,從事民族聲樂理論研究的作者們的h指數普遍偏低,從被引量的不足和h指數偏低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在這22年間,民族聲樂理論研究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但仍然處在初級階段。這或許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民族聲樂的定義與發展方向還存在一定的爭議,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另一方面,從事民族聲樂的工作者們往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文藝團體中的演員,他們大都不做理論研究,另一類多是高等院校的老師,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口耳相傳的教學上,對理論研究重視也不夠。

表4 高被引論文主題分類統計

表5 高被引論文作者機構

表6 高被引論文的作者h指數
3 結語
通過對我國22年的民族聲樂方向高被引論文的信息統計,對其影響力的分析,以及作者h指數的分析,可以了解學者們關注的學術領域及熱點,分析學科發展情況。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民族聲樂藝術在近幾年國家經濟文化政策的推動下,出現了迅猛的發展勢頭,無論從發文量還是被引量都有了一個飛躍。民族聲樂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而專業期刊對民族聲樂理論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這22年間,民族聲樂理論雖然有了一個很好的發展,但是比較其他人文學科,還是呈現出了起點低、根基薄、發展慢的特點。 這與民族聲樂的學科特殊性緊密相關。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通過CNKI數據描述民族聲樂理論研究在22年間的狀況,盡管是客觀的,但也不能說明它的全部,特別是不能就其內容、價值和意義作出全面的質量評估,只是學術述評的一個特定角度。尤其是對論文作者的發文量與被引用量,本文數據只局限于CNKI,因此,不是作者全部成果的集合。
[1]程晗,項亮.1998-2010 年民族聲樂文獻綜述[J].北方音樂,2013,(2):53-54.
[2]金鐵霖.在第三屆中國民族聲樂研討會上的講話[J].中國音樂,2008,(1):46-50.
[3]郭海鷗.學術評價的新方法-h指數及其應用分析[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6):45-47.
[4]蘇新寧.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報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余惠承.建國以來民族聲樂理論研究文獻回顧[J].黃鐘,1999,(1):9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