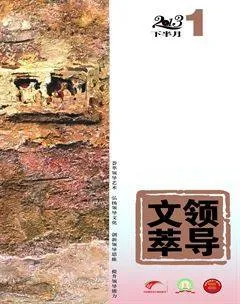高爾基政治立場之謎
□金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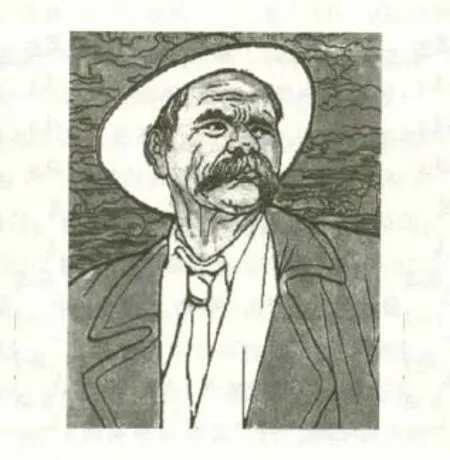
與列寧公開叫板,成為“不合時宜者”
高爾基原本是草根作家,在1905年之前,他基本上屬于文學圈內(nèi)的人。1906年初,他去了法國和美國。在美國,作家的地位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實話實說的政論家和名記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的“冷遇”,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傾化”。
按蘇聯(lián)官方的說法,在列寧的幫助下,高爾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其革命性大大增強。可也有人認為,高爾基的轉(zhuǎn)向與他的私生活有關(guān)。當時,他與莫斯科藝術(shù)劇院的女演員、交際花瑪麗娜熱戀,此人嬌艷嫵媚,又熱衷于革命冒險活動,正是她點燃了高爾基心中的革命烈火。1907年,高爾基以獨立代表身份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此后他成為比列寧更為激進的“極左”活動家。
出人意料的是,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期間,高爾基竟用大量的文學語言對這場革命進行了鞭撻。他說:“列寧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場極端的獸性試驗,他為了自己的試驗讓人民血流成河。”在高爾基看來,俄國社會變革雖是必要的,但“人道主義的理想在革命中發(fā)生了扭曲”。他在給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的信中說:全俄肅反委員會干了許多卑鄙齷齪的勾當,這個政權(quán)“正在激起我對它的反感”。捷爾任斯基稱,這時的高爾基與反革命沒什么兩樣。對此,列寧也深有同感,說:“高爾基與我們的分歧日益加深。”
然而,列寧對高爾基一直比較客氣,在高爾基和有關(guān)部門發(fā)生爭執(zhí)時他經(jīng)常偏向高爾基。列寧之所以不動高爾基的原因之一是:高爾基是他在知識界的最后一個朋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必須有這么一個“諍友”。在列寧看來,高爾基雖然經(jīng)常“冒出令人惱怒的傻氣”,但他“根本上仍站在新政權(quán)一邊,并不是蘇維埃真正的敵人”。
斯大林傾舉國之力接“海燕”回國
1921年,出于對蘇維埃政權(quán)的不滿,高爾基出了國,先是在德國,后又在意大利長住,一走就是10年。
客居他鄉(xiāng)、年近老邁的高爾基思鄉(xiāng)之情越來越濃烈,看到蘇維埃政權(quán)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正在日益發(fā)展壯大,他開始懊悔當初的言行。他在給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信中說:蘇聯(lián)“進入了新生時代”,“國內(nèi)生活的進步越來越顯著……俄國共產(chǎn)主義領(lǐng)袖們的驚人毅力令我嘆服”。他從“不合時宜”的立場上退了下來,從過去譴責布爾什維克的獨斷專橫,轉(zhuǎn)而贊同黨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但他深知,以他當年抗議新政權(quán)“濫施暴力”的態(tài)度,沒有最高領(lǐng)導人的首肯,任何回國的邀請都是無用的。
實際上,斯大林此時對高爾基想回國的心理動向一清二楚。只是高爾基可能還不知道,蘇聯(lián)國內(nèi)圍繞他回國的問題正在展開一場權(quán)力的較量。
1924年列寧去世后,蘇共黨內(nèi)度過了一段集體領(lǐng)導的“政治空白期”。隨后,斯大林相繼展開了與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的黨內(nèi)斗爭。因為高爾基與列寧的“私交甚厚”,且出國后的政治立場比較超脫,所以黨內(nèi)斗爭的雙方都在爭取高爾基的支持。斯大林很重視高爾基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及其活動能量等 “軟實力”。他在黨內(nèi)根基不穩(wěn)的情況下,非常需要列寧的“摯友”為自己增添政治砝碼。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高爾基在倫敦存放有大批檔案,誰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具有什么樣的殺傷力。
高爾基作為黨內(nèi)斗爭的重要資源而成為各派競相爭取的對象,這樣一來,高爾基回國便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
為了迎接“海燕”回國,斯大林指示新聞出版局局長先做一些鋪墊工作。蘇聯(lián)國內(nèi)似乎忘記了高爾基那些“不合時宜”的言行,竟稱他是“十月革命的堅決捍衛(wèi)者”。
回國后,高爾基顯然與斯大林走得更近。當時,蘇聯(lián)政府為高爾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華住所,但大部分時間里,高爾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別墅的附近。在當時,高爾基成為惟一一個可以隨時去見斯大林的人。他們兩人常常“一個叼著煙斗、一個吸著煙卷,單獨聚在一起,喝著葡萄酒,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紅色文豪”:馬戲團里的“丑角”
斯大林心里明白,俄國知識分子的問題要比黨內(nèi)斗爭更復雜,黨可以靠“鐵的紀律”來約束,可是要改變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與政權(quán)對立的習慣,就需要一個有權(quán)威的知識分子來做表率,而此人非高爾基莫屬。
羅曼·羅蘭曾戲稱回國后的高爾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鐵環(huán)的老熊”、馬戲團的“丑角”,此話一點不假。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高爾基對斯大林諂媚的用詞逐步升級。1931年,他寫到斯大林時,還是采用平鋪直敘的筆調(diào),如“斯大林同志說……”;1932年,他增加了具有贊揚意義的定語,如“列寧忠實、堅定的學生”,“我們的領(lǐng)袖”,“列寧的繼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長的、強有力的領(lǐng)袖”;到了1934年,他則稱斯大林是“第二個列寧”,是“真正的領(lǐng)袖”。由此,高爾基成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奠基者。
1930年11月15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同時發(fā)表了高爾基最著名的一篇政論文章《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這句話后來成為“時代語錄”,連斯大林也一再引用。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說,高爾基成為“俄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頌揚奴隸勞動”的人。西方則稱,高爾基已經(jīng)徹底投降,成為斯大林政治的傳聲筒。
在高爾基晚年病重期間,《真理報》像當年列寧病危時那樣,定期發(fā)布這位大作家的病情,斯大林去醫(yī)院探望過三次。1936年6月,68歲的高爾基去世,斯大林親自為其送葬,官方對逝者評價的調(diào)子高得不能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