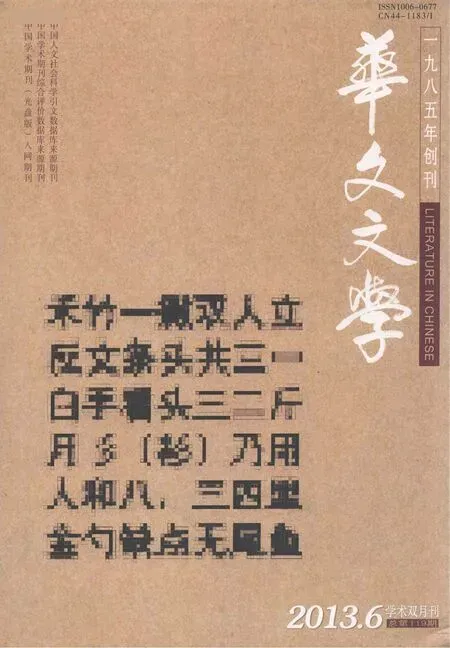中國文學的世界性——論陳銓的文學批評觀
曾一果 季 進
(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最近幾年,中國學者就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價值和地位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尤其是德國漢學家顧彬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尖銳批評,更是引發了中國學術界對于中國文學存在價值的思考。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到底有沒有貢獻?西方文學是否比中國文學更高級?我們該站在什么樣的立場看待中國文學?這些問題困擾著不少中國學者。當然這些問題都不是新問題,五四以來的學者也都一直在探討、思考。例如在20世紀40年代,“戰國策派”的主將陳銓便就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價值和地位進行了深入討論。陳銓曾在德國留學,深受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和尼采思想的影響,他借鑒康德、黑格爾和叔本華等人的思想,深入考察了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特征,并站在“文化主義”的立場,重新評估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世界價值,提出重構中國詩學的四種尺度,并指出了中國文學批評應走的“新方向”。但由于各種歷史因素,陳銓對于中國文學批評詩學的建構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一、“文化主義”的批評觀
1943年陳銓以唐密的筆名,在《民族文學》上發表了《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一文,論文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文學到底有沒有世界性?陳銓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呢?其實這是他針對1917年“文學革命”以來的中國文學現狀的思考。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化氛圍為一股懷疑和反叛精神所籠罩,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進步的,而中國傳統的一切都遭到了懷疑。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使許多人產生了一種“文化焦慮”,古典文學被認為是腐朽沒落之物,跟不上世界潮流,它們對世界文學已毫無意義,中國文學只有全面拋棄舊文學,引進西方文學思想和價值觀念,才能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學難道真的缺乏“世界性因素”?到底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呢?陳銓的這篇文章就是想解決這樣的文學問題。
20世紀20年代后期,中國文學和文化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早年激烈批判傳統文化的胡適等人也開始“整理國故”,重新審視中國的文化傳統。陳銓的一系列文章也是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這些文章一個很大的貢獻是較早地站在“文化主義”的立場,重新評價了中國固有的文學和文化。在《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中,陳銓上來就提出要判斷中國文學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學到底有沒有對世界文學作出貢獻,就必須有一定的“批評標尺”,如果沒有一定的批評標尺,每個人自說自話,自然無法認識中國文學的價值。為此,他對世界范圍的文學批判類型進行了深入考察,認為世界范圍內的文學批評類型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修辭式、內容式、天才式和文化式。他認為有些民族的世界價值在于修辭或者內容,也就是藝術價值高,但絕大部分民族文學的價值卻不能用修辭、內容和天才去考察,而應該拿“文化的標準”去衡量,因為文化才是一個民族許多人思想習慣的“結晶”:
一個文化是一個民族許多年代許多人物生活思想習慣的結晶,經了種種方法地熔鑄陶冶,結果成了一個民族共同對人生的態度。他們有他們特異的世界觀人生觀,同旁的民族迥不相同。
在陳銓看來,就是天才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特殊的文化環境中產生,“在這一種特異地世界觀人生觀的空氣中,有天才的文學家會去創造他的文學,不知不覺也就受了影響,結果他的文學作品,一方面發表他個人的思想感情,同時一方面他也是一個文化的代表。如像歌德的浮士德固然是歌德對人生的啟示,而同時也就是全德國文化對人生的啟示,因為浮士德不但代表歌德個人同時也代表德國全民族。拿文化式的標準來衡量文學,就是去研究某一種文學里面表現出來某種文化對人生的啟示。因為我們的標準是從文化上著眼,所以凡是愈能夠代表某種文化的作品,我們愈認它為偉大。”陳銓雖然受到尼采影響,強調“天才”的歷史作用,但他和尼采不同的地方是,他強調天才是在一定文化環境中產生,缺乏了這種環境,也就沒有了天才。
至于那些缺乏藝術性、天才性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在陳銓看來也并非沒有價值,只要它能夠代表某種文化,不管它有無藝術成分,都是“偉大的”,他認為中國戲劇就是這樣,盡管藝術成分不高,“大部分的戲劇本都俗陋膚淺”,但卻具有“文化的性質”,“代表中國文化的力量卻非常之大”,因此具有很高的價值。陳銓指出,“文化標準”的文學批評,和修辭、內容以及天才標準的文學批評之間的根本差異在于,“文化標準”的批評者并不注重一個作品或一個詩人在藝術上的成功,而注重代表整個文化的文學。
陳銓的文化思想其實與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著名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觀點很相似。雷蒙·威廉斯認為文化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它的內涵隨著社會變遷和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總體來說,人類文化可以分成三種文化類型:1.理想的文化,文化是人類完善的一種狀態或過程,按照這種定義“文化分析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或作品被認為構成一種永恒秩序、或與普遍的人類狀況有永久關聯的價值的發現和描寫”;2.文獻式的文化,文化是理性和想象作品的集合,主要是指一些歷史典籍和文學經典,這些作品集合以不同的方式詳細地記錄了人類的思想和經驗;3.社會的文化,文化是對一種特定生活方式(as a way of life)的描述。雷蒙·威廉斯肯定的是第三種,強調文化是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而陳銓實際上也是把文化看作一種整體的實踐行為和生活方式,在這種文化觀念下,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無論它是高雅的,還是通俗的,無論它是好的,還是壞的,都代表了某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以是有價值、對整個世界文學也是有貢獻的。
盡管陳銓本人身上具有濃厚的精英主義色彩,但他的“文化主義”批評觀,卻不是精英主義式的,相反,他顛覆、突破了以審美和道德為準則的精英主義文學批評傳統。他認為那些存在于底層的各種通俗、淺陋的民間文化并非毫無價值,從文化角度看,這些民間文化具有較高的文化和歷史價值,這些低俗的民間文化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樣式。由此可以看出,陳銓的文化主義文化觀,其實為人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學和文化,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學和文化的價值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二、中國文學的世界性
而在其批評的實踐過程中,陳銓即以一種“文化主義”的文化標準考察中西文學。1933年,陳銓用德文完成了博士論文《德國文學中的中德純文學》,1936年,商務印書館將此博士論文以“中德文學研究”為題目出版。在這篇博士論文中,陳銓運用文化主義的批評標準,仔細考察了《趙氏孤兒》、《西廂記》這些中國文學作品在德語世界的傳播過程,并重新評估《趙氏孤兒》和《西廂記》的文學價值。
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中國學者,大多從事西方文學典籍的翻譯,很少反過來研究“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傳播情況。主要原因便是像陳獨秀、胡適等五四先鋒深受西方進化論思潮的影響,覺得在世界文化潮流中,中國文化已經落伍,西方文化是“先進的”、“高級的”,代表著未來文學的方向。陳銓卻是一位較早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文化的學者,這本身就反映了陳銓具有很強的“文化意識”,他不因中國其他方面的落后而認為中國文學和文化也毫無價值,因為他認為從文化主義的立場去看,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價值都是一樣的,提供了不同的人類生活方式和文化樣態。陳銓仔細地梳理了從1763年(即《中國祥志》)以來二百年間,“中國文學”在德國的翻譯和介紹情況,考察了歌德、萊布尼茨等人所受到的中國文學的影響。在仔細的考察中,他發現由于中德兩國之間的隔膜,德國人對于中國文學并不了解,以致他們翻譯中國文學時產生了許多錯誤:
如果我們再去翻一翻閱在德國最負盛名的兩部《中國文學史》,一部衛禮賢(Wilhelm)一部是格汝柏(Grube)。看見他們講中國文學家名字同作品的稀少,我們也會同樣地失望。至于德文里大部分的翻譯,都是從英文或者法文轉譯出來,英文法文的譯者已經就不高明,德譯本的可靠性更可想而知。一般譯本里的緒言,大都是亂七八糟地瞎說。
陳銓的批評研究無疑提醒國內學界,不要什么都以西方為是,他說從十八世紀以來,即使最負盛名的德國漢學家,也經常誤讀中國文化,因而才把中國二流作品《灰闌記》、《好逑傳》當作中國經典。陳銓認為如果從“文化”角度就很容易理解這種現象,歐洲人學習漢字本來就很困難,要了解中國文學經典,那就更要耗費很長時間,《灰闌記》和《好逑傳》之類的中國二流作品卻能夠簡潔明了地提供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想,所以就容易被西方的學者和大眾接受。
除了站在“文化的”文學批評立場考察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傳播情況,陳銓也用“文化的標準”審視中國古典文學,與梁漱溟等學者的看法一樣,陳銓也認為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早在孔子和老子之前,就已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從那時中國這個民族對人生的態度就基本固定了,而偉大人物孔子、老子等的作用是固定了這種文化,結果形成了三種基本形態:合理主義、返本主義和消極主義。孔子代表合理主義的人生態度,老子代表返本主義的人生態度,外來的釋迦牟尼代表消極主義的人生態度。而政治和文學作品只不過是三種基本文化形態的具體演繹,譬如有的作品表現的是孔子思想,有的作品表現的是道家思想。陳銓還詳細地分析了三種文化所代表的具體思想,他認為孔子思想的特點在于強調人生的明白性,一切都清清楚楚,而站在這一種文化觀的立場來創造的文學,不會有“偉大內心的沖突”,“激烈感情的震蕩”,“豐富的想象”和“神秘的思想”。他說中國的散文和史書大多受到孔子思想支配,這些文章的技術達到了很高水平,令其他民族難以企及。“我們只消想,英法散文的歷史,也不過三四百年,德國不過二百年,再想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散文,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就很可以自豪了。”像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朱熹的《通鑒綱目》,都有一貫的儒家精神,史料和文章的本事,具有很高的水平。他認為從文化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中國文學對世界的巨大貢獻。
同樣,陳銓認為道家和佛家文化也深深地浸透在中國的文學藝術之中,并且對世界文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陳銓雖是“尚力文學”的代表人物,但他卻從文化主義的立場出發,對強調柔弱文化的老子大加贊賞,他說《道德經》“是一部奇書,可以算全世界哲學詩里最偉大的著作。他長不過五千言,但是這五千字所表示出來的哲理,別人五百萬字也表達不出來那樣豐富。”他認為《道德經》顯示了中國文學在深刻性方面也絲毫不遜于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學。如果不了解陳銓的文化主義立場,就很難理解“尚力文學”的代表人物陳銓會如此褒揚老子,而在“文化主義”視角下,陳銓還看到老子與西方近代哲學的關聯:
第一個有膽有識,激烈反抗的人,就是尼采。他看見世界的危機,他恨極了膚淺的生活,他想要重新去維持人類的尊嚴,他想創造一個新的神話,新的宗教,新的文明。二十世紀的初期,在哲學界,黑格爾復興運動,生存學派,漸漸普遍,從新康德派的“理性哲學”變成了近代哲學的“精神哲學”。在文學方面,自然主義,漸漸消滅,最時髦的,卻是新浪漫主義,表現主義,西洋文化的趨勢,是從外形到內心,從物質到精神,從枝葉到根本,從分離到統一,是有目共見的事實。老子的哲學,因此在歐洲也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就好像十八世紀歐洲光明運動者,崇拜孔子的合理主義,歐洲不滿意現代文化的思想家,也回頭研究老子的返本主義。
如果不是本著“文化主義”的立場,陳銓是看不到老子和尼采之間有關聯的,正是“文化主義”批評立場使得陳銓對西方文化有著清醒認識,使他意識到不同民族的文學各有千秋,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希望《道德經》可以變成“現代人到東方的橋梁”,他甚至希望通過交流,把中國文學帶進“與全人類相關的世界文學”中去。
三、重建民族本位文化
“文化式”的批評觀,其實亦是陳銓后來努力建構“民族文學”的理論依據,“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事情。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列強的入侵之下,中國不斷遭遇失敗,這直接導致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產生,五四運動就是在民族危機中爆發。在民族存亡的問題上,無論是左翼文學組織,還是右翼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均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思考中國問題,推行各自的“民族主義”主張。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處于戰爭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文化和民族文學的思考就更深入了,沈從文、費孝通、周揚、胡風、老舍、茅盾等人關于“大眾文藝”、“民族文學”等問題的討論如火如荼。此時,陳銓也站在“重建本位文化”的學術立場上,提出建構“民族文學”的口號。
陳銓肯定了文化是文學的決定因素,文學只是文化的具體形態,具體而言,是民族文化的具體形式。他說當一個民族“到了文化相當的程度,大多數人漸漸有一種或他種共同對人生的態度”,這就形成了民族文化,而一切的政治宗教道德風俗哲學美術,都直接間接接受這個標準的影響。由于民族文化決定著“民族文學”,所以他認為在“文化的標準”下,建立“民族文學”是必要的,民族文化需要一些作家把它“充分表現出來”:
站在世界文學的立場來說,一個民族對于世界文學要有貢獻,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們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現出來。一位作者,在世界文學史上要占一頁篇幅,一定要有寫作品,代表他民族特殊的性格。英國文學史里面,不需要一個中國人,勉強加進去也沒有多大的意義,王實甫和曹雪芹的戲劇小說,在世界文學上,自然有他們很高的地位,然而他們決不是莫利哀和托爾斯泰。他們都是中國人,《西廂記》《紅樓夢》真正的價值,就在于他們表現中華民族特殊的文化。
陳銓強調,一個民族的文學要對世界性有貢獻,必須是表現自己,而不是模仿他人,他認為如果一個文學家成天仿效外國,那么他的文學,也不值得世界上的人尊重和欣賞。陳銓激烈地批評了五四以來的“拿來主義”文學傾向,1919年的辛亥革命為中國帶來了民族主義意識,使得人們第一次認識自己民族,而新文化運動打破了舊文化傳統,帶來新的文化氣象,這一點是為陳銓所肯定的。但是陳銓認為新文化運動并不令人滿意,因為它沒有創造出新的文化,相反盲目崇外的風氣造成了一種“古人不要了,外國人神氣了,打倒舊偶像,崇拜新偶像,名義上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外國舊文化運動”的現象。他認為這種“新文化”是可怕的,得不償失,不僅沒有帶來新的文化,最終會連中國文化的根基也喪失殆盡。
自然,陳銓并非要借民族文學反對西方文化,他試圖區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以說明學習西方存在著不同的層面。他認為文明可以全部搬過來,文化卻不能夠全部搬過來,努力是白努力,定奪不過摧毀自我的發展。陳銓眼中的文明顯然與科學技術相關,他認為可以移植和仿效,而文化則與精神結構關聯,不能完全照搬。而在陳銓看來,新文化運動的失誤就在于混淆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全盤照搬西方。而要改變這種現狀,在他看來就是要重新建立起本位文化的民族文學來。
但是本位的“民族文學”的內核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復活中國古代的文化就行了?顯然不是,陳銓并不像其老師“學衡派”的代表人物吳宓那樣過分迷戀中國傳統文化,而認為五四新文化一無是處。相反,他受了黑格爾的“時代精神論”的影響,特別強調文學的時代因素。他認為新文化必須要由新文學來表現,舊文學不能表現新精神。陳銓批評了中國古代文學缺乏“時代意識”,盲目崇古,不思創造,導致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數千年沒有發展,他認為個中原因就是“時代精神”沒有演進,文學不能擺脫古人。所以陳銓提出重建本位的“民族文學”并不是“復古”,而是重新尋找民族文化的思想資源,并在此基礎上推陳出新,發展出新的中國文化。
當然,這是陳銓的一種設想,在實際的建構過程中,他仍然是采取了“拿來主義”態度,將黑格爾、康德、尼采的理論雜糅在一起,作為自己建構中國“民族文學”的理論根基,他特別強調了文學的主體性,甚至大膽地提出以“權力意志”為中國文學批評的新動向。
四、文學批評的新動向
1943年,重慶正中書局出版了陳銓的著作《文學批評的新動向》,這本著作中的許多文章都曾經發表在陳銓、雷海宗等人主編的《戰國策》上。這些文章的核心便是建立“民族文學”,前面已經指出,陳銓其實是用康德、叔本華,尤其是尼采的主體思想作為其重建“民族文學”的理論資源。
陳銓認為西方近現代文學批評和古代文學批評最大的不同,就是現代文學批評發現了主體(人)的價值,他說,“文藝復興”之前的希臘悲劇和希臘哲學以亞里士多德的批評觀為代表,都相信自然中有一定的規律,這種思想統治西方思想二千年,而文藝復興打破了這種觀念,把文學批評的對象由自然轉到了人身上,確立了以人為主體的文學批評體系。陳銓稱贊康德是西方文學批評轉型中最偉大的批評家,他認為正是康德動搖了西方傳統的基石,“假如人類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世界上一切規律都不是自然事物的本身,乃是人類心靈的創造,那么在文學方面,從希臘以來一脈相傳的文學批評家所認為天經地義的規律,就時時刻刻有動搖的危險,因為規律是人類心靈的創造,人類心靈有變化,文學批評的規律自然也就有變化。”陳銓認為近代西方文化就是“從外在到內心,從物質到精神”,越來越張揚“精神主體”,永恒不變的外在規律不復存在,一切隨著主體意志的轉移而轉移。
普通個體的內心世界已夠豐富多彩,不受規律約束,天才就更不用說。陳銓接受了康德、尼采的天才觀,極力宣揚天才的價值。他指出天才不但不受一切規律束縛,而且能夠創造規律,“仿效不是天才,天才一定有與眾不同的貢獻。規律不能束縛天才,天才隨時可以創造規律。一位天才藝術家的作品,我們能夠就它本身的規律來說明它,不能夠用旁人預定的規律來指摘他。”他還抄錄了康德的大段原文稱贊“天才”,他把天才看成自由心靈和崇高精神的體現。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陳銓強調主體和天才,這與其文化主義批評觀并不矛盾。“文化的標準”是陳銓文學批評的基石,而文化在陳銓看來,不僅與物質相關,更聯系著精神世界。所以天才代表精神,也就代表著一種文化,具體地說,代表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在文化的前提下,陳銓在盛贊天才的同時,并沒有否認那些藝術性不高的一般文學作品。在陳銓看來,盡管一些藝術性不高的文學作品可作民族文化的典型,但天才所創造的文藝作品,往往更能代表某一民族文化,要想認識德國的思想和文化,自然要去閱讀歌德作品。西方近現代文學批評實現了由外部世界向內部世界的文化轉向——強調個體精神和自由意志。這一文化轉向被陳銓認為可以借鑒過來,解決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展問題:
人類的自我已經發現了,世界已經轉變了;天才,意志,力量,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創造發展,是全世界人類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們再也不要任何“外在”的規律,來束縛我們自己,我們要根據“內在”的活動,去打開宇宙人生的新局面。
陳銓認為中國的民族文學要想發展,也應該強調個人主義和主體精神。他認為新文化運動輕視主體性,因此沒能把握“文學批評的新動向”,具體而言,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犯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嚴重錯誤:即“把戰國時代看作春秋時代,把集體主義時代當作個人主義時代,把非理性主義時代當作理性主義時代”,他說五四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時候,忽然發生了轉向,把本來強調主體性的文化活動變成了崇尚客觀性的科學活動,導致了科學至上、階級斗爭等思想的泛濫,中國文化走上了重視形而下的物質主義道路,陷入了盲目的科學、機械和階級信仰,忽視了個人和社會的精神建構。結果,不僅個體自由失落了,而且整個民族從此喪失了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要擺脫這種現狀,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光靠科學和機械文明是不行的,還必須創造自身的精神文化。
而作為進一步要求,尼采的信徒陳銓希望中國文化也應有在世界大戰的時代環境中求生存的“權力意志”。所以,在重慶出版的《文學批評新動向》一書,陳銓把“意志哲學”作為中國文學批評的將來方向,他說在將來社會里,“意志哲學”才是中華民族進步最合適的良藥,中華民族要在大時代中生存,必須追求“權力意志”。
通過上面論述可以看出,陳銓吸收西方文學中關于主體性的批評理論,提出以“文化的標準”考察中西文學的價值,顛覆了以審美為中心的精英主義文學批評模式,讓人們重新認識了中國文學和其他民族文學的世界價值,對于我們思考當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也具有重要啟示。而且,他提出的“民族文學”主張,強調個人意志和主體精神,弘揚民族主體意識,更是對“現實主義”的批評主流的反撥。
當然,陳銓的“民族文學”仍然有很大缺陷,雖然他試圖建構中國文化本位的“民族文學”批評體系,可其“民族文學”的批評體系的核心觀念卻依然源自西方哲學話語,其文學批評觀只不過是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等人哲學思想的雜糅,并不完全適合中國文學,尤其是他對尼采“權力意志”思想的大力宣揚,更是步入了批評的歧途;而且在實際的文學創作實踐中,陳銓所創作的《野玫瑰》、《藍蝴蝶》等戲劇文學作品也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重建“民族文學”的主張最終成了一紙空言。
①②③⑦⑧⑨⑩陳銓:《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民族文學》第2卷第1期,1943年7月。
④⑤[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讀本》,羅鋼、劉象愚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頁。
⑥陳銓:《中德文學研究·緒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12][13]陳銓:《民族運動與文學運動》,《文學批評的新動向》,正中書局1943年版,第20-21頁;第35頁;第34-35頁。
[14][15]陳銓:《文學批評的新動向》,昆明,《戰國策》第17期。
[16]陳銓:《五四運動與狂飆運動》,《民族文學》第1卷第3期,194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