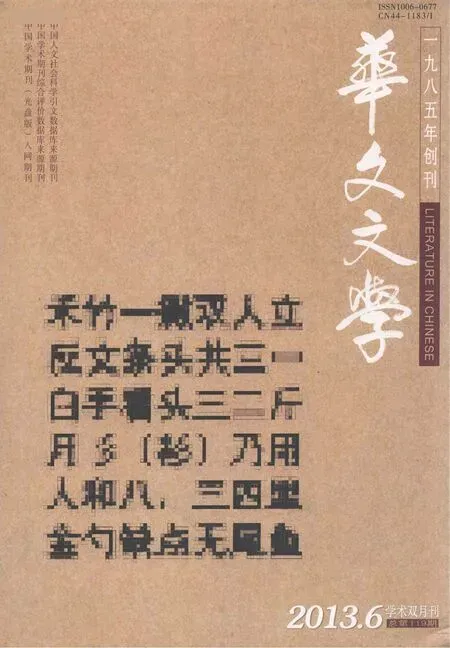求新,求變,求美——紀弦現代詩的美學追求
梁燕麗
(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 200433)
紀弦先生生年百歲,作為一個世紀詩星,自始至終求新、求變和求美,所以他的詩總是鮮活和新穎的、富于審美特質的,貫穿著現代詩的創生歷程和美學追求。在《紀弦精品》的序言中,先生自言:“我的題材是多種多樣的,我的手法是千變萬化的。或為象征的,或為寫實的,或為抽象的,構成的,超現實的;或為相對論的,采取什么樣的一種表現手法,要看所處理的題材如何而定。”由此,從題材內容角度,一般把紀弦詩創作分成三個時期:大陸時期(1948年前)、臺灣時期(1949-1976)和美西時期(1977—),體現出“我的詩生根于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決定了我的詩”。然而,從藝術審美的角度,我們將從純情和反叛,現實和超現實,以及現代詩的散文化等方面觀照紀弦詩的美學追求。這些追求在各個時期,甚至在一首詩中往往是交織、交融在一起的,整體上顯示出紀弦現代詩的審美特征,本不能在時序上或邏輯上分門別類,分開來說僅僅是論述的需要。
一、從純情到反叛
無論“摘星的少年”,還是“檳榔樹”和“半島之歌”,紀弦都有許多“純情”的詩作,包括愛情詩、飲酒詩、懷鄉詩、植物詩、山水詩、宇宙詩等,表達一種真實、純凈、簡樸、客觀的美學意蘊,也追求一種現代詩的“散文價值”。然而,紀詩有時又會在單純的底蘊上騰空而起,表現一種觀念或美學上反叛、創新的決絕、復雜,這種探索在1950年代中提倡現代派之后或許成為主流,但亦時有漩洄。正如《半醉》里那個“對于那些頑固世俗的見解,/我拋出了挑戰的手套”,仗著酒(酒神精神)而如此勇敢的挑戰者;又如《個性》一詩:“在我的路上,/你掘了一步一陷阱;/在我的酒中,/你下了極毒的毒藥。/但我舉杯一飲而盡;/我大踏步向前走”,事實上,經過現代主義洗禮的詩人是最難歸類的,因其最想追求的是創新、變化和個性。
紀弦一些極為動人的情詩和一些關注現實的即事題詩,可能在美學形態上是較為單純和虔敬的,如那首感天動地的《你的名字》:
用了世界上最輕最輕的聲音,
輕輕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寫你的名字、
畫你的名字、
而夢見的是你發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燈,如鉆石,你的名字。
如繽紛的火花,如閃電,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燒,你的名字。
還有,那首玲瓏剔透的《戀人之目》中“戀人之目,黑且美”的醇美詩句。虔誠者則莫如《獨行者》:
忍受著一切風的吹襲
和一切雨的淋打,
赤著雙足,艱辛地邁步,
在一條以無數針尖密密排成的
到圣地去的道途上,
我是一個
虔敬的獨行者。
看似簡簡單單的詩句,純粹中有深味,輕盈中見重量,令人回味。又如寫于1952年的《現實》:
甚至于伸個懶腰,打個呵欠,
都要危及四壁與天花板的!
匍伏在這低矮如雞塒的小屋里,
我的委屈著實大了:
因為我老是夢見直立起來,
如一參天的古木。
這里頗有魯迅野草中“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的憤慨,又有紀弦式幽默機敏的表達方式。“現實”如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縱然你是大材,在逼仄狹隘的困境中,也只能匍伏著生存,參天古木的生命伸展只是天才的夢想。一些從個人的地平線走向眾人的地平線的詩作,如對于草根普羅大眾的關懷,以及社會變革和社會反抗的關注,青澀青春的政治抒情,使沉滯局促的生涯也有激越的想象。如《貧民窟的頌歌》:“我住在貧民窟,/我是貧民窟的桂冠詩人,/故我作貧民窟的頌歌。……無數的窮人!無數的窮人!/無數的窮人!/無數的被欺騙與虐待的潮澎湃著。”作為貧民窟的蒼白的眾生物之一的我的血澎湃著。又如《窮人的女兒》:
窮人的女兒坐在垃圾堆上,
用她的天藍的眼睛凝視著街的遠處。
她是那么莊嚴,那么高貴,那么美,
像一個有許多王子在追求她,
有許多騎士向她宣誓效忠的
古城堡的公主
坐在垃圾堆上的窮人的女兒,變成高貴莊嚴的古城堡的公主,這是紀弦式的浪漫唯美想象,再增添上一些烏托邦明麗浮想。而《記一個酒保》:“我所永遠忘不了的/是那小酒店的阿胖,/他心仁厚,/他的靈魂善良;/沒有一點兒俗氣,/在他那純粹的平凡里”,卻又是用樸素、平易來提煉“平凡”,使之成為通向不平凡的感情去的鑰匙,仿佛舉頭三尺有天使。更有那些回望大地的怡然自得之詩,如《昔日之歌》:“昔日我住在一座小城里,深而幽暗的古老之家很難忘,日子如小城市的單純,而古巷的晨昏是多詩的……”還有《構圖》:“寂靜的十字路口/滿載著甘蔗的牛車/遲緩地行過,/一輛,二輛,三輛……/像活動的圖案。/……島上/詩一般的黃昏。”如此散文化的親切、明凈,不矜持、不夸張地侃侃吟述一種自然、古樸的生活感受,昔日小城的晨昏與今日島上的黃昏,乃是重復出現的詩意棲居的構圖。紀詩中還有更多關懷深廣、情意綿密的詩作,如《愛云的奇人》、《今天》、《狂人之歌》、《命運交響曲》、《狼的獨步》等代表作,客觀生活經過主體的情感化,深深打上個人情結的印記——關乎生死、生命、命運的詩性哲意。形式上的變化從四行一節、凝練純情,到大量運用散文體長句、第三人稱敘事的小說筆法,夾以第一人稱的內心獨白,顯出現代派的色彩;內容上亦從輕柔善感、普世關懷,轉向對生活、愛欲、命運、存在的內心激辯,呈現出騷動反叛的靈魂。紀弦命定要扛起現代主義的大旗,在理論和創作中不斷求新、求變,引領現代詩的煉獄:新的挑戰接著新的挑戰,新的啟發接著新的啟發,新的戰栗又有新的戰栗。然而,從純情到反叛的詩風,在紀弦身上又是辯證統一的。
二、現代詩的散文化
紀弦是現代詩的點火人。他在《紀弦精品·自序》中寫道:“什么是我對詩壇最大的貢獻呢?曰:文字工具之革新,散文主義之勝利。”現代詩反傳統,“就是反它那傳統的‘韻文即詩’之詩觀,乃系置重點于‘質’的決定”。也即,現代詩是內容主義的詩,而非形式主義的詩。現代詩舍棄“韻文”之舊工具,使用“散文”之新工具。現代詩不僅舍棄傳統詩(即舊詩)的形式拘束及文字的襲用,而且,紀弦在1950年代中圍繞《現代詩》雜志創立的“現代派”,更直截了當地提出“新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如果說傳統詩以重感性的“詩情”為根本,那么現代詩則以重知性的“詩想”為根本。總之,紀弦倡導譜寫全新的詩。這種除舊布新的膽識與決絕體現在《一間小屋》一詩:
……
當我提著一大串的鑰匙,
走入這間堆滿了線裝書的小屋,
好不容易才找到那珍本,
而正在一頁頁搖頭擺腦地朗讀著時。
“咦!怎么搞的?眼睛花了不成?”
一股子陳腐的氣息鉆進了我的鼻孔來,
而珍本,已化為灰燼。
如此對待舊傳統,即使今天看來也不無偏激之處,在當時必然引起詩壇的大辯論。紀弦、林亨泰與覃子豪、余光中等展開了“現代主義論戰”,這場論戰歷經1956年和1957年兩年,雙方大戰三百六十回合,結果無論勝負,所幸整個詩壇終走向了“現代化”。自此而始,現代詩的命運,無有格律依傍,無有必定遵從的規訓規則,沒有寫下來就被認定為詩的形體格式,像傳統的詩詞那樣。那么每首現代詩或許都是一個邀請,或者一個挑戰,每首詩都有自己的面貌,在別人的世界里遭逢它自己,在讀者的閱讀理解里實現,或不實現它自己。詩人也必須完全敞開自己,等待讀者發現和參與,在閱讀中創造屬于自己而不必是作者的理解與體會,推衍文學的潛在價值。于是,接受美學及其閱讀的動態過程備受關注和強調,只有讀者的釋讀、賦形,詩才是一首詩,一切都是邂逅,正如帕斯所言:“每一個讀者都是一首詩,每一首詩都是另一首詩”。而讀者的口味會變,息息在變。現代詩創作也在變,求新,求變,讀者的口味因詩人的詩而變,一觸即變。詩的藝術價值和欣賞價值再也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
三、現實和超現實
現實的詩和超現實的詩都代表紀弦的一部分追求。一些詩寫得清澈淺顯、簡潔明快、毫不晦澀,當然其中也有用“簡單”去傳達“不簡單”的,然而,另一些詩表達更為廣闊、復雜、錯綜、鮮明、多變化的意象,要表達的應是潛意識的、意識流的、多面的,甚至在字面上不連貫、非邏輯的,所謂超現實主義,如《時間之歌》、《時常我想》、《在地球上散步》、《黑色之我》、《我,宇宙》、《足部運動》、《無人島》、《失去的望遠鏡》、《火與嬰孩》、《午夜的壁畫》等現實與超現實。請看《在地球上散步》:
在地球上散步,
獨自踽踽地
我揚起了我的黑手杖,
并把它沉重地點在
堅而冷了的地殼上,
讓那邊棲息著的人們
可以聽見一聲微響,
因而感知了我的存在。
一個踽踽獨行的老人,用手杖點在地上,發出微響,這是“現實”,在現實的基礎上開展的“超現實”想象:則是具有“魔幻”色彩的黑手杖,“沉重”地點在“堅而冷了的地殼上”,“讓那邊棲息著的人們”,“感知了我的存在”。陰陽相隔一點即通,這種生死界限的突破,此岸與彼岸的感應,可說是“現實”中的“超現實”。詩者即巫,詩想象的翅膀可以上天入地,可以通靈,結尾完全超越技巧,一種由“詩想”油然而生的詩意,形神自然自在。《預感》中“自殺的太陽一輪”,《火與嬰孩》中嬰孩夢里的“火”:從爐火、火柴到火山、火災,都是自動生成的神奇圖景,暗示著人神秘莫測的潛意識。再看《午夜的壁畫》:
一盞燈,柔和地
亮在一間小小的木屋里;
三個一模一樣的沉思著的影子,
構成了一幅午夜的壁畫。
午夜的壁畫,
是即我之三位一體。
午夜的壁畫,
是即三位一體之我。
修長的我,
不可思議的我,
和破碎了的我。
……
我從何處來?
我往何處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而我知道的是:
縱有春風拂過,止水呀也不揚波的了。
故我投修長的影在壁上;
投不可思議的影在壁上;
那個破碎了的我
也投影在壁上。
此乃燈之杰作,
還讓燈去欣賞。
燈是美的,
小小的木屋是美的。
午夜的壁畫也是美的,美的。
“不可思議的我,和破碎的我”,“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這些天問似乎出諸客觀的角度,但卻集中主觀的抽象,超現實的意喻所描摹的無非現實情況。現代詩,就像現代畫中包含了各種解釋一樣。看現代畫時,觀者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感受去領會,不一定有特定的解釋;同樣道理,讀者可從某種表達中去推想、體會詩意。也即,欣賞的方向沒有特定角度,或許你今天這樣理解,這樣看,但一年后,可能又有另外的理解,不同的看法。現代藝術與古典作品不同的地方或許就在于此,也該如此。“午夜的壁畫,是即我之三位一體,午夜的壁畫,是即三位一體之我”,欣賞現代詩該像如此多面性。現代詩也不同于朦朧詩,現代詩中的“朦朧”不過是一種程序,不是要令讀者不明所以。創作是內容決定形式。“燈是美的,/小小的木屋是美的。/午夜的壁畫也是美的,美的。”紀弦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或一個頹廢派,他說:“我的文字,有時明朗,有時朦朧,但我總會展現一幅畫面,讓你可以看得見;指示一種境界,讓你可以走進去。”他的現代詩雖然求新、求變不遺余力,但首要的是求美,因為美是詩藝的靈魂。
陳寅恪先生自述教學三大特點:書上有的,他不講;別人講過的,他不講;他自己曾經講過的,更不會講。香港詩人飲江聯想到超現實主義詩人,或許會說:“這世上有的,我不會講。”也即,現實和超現實的詩,既要和存在著的東西相關,更要與非既存的東西相關。存在著的東西前來打招呼,可能就是寄望于詩人去和不存在的東西打交道。列維勒斯在《上帝,死亡與時間》中說:“古遠得無法記憶者對不可預見者的敬重”。詩人不恨古人之不見,應恨無由對無法記憶者和不可預見者的入思和敬重。先祖、先人、先行者、先輩,和后來者、后輩、后死者,不可預見者,輪回于此于彼者,于今生于來世者,其中包含詩人對于超現實一點點領會,正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說:“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也是愛因斯坦所說:“努力學習,等待啟示”。超現實的詩作,既是技巧又超乎技巧,神附體,靈感眷顧,上窮碧落下黃泉,會有不可知的東西降臨,或者到來。但超現實并非等于神話,現代詩人永遠傾向于人或人性的價值。人不需要神打造,如果生命有意義,是人創造出來的意義,一切與神無關。如果真有神的存在,人也要與神劃清界限,各有各的造化。然而,超現實的古代神話和現代宇宙,都是現代詩創作靈感的源泉,詩人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另一個投影。
生年只滿百,卻懷千歲思。直至晚年,紀弦寫下不少超現實的未來詩和宇宙詩,如《悲天憫人篇》、《有一天》、《給后裔》、《夢想》、《二十一世紀詩三首》、《無題之飛》、《玄孫狂想曲》、《籍貫論》、《人類的二分法》等。紀弦不老,因為紀弦詩超越時空,永遠不老。《有一天》這樣寫道:
有一天,我重返地球老家,
看見我的同類還在自相殘殺。
我就唉的一聲嘆了口氣,
說道:像這樣的野蠻、無知,
你教我怎能邀請人家
前來訪問、參觀?
……
總有一天,我們的子孫,
是要乘坐超光速的宇宙船,
飛到那顆藍色的行星去,
向那些文明人學習的。
這首寫于1989年的宇宙詩,不僅具有地球人的宇宙意識,而且頗有理想主義精神。超光速的宇宙船,乃是島宇宙與島宇宙之間的交通工具,紀弦相信在今后五百年至一千年以內,這個夢想,是一定可以實現的。縱然這是詩人說夢話,也能使我們頓然心胸開闊,頓時與營營役役、同類相殘的生存狀態拉開距離。“藍色的行星”指地球,地球是太陽系中水星、金星之外第三號行星,遠遠看去,是藍色的,一種藍色矢車菊一般的藍色,非常美麗。可是美麗也只是一種夢幻,當外星人向往著子孫后代將乘坐超光速的宇宙船,來造訪美麗的藍色地球,向文明人學習,地球人不能不深感慚愧和反諷意味。在《給后裔》中:
我的孫兒的孫兒的孫兒,
立個志,去做太空人吧!
去訪問仙女座的大星云吧!
那渦狀的,多美麗呀!
她是我們最近的一位好鄰居。
而當你們超光速的太空船
登陸在那邊某一太陽系
之某一類似地球的行星時,
請回看一下自己的家鄉銀河系,
究竟像不像一個車輪?
詩人的想象力超過孫悟空十萬八千里的筋斗云,到達未來的宇宙世界,超越時空回望來處,銀河系不過是一個車輪,而人類的自由與開闊已無可限制,種族、膚色、籍貫、偏見都顯得渺小而陰暗,當“我一下了碟形的宇宙船,就看見廣場上那么多的兒童”,白人、黑人、紅人、黃人、棕色人、非洲人、歐洲人、亞洲人、阿拉斯加人,他們在唱印度歌、日本歌和臺灣民謠《阿里山的姑娘》……詩人“沒有省籍、沒有國籍,也沒有洲籍,/……而只說我是一個‘地球人’,/這也未免太委屈了,今天。/至少,你們應該承認:/我是一個‘太陽系人’”。如此看似漫無邊際的超現實想象,亦是針對今天許多依然尖銳的現實問題,用“一點也不難懂的”散文化的詩句,表達出現代人的普世情懷和宇宙意識。誰說現代詩不可以這樣寫呢?誰說現代詩一定該怎樣寫呢?形式沒有限制,想象沒有邊界,求新,求變,求美是紀弦永恒的追求,也是他留給我們的珍貴啟示。
①②④⑤紀弦:《紀弦精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第3頁;第5頁;第3頁。
③莫文征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紀弦精品》,分成“摘星的少年”、“檳榔樹”和“半島之歌”三個部分,對應大陸時期、臺灣時期和美西時期。
⑥王良和:《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