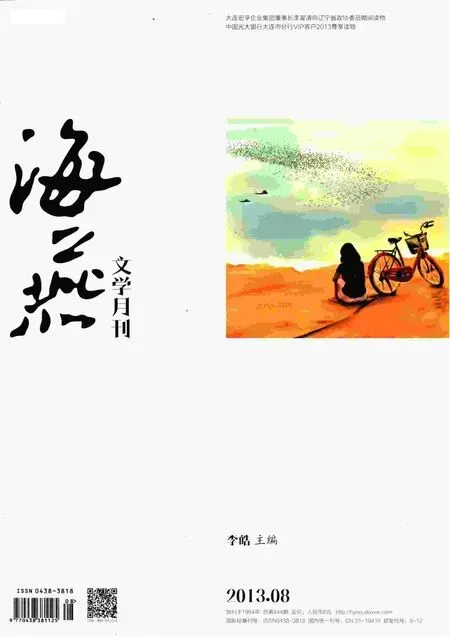姥姥、姥爺和老叔
□孫海東
姥姥的忌諱
我姥姥,活了78歲,生了10個孩子。
那天,她的外孫在課堂寫了一篇作文,開篇第一句話:我姥姥為了她的10個孩子打了一輩子食。
姥姥果真是打食的。
姥姥原本是有名字的,年輕時也是個眉清目秀的“大家閨秀”,是真正的那種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子。但自打嫁給老王家,生活就發生了巨變,日子就不再是衣食無憂,尤其是在第二個兒子餓死之后,姥姥曹桂蓮的大名就沒人再叫了。打我記事起,就聽人們管我姥姥叫“快馬里”,那意思這個女人是風風火火、一日千里型的。
我印象中的姥姥,是村里最厲害的女人。她往街心上一站,可以罵上三天三夜,而那話都不帶重復的。村里從吃奶的娃到半百的漢,沒有人不懼怕她。罵歸罵,姥姥的人緣卻出奇得好,誰家有了大事小情,總要讓她出面拿主意想辦法。后來我才明白那不僅僅是一種怕,而是敬畏,姥姥不是那種潑婦,每次與人吵架都是理在她手里。
那時家里實在是太窮了。瞅著一串兒一個比一個小的孩子,姥姥每天的主要任務是出去打食。打食的主要方式是走村串戶地借糧,從這個村到那村,方圓幾十里一天就能走個來回,“快馬里”的稱呼由此而來。
我姥姥并不做飯,主要是負責打食。今天從公社貸回10塊錢救濟款,明天從大隊背回一小口袋救濟糧,往鍋臺上一放。幾個大女兒做飯的工夫,姥姥盤腿往炕上一坐,拉過煙笸籮,卷上一支旱煙,一邊吐著煙圈兒,一邊盤算下一頓該怎么弄了。
又一個清晨,姥姥背起空面袋出門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奔波在打食的路上。通常她是蓬著頭發,褲管高高卷起,可能衣襟上還沾著幾個飯粒,如果路上有狗沖她吼叫,她會一腳把那牲畜踢出去好遠。沒人會相信,她曾是個寡言少語溫柔可人深宅大院里的書香女子。
因為打食,上到公社書記下到十里八村的人幾乎沒有不認識姥姥的。母親說,如果沒有姥姥打食,剩下的九個孩子不會都活到今天,活得這么實成,沒病沒災。按照現代文學作品的標準描述,這應該算是賢妻良母的典型表現了。但沒人從姥姥嘴里聽過什么愛不愛的,她只是沒完沒了的外出打食,或者說是覓食。現在看電視,每當瀏覽動物世界里的鏡頭,總能想到我姥姥。
要強調的是,姥姥打食回來,盤腿坐在炕上,看著女兒們把飯食做好。一般來說,實米實面的、沒有揣糠摻菜的干糧都是留給五個兒子的。但她從不明說,總是說這個餅形狀不大好,放在一邊,那個發糕夾生了,女孩子吃了不好消化。于是那些像樣的飯食基本上是輪不上女兒們吃的。時間長了,女兒們就發現了這個不公平。那天大女兒壯著膽子表示出不滿,我姥姥便勃然大怒:“偏向什么,什么偏向,你們哪個不是我生的?!”
后來,四個女兒出嫁了,五個兒子陸續當兵走了,姥姥的打食生涯也就結束了。但她還是習慣性地沒事出去搗鼓一袋糧食回來,堆在倉房里,盡管那時的日子好過了,家里早已經不是吃上頓沒下頓。再后來,要不是姥爺看見那些快發霉的糧食要招惹一場鼠災,及時制止,姥姥的這個習慣可能會伴隨她到死。
但,打食的病根是坐下了。雖說不再是打食了,可門還是要出的,只不過是名詞改了,“打食”變成了“串門兒”。
我姥姥每天都要串門子。只要我去姥姥家,串門兒總要拽著我。于是,我每次都能聽到那句抱怨:這九個崽子,可把我累死了,這輩子凈給他們打食了。對方保準搭腔說,你不稀罕你這幫孩子嗎?姥姥往往正色道:“稀罕?煩都煩死了!”
轉眼又過去二十多年,我姥姥已經成了快奔80歲的人了。
姥姥瞇著眼睛,腦子都不大清醒了,但依然能卷著旱煙,吐著煙圈兒,說起過去的事來,還是那句話:這九個崽子可把我累死了。
那年正月,我要上街理發,姥姥忽然睜開昏花的老眼,高聲喝道:“不能剪!”我忙問緣由,姥姥遲疑半晌,才喃喃地說:“過幾天不行嗎?正月剪頭是妨舅舅的。”
那會兒,我大舅已經有孫子了,最小的舅舅的孩子也都上了小學。
我站在門口好久無言。沉默中,忽然又聽見姥姥在炕上獨自嘟囔:這九個崽子可累死我了。
母親說,記住兒子,這是你姥姥的忌諱。
后來我想,這其實就是我姥姥的愛,尤其更愛那幾個兒子,雖然她一輩子都沒說那個字。
姥爺是塊自留地
姥爺是個老兵,姥爺還是個逃兵。
但姥爺不是那種真正意義上的逃兵,他是在遼沈戰役被打散了的兵。不過后來這也成了他的一個謎。這么多年,一有人嘮到那段歷史的時候,姥爺的臉色就很難看。
王守財是姥爺的名姓。在我的記憶里,姥爺是個能干的人,一輩子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天還沒亮已經在地里忙活了,月牙兒爬上來才見人從地里回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身上的衣服也永遠是沾著泥土的。快70歲的人了,忙活完地里,還惦記著到地邊的山上栽樹。姥爺說,有了樹地里的土就不薄了。
正因為這樣,姥爺家的地是出了名的壯,出了名的好。人們都說姥爺家的地是扔進石頭都能長出莊稼的。姥爺愛他的自留地,自然也是出了名的。
姥爺外號叫“王老鑿”,那意思就是特別的倔。倔歸倔,姥爺最認理兒。不過誰要是在他身邊提“逃兵”兩字,他就會不分青紅皂白,指定跟你家急頭白臉,那種神情能嚇死個人。那天姥爺和村里的人鬧了矛盾,爭吵中,對方喊出“逃兵”兩字,姥爺掄起鋤頭,差點打折人家的腿。
那天晚上,姥爺喝了很多酒。姥爺就對10歲的我說,爺們兒,陪老爺子喝一盅。我當然不能喝。但姥爺管自還在說,爺們兒,不,連長,不是我要當逃兵,是我實在放不下家里的地,我爹囑咐我一定要把家里的地種下去。
姥爺的話當然我沒懂,但這么多年之后,我懂了。
姥爺是個農民,真正土得掉渣的農民,也是一個真正打心眼里熱愛土地、孝順長輩的農民,為了這個,他不得不從戰場上回來。
他回來了。
姥爺一路要飯從錦州走回到朝陽。沒有人知道這一路上他經歷了什么,總之他回來了,把地侍弄成全村最肥沃的,一直把我的太姥爺伺候到90歲無疾而終。
記得那天晚上,姥爺趴在炕上讓我幫他揉腿。他的腿因為當年打仗過冰河落下了病根,滿腿青筋暴起,昏暗的油燈下,就像蚯蚓爬滿了腿。姥爺瞇縫著眼睛說,小子,別看姥爺當兵沒少遭洋罪,可還當真沒當夠呢,是不回來不行呀!
多少年后,我姥爺,也就是“王老鑿”,響當當地先后把五個兒子都送進了部隊。按說,那時候家里正缺勞動力,但姥爺硬是讓五個兒子都穿上了軍裝。兒子們走了以后,姥爺還是一個人在地里忙活著。他的地里沒有別人家那種父子歡聲笑語的熱鬧勁兒,永遠都是他一個人的影子。仍然是太陽沒升起時人已經在地里了,月牙兒爬出來時人才回來。
姥爺本來是個高大的人,后來腰彎了,背駝了,頭發白了,但地仍然是村里收成最好的。
自打大舅當兵之后,姥爺家的門楣上就多了一塊牌牌,上面寫著“光榮之家”。每年貼的春聯也永遠是“發揚優良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第五個舅舅送走那天,姥爺依然喝了酒,依然是喝多了。他摟著我的肩站在門口,盯著那牌牌凝神地看。
姥爺說,小子,其實誰都不知道,我的自留地里收成最好的,就是這五個兵,現在我的夢算是圓滿了。
再抬頭看時,姥爺那滿是皺紋的臉有淚在淌。但仔細看時,姥爺分明在笑。
那個牌牌,風吹日曬早就沒了顏色,姥爺卻執意讓它在門楣上那么掛著,直到他死。
九命老叔的“猴日子”
我老叔在家族哥們里排行老五,小名就叫老五,大號叫孫洪民。
我老叔歲數不大,雖說才五十六七,可經歷的風險卻不亞于百歲老人。因此十里八村的人都管他叫“九命老五”,我則稱呼他“九命老叔”。
話說老叔6歲那年冬天,村里有一拉酒糟的馬車從家門口路過,生性頑皮的老叔就猴似的躥了上去。
災難就這樣降臨了。
那馬說不上為啥驚了,車翻了。那不是一般地翻,是整個車翻進了深溝,馬都被摔癱了。一車的酒糟把老叔實實在在地埋在里面。被甩出去的車老板大驚,爬起來沖進溝去,一個人就把車掫了起來。按說,一般人遇到這樣的事,肯定在劫難逃,必死無疑,可車被掫過來的瞬間,老叔又猴似的從酒糟里躥了出來。
又話說10歲那年,正值三伏,老叔口渴難耐,就蹲在村頭一口大機井邊弄水喝,結果一頭栽了進去。老叔不識水性,按說,一般人遇上這種情況,肯定在劫難逃,必死無疑,可老叔被人倒提著兩條小腿從井里提溜出來,控出滿肚子水后,仍然精神抖擻,活蹦亂跳地上學去了。
之后的40多年,我老叔一路刀光劍影,險象環生。
比如說,蓋房子從房梁上摔下來,摘梨從樹上掉下來,不止一次喝酒喝得滾了砬摔進溝,誤喝做豆腐的鹵水搶救幾天幾夜,總之最后的結局都是這樣的:他都是猴似的躥起來,該干啥干啥去了。
“九命老五”的稱謂由此而來。
生活中的老叔就像山野里的一棵草,生命蓬勃而充滿韌性。
直到如今,瘦小干枯的老叔,仍然走到哪里都不被人重視,但他的命卻比那些看上去光鮮的人要好得多。
比如說,他娶了一個比他高一頭的女人做老婆。
比如說,他是全村同齡人中唯一掙工資、有勞保的人。
再比如說,喜歡兒子,就一口氣生了仨,小兒子居然是老嬸做了絕育手術后又有了的。
前些日子我回家,迎面撞上老叔騎著自行車,驚險雜技般地從山路上沖下來,見我又停不住,一下子撞到了樹上。他爬起來,跟驚魂未定的我打招呼:“大侄子回來啦,這車沒閘。”
回家后,又聽父親講述老叔驚險新傳,這新傳已經具有時代感了。
比如說,他喂養的毛驢死了,他跟那頭得破傷風的驢相處多日居然平安無事。
再比如說,他被假古董販子騙去了兩千塊錢,而依然保持堅強的神經,吃喝照舊,睡得麻香。
這回,村里人又在他原有的綽號前加上了定語:“沒心沒肺之九命老五”。
其實,老叔有心有肺,他生活的煩惱和普通人一樣多。房子該修了,兒子該娶媳婦了,他的牙掉了好幾顆該去修修了,老伴兒身體有病也該進城瞧瞧了。按說,諸多煩惱落到誰身上也肯定會愁云滿面,但我所看到的老叔,依然是精神抖擻的、風風火火的、笑聲笑語的。
那天清晨,又見老叔爬到房后的樹上摘桑葚,父親就笑曰:“你老叔哪只九條命呀!”老叔也在樹上大笑:“估計我這輩子是九十條命,大伙兒給我少算了八十一條呢!”
現在,甭管有風沒風,有雨沒雨,老叔還過著他快活的猴日子,房還在上,樹還在爬,酒還在喝,驚險的鬧劇還在不斷上演。
這,著實讓人看了眼饞,也看得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