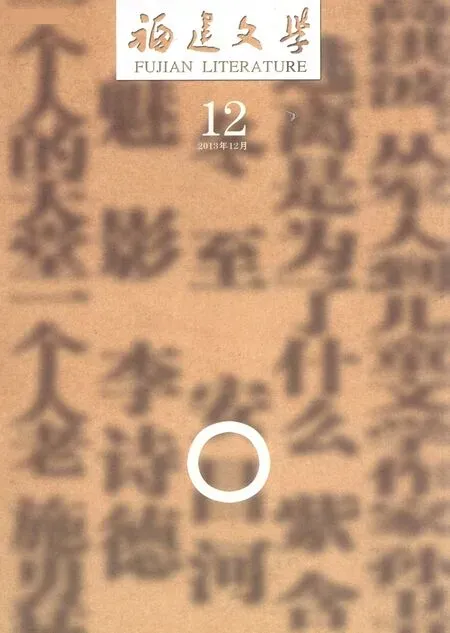“魅影”背后的隱喻意義——讀小說《魅影》
□ 劉 忠
生活中總是有一些神鬼莫測的事情發生,干擾人生方向的選擇和目標的實現。習慣上,我們將其統稱為命運,其最大特點就是飄忽不定,拒絕解釋。就常人而言,人們很樂意跟著“好運”一起走,而不愿意被“壞運”拖著走。但是,對于文學創作來說,命運的神秘莫測、飄忽不定不僅不是缺點,而是一個瑰寶、一處富礦,它契合了文學創作倚重的不確定性,給接受者預留了無盡的想象空間。小說《魅影》表現的就是這一命題,一個飄蕩在村莊之上、深藏在村民心里的魅影。
在中國文學中,鄉土文學一直居于主導地位,源源不斷地為作家提供創作動力,并與不夠發達的都市文學形成鮮明對比。一直以來,鄉土敘事存在兩種不同的傳統,即回憶、贊美式和批判、反思式,前者的代表是周作人、沈從文、汪曾祺等,后者的標桿則是魯迅、老舍、高曉聲等,鄉土小說創作基本上都搖擺于這兩種敘事之間,不同的僅在于風物人情的迥異和作家主體精神的強弱上。置于鄉土視域來看,《魅影》走的是批判、反思一路,屬于“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魯迅《故鄉》)的一類,與魯迅、老舍、高曉聲等人的反封建、國民性批判不同的是,《魅影》的視點和重心明顯下移,從宏大主題轉換為私人敘事,從批判愚昧保守到反思欺騙算計,思想史的說教成分減少,審美表現的藝術成分增加。
《魅影》的發生背景是“文革”后期,農村土地改革即將進行,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列入議事日程,一切都還處在混沌、觀望、不確定的中空期。村長六指、村民中興大伯、唐老爹等人利用迷信、巧合、讖語來蠱惑人心、中飽私囊,演繹了一連串匪夷所思的活劇,其間穿插菩薩送子、菩薩打架、幽會偷情、賽龍舟狂歡等詭異十足的事件元素,輔以魔幻色彩的動物群體求偶的象征,把隱藏在鄉土皺褶深處的種種劣跡描畫、揭示出來,撕毀給人們看。當然,這種描摹、反觀是冷靜溫情的,而不是金剛怒目的。
“雜姓灣”,中國鄉土版圖上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莊,一群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鄉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居住空間的封閉進一步上升為思想精神的隔絕,荒寒破敗的生活方式很難尋覓到一絲生氣。從理性的角度考慮,逃離也許是擺脫鄉土孤寂、隔絕生活方式的最好選擇,魯迅、徐欽文、許杰是這樣,莫言、劉震云、閻連科也是如此,莫言回憶1976年參軍離開故鄉的感受,說“它耗干了祖先們的血汗,也正在消耗著我的生命,我感到我如一只飛出了牢籠的鳥”。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說:“我已經發現,認識自己故鄉的辦法是離開它;尋找到故鄉的辦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頭腦中、自己的記憶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個異鄉去找它。”然而,“雜姓灣”不這么想,六指隊長、忠興大伯、唐老爹、蕎兒、王引寶們也不這么認為,同時,社會語境也沒有為他們提供應有條件。雜姓灣的日子平靜如水,泛不起一絲漣漪。有一天,村西頭多年不孕的蕎兒懷孕生子了,蕎兒的示范效應在引發種種非議的同時,也迎來一群群外地男女,他們莫名其妙地涌向忠興大伯家,央求忠興大伯“送子”,由此,拉開了雜姓灣“求子”、“送子”的神話大幕,有人為之欣喜不已,有人為之苦惱萬分,亦有人在暗中盤算,從中漁利。既是人造神話,自然就有人為戳破的時候,新菩薩唐老爹的降臨、兩個菩薩月夜打架、六指隊長導演的賽龍舟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一步步地把“送子”把戲的魅影勾畫了出來。最后,賽龍舟狂歡的人潮搶走了蕎兒的兒子,徹底顛覆了整個“送子”、“求子”神話。雜姓灣一切復歸平靜,不同的是村里多了一個女瘋子,忠興大伯家的外墻上又被刷了一層新標語:基本國策,不可動搖,妻子王引寶的那句讖語“一胎刮,二胎扎,三胎四胎永不發”成為了事實。
小說故意虛化社會、政治背景,把一個非理性、狂亂的時代虛化,借用一個不乏戲謔、魔幻的“生育”故事,來隱喻鄉土肌理中的偽善、奸邪,鄉村并不意味著美好、單純,也有丑惡、繁雜;村民遠非都是淳厚、善良,亦有虛偽、狡黠,甚至是邪惡。從蕎兒的“意外”生子到村民的“求子”再到蕎兒的“失子”,始終有一張無形的神秘之手,一個神秘莫測的魅影,導演著一幕幕悲喜劇,無時不在,無處不有。這“魅影”飄蕩在雜姓灣,也游走在其他不知道名字的地方。套用一句思想史說法,就是“啟蒙是一個未完成的話語”。作者李詩德很巧妙、很藝術地把這一主題意蘊表現了出來。
人物塑造上,《魅影》做到了個體和群像的統一。無論是敘述送子迷信活動還是描摹賽龍舟狂歡,抑或是表現兩個菩薩打架的荒誕,舞臺上演繹的既有個人又有群像,老謀深算的六指隊長、狡猾迷信的忠興大伯、善良又有心計的蕎兒、見風使舵的唐老爹……一個個人物形象或清晰或模糊,組成了一個縱橫交織的人物譜系,他們或者是魅影的受害者,或者是魅影的制造者。鄉村的“小”反襯出人心的“大”,生活的單調凸顯魅影的神秘難測、迷信思想的根深蒂固。
結構方式上,《魅影》情節相對簡單,以“魅影”統攝其間,趣味性、魔性十足。不滯留于鄉土小說常見的風物人情描寫,而是圍繞主旨剪裁取舍,月桂樹顯靈、賽龍舟儀式的狂歡、動物求偶的熱烈……無不環繞于“魅影”四周,氤氳著一種詭異的氣息,助推“生育崇拜”情節的展開,為“魅影”提供足夠大的物理空間和心理距離。
人們常說,好的語言自己會說話。《魅影》語言不僅不“魅”,而且很“粗”,口語、俗語、俚語充斥其間,平白得晃眼,干脆得讓你仿佛聽到了雜姓灣人們的聲音,看見了他們的面容。“封閉的雜姓灣本來就不嚴實的外殼,就這么被一群不速之客輕易地擠碎了,就像一只雞蛋被打破之后,蛋青蛋黃混在一起,攤在哪里都不好收拾。”“灣子里的早晨,最初的一道風景線并不是日出。似亮非亮時,一去二三里的公雞叫聲此起彼伏,逐漸沸騰成一鍋爛粥。公雞的聲音停歇后,母雞起床了。母雞起床的聲音顯得瑣碎,窸窸窣窣,沒有公雞的干凈利落,有些稀里糊涂。”……如此這般洗練的文字扎根鄉土,深入到人物個性肌理。駕馭這樣的文字要緊的是功夫,是收放自如、準確到位的語言功夫。不裝,操著滿嘴“雜姓灣腔調”的忠興大伯、唐老爹、六指隊長,讓你咂摸出那種鄉土味十足的“迷信”氣息,品味出滲透著強烈權力意識的鄉紳傳統。不矯,祛除繁文縟節,了無偽飾,剩下的是入情入理的文字,寫活一個村莊、一群村民。
總的來說,小說在“魅影”的隱喻意義開掘、人物塑造、結構安排、語言表現等方面顯示了純熟、高超的一面,盡管其中魔幻、戲謔成分多了些,像菩薩打架一節更是有點想當然,但瑕不掩瑜,就像小說的名字《魅影》那樣,作者以其特有的方式為我們呈現了鄉土、鄉民粗糲的一面,讓今天的讀者們記住還有另一個空間、另一群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