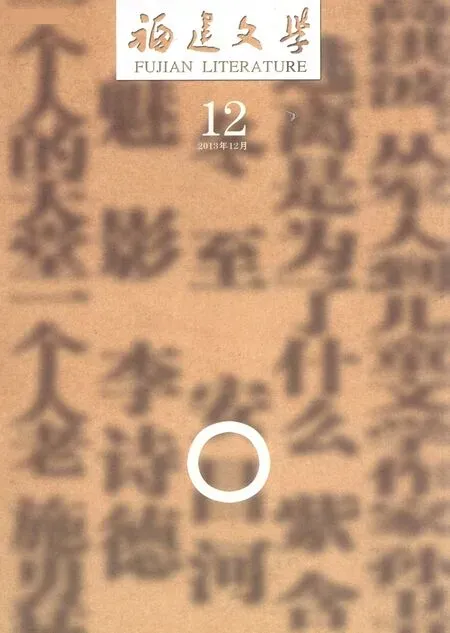詩的外衣(創作談)
□施勇猛
詩的外衣(創作談)
□施勇猛
有一只飛蟲它飛來飛去,不知道它在找什么。我盯著這只飛蟲,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知道了也沒有意義。在一只飛蟲的世界里,飛著生,飛著死,這就是它的全部。
詩也一樣,我根本不想知道什么叫做詩,假如詩也能飛,也必定飛著生飛著死。飛是自由,一種活著的狀態,也是死的狀態,或者根本沒有狀態。很久以前,聽朋友談詩歌,總覺得與詩歌無關,無非是喜歡和朋友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人總是開心的,會忘記很多東西,至少會忘記一些愁緒,會忘記孤獨。
所謂詩歌對于我,就是這樣,我所經歷過的,所能想到的,把它寫出來,這樣,人生的憂郁和孤獨,就會忘記,我就會開心,就讓所謂的詩歌幫我記著,或者忘了,就由它吧。
在這個朋友、愛情都需要驗證的年代,我們還有多少東西可以信任永久,可以忠貞不渝,可以無畏付出?活在這世上,生命是一種過渡,一次燦爛絢麗的綻放,又何必用什么來證明我們的存在。詩也如此,它無法證明什么。詩火熱冰冷,孤獨無情,詩是一種軌跡,心靈軌跡,一種證明心靈曾經存在的方法,僅此而已。
正如我看見的一只飛蟲,飛得緩慢的時候,我們都有殺了它的想法。一個微不足道的生命,在人間往往被漠視。正如我們,在時間,在距離,在人心里,也許也飛得緩慢,飛得那樣細微,,細到無聲,細到看不見自己在飛。我們就是這樣,以為走在人間,其實已飛出人心。所謂的詩歌,是我們心靈世界的錯誤,是變異,是一切美好一切丑惡,一切我們想忘卻忘不了的事。詩本身沒有對錯,錯的是我們。我們相信永遠,相信美好,相信堆砌在我們身邊的真實,但就是忘了誰會相信我們,我們還能相信誰。
在我所能理解的世界里,是一個被簡化了的世界,只剩人、事、物。一個精確計算的世界,有著異乎尋常的優雅和從容,愛、恨、忠誠、背叛,都有著精確的刻度。我所理解的世界,每一天都試圖感動我,或者試圖說服我。我的世界充斥著高尚和卑微,憐憫和絕情,充斥著倒流的影像和幻覺。其實,這一切都是妄想,就是這樣,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舊了的蹤跡,有愛的痕跡,有無望的撫慰。
現在,我看見的那只小小的飛蟲,仿佛也不存在。我和這只飛蟲彼此互不干擾,彼此忘了存在。多好。正如所謂的詩歌,對于我,也不過如此,或者這個世界對于我,也如此。生命中的安慰,可能有,但不會時時有。拿什么來忘記生命中面對的所有奢華和盛宴,像一只飛蟲那樣隨心所欲。
誰把水揉碎了,讓一夜的城破了。這漫天的春雨,在燈的微光中,露出了短暫的面容。冰冷不是它的本意,短暫不是它的祝福。時間的永恒,讓我們飄蕩如雨。聚了,散了,像松開的命運,如此簡單,卻永遠猜不透。像一場戲的最后,有時候會下起小雨,那些無處可飛的飛蟲終于不見了,如同我所見到幻覺,一切轉眼成空。不管是一天一年或者一世,我們所謂的時間,和我們的名字一樣冰冷。在我眼里,所謂的詩歌,記不住所要想念的一切。
今天,我用我的方式愛這個世界。有人說在黑暗里,影子會離開我們,有人說在亮光里,光線會將影子趕出我們的身體,影子仍然想要離開我們。我們親愛的生活給我們的教訓是,你無論如何都無法將自己冰冷的影子變得溫暖,你無論如何都無法守住自己的影子。所謂詩歌,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借到的一個玩具,或者是一個自言自語的片段,可以讓我去看看心靈里還會有什么。
責任編輯 郭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