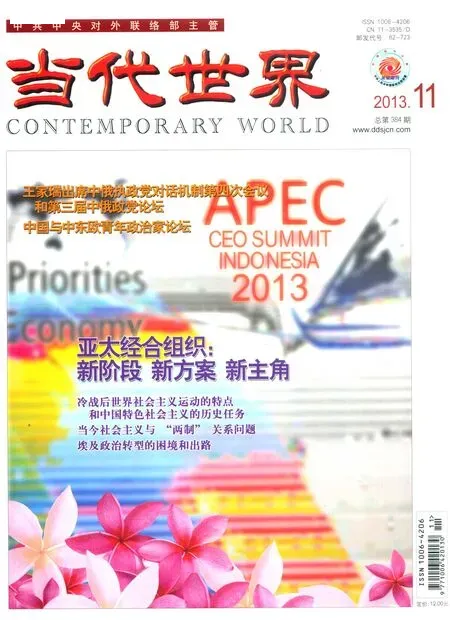日本因應美國戰略東移的舉措及其影響
沈雅梅/文
日本因應美國戰略東移的舉措及其影響
沈雅梅/文
從民主黨鳩山內閣到自民黨安倍內閣,日本對美國戰略東移的因應,經歷了一個調整、呼應、進而加以利用的過程,體現出較強的戰略連續性,表明日本因應美國戰略東移的基本思路是,在國際權力轉移特別是東亞力量結構發生轉變之際,對日美同盟關系進行再定義,重新確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定位,尋求對東亞地區秩序的重塑發揮主導作用。
一、日本對美國戰略東移的基本態度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后,全方位加大亞太戰略投入,迅速提升與中國和東盟的關系,日本擔心美國的亞洲政策“重華輕日”,將削弱日本在地區和國際上的影響力,鳩山內閣追求自主外交的努力就流露出對日美同盟關系的危機感。然而,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日本的政治安全利益訴求日益產生強大共鳴,日本外交逐步落回到日美同盟的軌道上。
(一)積極歡迎美國對亞洲安全事務的關注
日本戰略界的主流觀點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特別是軍事意義上的重返亞太,是日本的福音。日本可通過融入、配合該戰略,從而積蓄力量,內聚共識,外塑依托,為最終擺脫“戰后體制”、回歸“普通國家”創造條件。
首先,亞洲地區力量結構變動對日本造成沖擊,其希望獲得美國的安全保護。2010年1月,美日就《日美安保條約》簽署50周年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兩國“為確保日本的安全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將繼續構建不可撼動的同盟關系。由于日美在亞洲和東亞的利益均在擴展,今后雙方的聯盟管理計劃將更多地在亞太地區展開。
其次,日本希望以美國盟友的名義承擔地區安全責任,拓展自身軍事空間。日本擔心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戰略收縮可能導致亞洲權力真空,影響日本安全戰略的實施。2012年1月美國《防務戰略指南》提出加大在亞太部署軍力的比重,打消了日方對此點的疑慮。日本希望與美國分攤負擔和責任,期待為亞太安全發揮更大作用,尋求軍事突破。
再次,日本輿論普遍認為,美國重返亞太是為了制衡中國的崛起,這一點與其不謀而合。日本防衛界指出,美國重返亞太不只是地緣意義上的外交議程調整,其本質是解除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戰場的戰爭動員,預示著美國防務戰略的根本變化,說明美國致力于應對新的安全挑戰。日本2010年《防衛計劃大綱》及2011年以來《防衛白皮書》、《外交藍皮書》等文件均渲染“中國威脅”,試圖把中國塑造為日美的共同安全挑戰。
(二)迫切尋找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定位
日本尚不清楚自身應在“再平衡”戰略中扮演何種角色。2013年2月,安倍晉三首相訪美時在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演講開篇即宣示:“日本永遠不會是一個二流國家,”它將扮演好“規則的促進者,共同利益的捍衛者,以及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盟友和伙伴”等多重角色,這表明日本面對美國的“高調重返”,正在積極思考將何去何從。
對日本而言,確立自身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定位需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第一,加強日美安全戰略協調。美國2010年2月《四年一度防務評估報告》、2012年1月《防務戰略指南》及日本2010年12月《防衛計劃大綱》等綱領性文件,為日美安全戰略協調奠定了基礎。但日本注意到,美國正在經歷財政削減計劃、亞洲外交班子變動及中東局勢動蕩等內外不確定因素,因而對“再平衡”戰略的可持續性抱有懷疑,希望加強與美國的政策溝通和協調。
第二,日本關注“再平衡”戰略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奧巴馬第一任內在“再平衡”框架下對中國的定位偏于消極、負面,特別是2012年美國《防務戰略指南》把中國列為對美國軍力輸出構成挑戰的“潛在敵手”。據此,日本安全戰略的針對性也更加明確,重視“中國因素”。以前民主黨外務大臣前原誠司為代表的強硬派甚至認為,既然中美之間已經上演一場霸權爭奪賽,日本就應當在“日美聯合對抗中國崛起的威脅”這一構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日美如何在美軍前沿部署方面開展合作。日本主動配合美軍實現前沿部署在“地理上更廣泛,行動上更靈活,政治上更具可持續性”。例如,日本認同美海軍陸戰隊移師關島等地有助于美國更好地應對地區突發事件。日本還向美軍在遭遇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的作戰能力提供支援。2012年4月朝鮮宣布發射遠程導彈計劃后,日本向沖繩等西南諸島及附近海域部署驅逐艦,把駐沖繩美軍納入其保護范圍。
二、日本因應美國戰略東移的舉措
為了影響并利用美國的戰略東移,日本加緊向美國靠攏,積極參與到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的制定和完善過程中,使其最大限度反映自身利益和主張,并在日美同盟的庇護下推動國家安全戰略轉型,提升對國際和地區事務的發言權。
(一)深化日美同盟
日美同盟關系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接觸的“基石”,為美國重返亞太起到助推作用,有利于提升日本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意義。日本政界主張加強日美同盟之聲日益高漲。2010年11月,鳩山繼任者菅直人與奧巴馬會見時強調,“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安全和繁榮的基石,”意味著對此前具有“脫美”色彩的外交路線的糾偏。2013年3月安倍訪美及首腦會談更是被日本媒體定性為“一次向國內外展示牢固日美同盟的重要會談”。
從軍事層面看,日本積極尋求與美國“全方位”合作,加速軍事一體化進程。具體的強化措施包括:討論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重新確定日美安保分工,著手建立美軍和自衛隊合作機制,強調為美軍提供戰時支援等。2012年2月,日美就駐日美軍整編計劃與基地搬遷問題分開執行達成共識,暫時緩解了各方矛盾。
此外,日本對美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TPP)的興趣,也成為日本強化日美同盟關系的一個重要環節。由于農業保護問題,日本國內尚未對TPP達成共識,但政府認為,加入TPP談判是符合日本長遠利益的重大決策。安倍內閣熱衷于TPP也不僅僅為了經濟利益,而是看重它對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
(二)發展自主軍力
美國重返亞太為日本軍力建設搭建了新的平臺。日本判斷,奧巴馬政府受國內經濟低迷和中東亂局牽制,實際用于應對中國崛起和亞太安全格局變動的精力和資源是有限的,會對自衛隊填補東海防衛權力真空抱更高期待。在日本與周邊國家的島嶼歸屬和水域劃界等爭端上,美國所提供的威懾也有限,日本需要強化自主防衛能力。
2010年10月,日本《防衛計劃大綱》提出“動態防務力”概念,把戰略關注從東北轉向西南,強調對日本本土及西南地區的防御,預示著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基于此,日本不斷擴充在西南各島駐軍,增加戰機潛艇,利用自身強大的海空軍力量,配合美軍“聯合作戰介入”概念的實施,抗衡所謂中國向西太平洋的“滲透”。
日本還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大力推動強軍計劃。2013年初,安倍內閣通過新國防預算,總額達4.77萬億日元(543億美元),比上年度增長0.8%,是近11年來軍費的首次增長。國防開支為自衛隊添置的武器極具攻擊性,包括F-35聯合攻擊戰斗機及兩棲突擊車。此外,僅在2012年一年當中,日美開展聯合軍事演習就多達16次。2013年6月,日本首次集結陸海空三軍精銳,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實施奪島聯合軍演,顯示出自衛隊正在加快建設具有“海軍陸戰”功能的精銳力量。在美國的促動下,日本還大幅放寬“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則”,借口出售用于救災和基礎建設等任務的裝備,推動日本防衛裝備的民用出口,為扶助軍工產業、提升裝備水平開綠燈。
(三)構筑地區“民主安全網”
日本重視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密切合作,主動塑造地區秩序。在雙邊層面,日本把美國在地區的主要盟友和伙伴——菲律賓、越南、印度、澳大利亞等列為自己的重點合作對象,且影響交往對象的手段已不再限于純粹的經濟外交。例如,日本提升與菲律賓、越南的戰略伙伴關系,承諾通過“活用”官方發展援助,幫助菲、越加強海岸警備隊裝備,擴大防務合作。為加強對東南亞的影響力,安倍上任后僅七個月里就三次到訪東南亞,訪問了東盟十國中的七個國家,并提出對東盟外交的五項原則,把這作為推行“價值觀外交”的主攻方向。
在多邊層面,日本以日美同盟為橋梁,加強美日印、美日澳等三邊軍事合作關系,構筑網絡化安全體系。日本還把參加TPP作為加強經濟規則建設、實現東亞繁榮與穩定的重要一環提出來,使TPP談判與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同時進行,力圖打造以美日為主軸的地區貿易圈,謀求對中國、韓國等地區主要經濟體的優勢。
由于美國新軍事戰略指南提出的美軍未來發展重點在海空領域,而日本在東亞海洋問題上與中國、韓國、俄羅斯均有島嶼之爭,它借機推出聚焦安全的海洋戰略,希望主動塑造東亞海上秩序。為此,日本傾力升級現代化海洋軍事機器,不斷在大中型戰艦建設方面取得突破;積極開展海洋外交,與越南、菲律賓等南海周邊國家建立海上安全對話合作機制;還頻頻發出建立東亞多邊海洋安全合作機制的倡議,為建立美、日、印(度)、澳“民主安全菱形”造勢。
(四)推動“聯美制華”
中日實力對比變化給日方造成心理失衡狀態,使日本遏制中國的意圖最鮮明。日本努力向美國說明中國是威脅,指出中國的崛起主要在軍事領域,并已發展為影響亞太安全環境的核心因素;美國對華“接觸”政策能否奏效,取決于美日能否成功對沖中國;美日應共同塑造地區安全環境,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國家傾向于合作性而非對抗性的關系。實際上,日本在加強日美同盟、發展自主軍力及經營地區外交等各個政策選項中,均有聯手美國、打造對沖中國崛起的安全秩序的訴求。
以中日釣魚島爭端為例,美國一度試圖通過拉偏架,介入東亞安全事務。可以說,美國重返亞太,為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鋌而走險提供了外部條件。應日本要求,駐日美軍近兩年來在沖繩部署了24架“魚鷹”機,由于其作戰范圍是600公里,能覆蓋到距沖繩450公里以外的釣魚島,此舉被認為對華形成威懾。
三、日本對美戰略回應的影響
在日美的新一輪亞太互動中,兩國或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但日美的不平等地位及日本的政策缺陷決定了日本的獲益空間是有限的。
(一)美日聯盟存在廣泛挑戰
美國把美日同盟作為進行地區參與的重要基礎,希望東亞存在低烈度的緊張關系,從而為其積極介入東亞事務、管控地區力量平衡提供現實依據,但這一現實依據必須是在美國掌控之下的,而不是能被他國任意擴大的。日方對美則有不好的記憶,歷史上曾多次被美國“越頂外交”傷害,國內民意對美國仍有不信任感。在重返亞太過程中,美國不愿被盟友“綁架”卷入地區沖突,對中日釣魚島問題的走向深感焦慮,坦言要“避免造成給日本撐腰的印象”,把工作重點調整為以外交途徑管控釣魚島局勢。這令日本感到被冷落,擔憂中美走近,甚至猜疑美國向中國“出賣”日本利益。就TPP談判而言,日本加入其中成本甚高但經濟收益并不明顯,從長遠看也可能激化美日經濟矛盾。
(二)日本亞洲外交面臨“信任缺失”
日本一相情愿地認為,通過“價值觀外交”聯合起來的地區國家會與日本一樣對美國亦步亦趨,共同編制所謂對華包圍圈,但地區現實與此大相徑庭。比如,印度外交追求平衡和自治,不會答應圍堵中國。東盟國家與中國發展關系有政治、經濟和地緣上的優勢,不會受日本操控。相反,日本走軍事大國之路,與美國頻繁軍演,極力推動修憲,缺乏歷史反省等,加劇了地區的緊張氛圍,加深了中、韓等鄰國對日本未來走向的懷疑,難以與日本建立互信關系。由于日本挾美自重,反復刺激地區國家的敏感神經,它在亞洲得不到信任,更難以成為地區的領導者。
(三)日本對華政策選項受到擠壓
日本對華政策取向與中美關系有較大關聯。有一種傾向認為,中美之間越對立,日美關系就越重要,日本在對華關系中就越占據主導;而當中美接近時,日本則需避免自身利益被中美之間的交易所吞沒。日本自2010年以來在釣魚島問題上先后炮制“撞船”事件、“購島”鬧劇等,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自以為有美國的庇護。實際上,中日、中美、日美之間密切的經貿聯系及獨特的三角結構決定了日本無法回避與中國交好的選項。隨著美國亞太戰略逐漸成熟,美國有望進一步增強對華政策的靈活性,對日本的期待將更多在實現經濟復蘇和共塑國際經濟秩序方面。日本外交需要在中美之間找到準確的定位,否則其對華政策的選擇空間和回旋余地將越來越小。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部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魏銀萍)
[1] Noboru Yamaguchi,“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U.S.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sia Policy, No.15, Jan. 2013. p. 7.
[2]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 22, 2013.
[3] James Politi, “US weighs trade pact with Japan”, Financial Times, Apr. 25, 2013, p. 4.
[4]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27,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