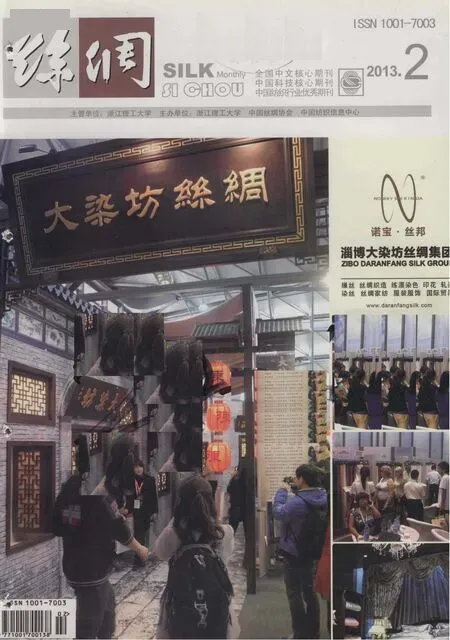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視角下的畬族服飾調(diào)查研究
陳敬玉
(浙江理工大學(xué)服裝學(xué)院,杭州310018;蘇州大學(xué)紡織與服裝工程學(xué)院,江蘇蘇州215000)
畬族是中國(guó)典型的散居民族之一,只有民族語(yǔ)言沒(méi)有自己的文字,隋唐之際就已居住在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qū),宋代才陸續(xù)向閩中、閩北一代遷徙,約在明清時(shí)開(kāi)始大量聚居于閩東、浙南等地山區(qū)[1],現(xiàn)在浙閩兩省的畬族人口占全國(guó)畬族總?cè)丝诘木懦梢陨稀.屪迦嗣裨诮甑陌l(fā)展歷史中創(chuàng)造了以“鳳凰裝”為代表的獨(dú)具特色的民族服飾文化、審美認(rèn)同和服飾制作工藝。服飾作為物質(zhì)文明、審美情趣和精神寄托的重要載體,以非文本的方式傳載著千年畬族的文化和歷史,浙閩地區(qū)的畬族服裝制作、銀器服飾品制作,以及彩帶編織等傳統(tǒng)技藝相繼被列入省級(j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區(qū)的畬族服飾存在一脈相承的延續(xù)性,又具有各自地域文化差異的獨(dú)特性。隨著經(jīng)濟(jì)文化縱深發(fā)展,現(xiàn)代文明沖擊帶來(lái)的文化趨同使民族文化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多元性的變化,現(xiàn)代化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逐漸進(jìn)入畬族村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shí)對(duì)傳統(tǒng)服飾習(xí)俗產(chǎn)生了一定的沖擊和影響。
1 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視角下的畬族服飾文化
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者賴(lài)斯認(rèn)為,民族藝術(shù)的傳統(tǒng)之所以能夠成為活生生的存在并發(fā)揮持久的影響力,是歷史構(gòu)成、社會(huì)維護(hù)、個(gè)體的創(chuàng)造與經(jīng)驗(yàn)體會(huì)等幾方面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民族服飾作為民族藝術(shù)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承載著民族歷史遷移、社會(huì)意識(shí)表達(dá)及手工制作者的個(gè)體創(chuàng)造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民族服飾本身具有固態(tài)的物質(zhì)性及制作工藝、文化傳承的非物質(zhì)性二元化特征。在保護(hù)傳承的過(guò)程中,應(yīng)當(dāng)一方面打破現(xiàn)有割裂的地域性研究格局,針對(duì)其物質(zhì)性特征,建立系統(tǒng)的博物館式的陳列進(jìn)行固態(tài)保護(hù);另一方面針對(duì)其非物質(zhì)的文化特征,從傳承人機(jī)制和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入手,建立活態(tài)文化保護(hù)機(jī)制。畬族服飾文化在信息爆炸、文化融合的當(dāng)今社會(huì),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濡化與涵化的問(wèn)題。文化濡化的作用表現(xiàn)為時(shí)間上的連續(xù)性,它使畬族群體的核心價(jià)值觀、宗教信仰、思想意識(shí)、行為方式能夠同服飾文化綿延不斷地傳給下一代,推進(jìn)傳統(tǒng)的薪火相傳,最終實(shí)現(xiàn)各種特有的文明方式的世代延續(xù)[2],可以保持文化傳遞的連貫性;涵化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發(fā)生變遷,引起一方適應(yīng)或抗拒另一方的文化,最后導(dǎo)致兩種文化的變遷和融合過(guò)程[3],其重要作用在于保持文化傳遞的變遷性,涵化深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文化的差異性。民族服飾的傳承與發(fā)展實(shí)際上是在兩者不斷交互作用下進(jìn)行的。
畬族在長(zhǎng)期的歷史遷移和民族發(fā)展過(guò)程中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性,尤以畬漢雜居形態(tài)為多。畬族人民學(xué)習(xí)漢族先進(jìn)經(jīng)濟(jì)文化的同時(shí),民族間文化的差異性隨著民族融合和經(jīng)濟(jì)文化的一體化發(fā)展正在逐漸消弭。在文化趨同的大潮下,畬族服飾文化亟需保護(hù)性整理和傳承研究。筆者進(jìn)行的田野調(diào)查走訪中發(fā)現(xiàn):雖然一些畬族服飾制作工藝被當(dāng)?shù)卣J(rèn)定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進(jìn)行保護(hù),但是,當(dāng)下各地民俗文化及手工技藝的表演式生存所暗含的危機(jī)更應(yīng)引起重視。對(duì)于傳統(tǒng)手工技藝而言,生活化、生產(chǎn)化保存才是維持其生命力的最佳方式,其藝術(shù)形式的傳承延續(xù)比單純的展示表演更具有保護(hù)意義。當(dāng)代社會(huì)中,畬族傳統(tǒng)服飾文化和服飾習(xí)俗產(chǎn)生分化,一部分隨著畬民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消褪,另一部分則在現(xiàn)代文明的影響下經(jīng)歷著轉(zhuǎn)化和重構(gòu),成為地方文化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重要的人文資源。所以,從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應(yīng)該在畬族整體的文化環(huán)境之下分析畬族服飾,在描述服飾特征的同時(shí)著重關(guān)注民族服飾的相互影響和變化。20世紀(jì)90年代開(kāi)始就有學(xué)者對(duì)包括服飾、語(yǔ)言在內(nèi)的一些畬族風(fēng)俗習(xí)慣的消失提出了思考,認(rèn)為是畬漢雜居自然同化的結(jié)果[4]。隨著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文化縱深發(fā)展,這種現(xiàn)象愈發(fā)明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與藝術(shù)遺產(chǎn)正成為一種人文資源,被用來(lái)構(gòu)建和產(chǎn)生在全球一體化語(yǔ)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shí),同時(shí)也被活用成當(dāng)?shù)氐奈幕徒?jīng)濟(jì)的新的構(gòu)建方式,它們不僅重新模塑了當(dāng)?shù)匚幕瑫r(shí)也成為當(dāng)?shù)匦碌慕?jīng)濟(jì)增長(zhǎng)點(diǎn)[5]。服飾是一個(gè)民族文化演進(jìn)的記載和社會(huì)價(jià)值觀念的縮影,對(duì)畬族服飾的研究應(yīng)該放置于畬族文化背景及民族發(fā)展的語(yǔ)境中予以解讀和闡釋?zhuān)瑢?duì)其的保護(hù)欲傳承也應(yīng)置于畬族文化背景下方才能保持其本色。另一方面也必須認(rèn)識(shí)到:服飾文化本身并非亙古不變,而是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人民審美意識(shí)形態(tài)發(fā)展及工藝技術(shù)發(fā)展而不斷變遷的,在保存服飾遺產(chǎn)的同時(shí)應(yīng)對(duì)其發(fā)展和演變進(jìn)行引導(dǎo),在傳統(tǒng)工藝延續(xù)與保存的同時(shí)順應(yīng)民族發(fā)展脈絡(luò),結(jié)合時(shí)代特征進(jìn)行合理發(fā)展。
2 田野調(diào)查中的畬族服飾
2.1 服飾形制
畬族的傳統(tǒng)服飾自成體系,據(jù)清朝李調(diào)元的《卍齋璅錄》記載,畬民“男女椎髻跣足”,衣尚青、藍(lán)色,著自織麻布[6]。
根據(jù)田野調(diào)查,現(xiàn)代浙閩地區(qū)的畬族服飾一般為藍(lán)黑色,男子服飾與漢族無(wú)異,女子服飾仍保留有濃重的民族特色,因地域不同而產(chǎn)生一定的差異。浙閩兩地的畬族服飾都是上下分體式,由花邊大襟衫、攔腰(圍裙)、綁腿及裙(或長(zhǎng)褲)組成,最大的差異在于被稱(chēng)為“鳳凰冠”的頭飾形制和花邊衫的邊緣細(xì)節(jié)上。浙江地區(qū)的鳳冠以綴珠式為主,福建地區(qū)以纏繞式為主。綴珠式鳳冠以竹片、石珠和銀器制成,已婚婦女佩戴。三角形鑲嵌刻花銀片的冠體象征鳳身,前面的立面為鳳頭,后面高高挑起的是鳳尾,耳側(cè)垂下一束石珠的末端墜有數(shù)片鵝掌形銀片象征著鳳腳。纏繞式與綴珠式不同,多以紅線夾雜發(fā)絲纏繞作為裝飾,未婚、新婚和老年女子的鳳冠在形制大小上稍有不同,以新婚年輕女子的最為艷麗。由于傳統(tǒng)鳳凰冠制作精致、造價(jià)較高且脫戴較為復(fù)雜,現(xiàn)代畬族女性在節(jié)慶活動(dòng)時(shí)多采用簡(jiǎn)化的鳳凰冠。簡(jiǎn)化的鳳凰冠以一絨布頭箍為主體,上有仿銀繡花裝飾和塑料珠飾,使用時(shí)戴在額前于腦后系帶固定即可,操作簡(jiǎn)便但制作粗糙。
浙江地區(qū)服飾式樣較為一致,以景寧式為代表,福建地區(qū)的畬族服飾主要分為福安、羅源、霞浦、福鼎四種類(lèi)別(表1),其中以羅源地區(qū)的服飾最為華麗,在民族認(rèn)定時(shí)被選為畬族服飾代表樣式。景寧彩帶傳人藍(lán)延蘭回憶父輩描述的傳統(tǒng)服飾為:女子上著彩條飾邊的大襟衣,多為五條飾邊寓意五谷豐登;腰部系有攔腰(形似圍裙,寬至兩側(cè)中縫,長(zhǎng)及外衣下擺,兩端以彩帶固定),下裝為筒裙。日常穿著長(zhǎng)度及膝的短裙以便勞作,節(jié)慶時(shí)盛裝為長(zhǎng)及腳面的長(zhǎng)裙,裙下(內(nèi))著綁腿,解放前畬民貧苦,多為赤腳或穿著草鞋,重大活動(dòng)著花鞋。這些描述與德國(guó)學(xué)者史圖博(H.Stubel)和李化民在《浙江景寧敕木山畬民調(diào)查記》中的記載基本相符[7]。傳統(tǒng)畬民的服裝從紡紗織布到染色裁衣均由女子完成,但自20世紀(jì)70年代后,畬民自己織布做衣服的情況就逐漸消失,均為裁縫制作或購(gòu)買(mǎi)成衣。目前在浙閩地區(qū)的畬村中還偶爾可見(jiàn)穿大襟衣扎攔腰的老年畬族婦女,50歲以下的人群中日常穿著民族服飾的現(xiàn)象幾乎消失。

表1 浙閩地區(qū)畬族服飾的形制式樣對(duì)照Tab.1 Comparison of shape and structure of costume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in Zhejiang and Fujian regions
在實(shí)地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福建福安、霞浦和福鼎地區(qū)的畬族服飾樣式相似度較高,均為右衽立領(lǐng)大襟衫,大襟處有紅色鑲邊和繡花,主要差異在于花邊衫的圖案裝飾及鳳冠的樣式。其中福安式樣的服裝大襟處為三角形繡花,意指高辛帝的半塊玉璽;霞浦與福鼎式樣大襟處繡花頗為飽滿,福鼎式樣的領(lǐng)口有兩顆彩色毛線制絨毛球。此三地的鳳冠較為相似,都是以紅繩摻入發(fā)絲盤(pán)發(fā)于頂。福建羅源式樣較為獨(dú)特且最為華麗,上衣為右衽交領(lǐng),自領(lǐng)口處向外排列多層花邊直至肩部,日常頭飾為紅色絨線盤(pán)繞而成的鳳冠,高聳于頂。浙江景寧式樣在服裝上不重刺繡而重鑲邊,以花邊衫和珠串鳳冠的樣式為典型特征。
2.2 服飾手工藝制品——彩帶
彩帶是一種歷史悠久流傳廣泛的手工藝織品[8],又稱(chēng)“攔腰帶、帶子”,是畬族服飾手工藝的代表。彩帶既具有服飾上的實(shí)用功能,又在畬族婚嫁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可以用于邊緣裝飾及固定攔腰、綁腿、背篼帶、褲帶等物件外,還是畬族青年男女的定情信物。畬族彩帶一般寬2.5~6 cm,多以白色棉線為底,中間用彩色棉線通過(guò)經(jīng)緯變化織成斜向排列的黑、紅、青、綠色幾何形字符圖案[9](表1中畬族婦女腰間所系白色織帶即為彩帶)。這些字符各有寓意,有的是受漢字影響演變而來(lái),有的是在本民族長(zhǎng)期生產(chǎn)生活中根據(jù)象形表意逐漸形成,如表2所示(根據(jù)彩帶傳人藍(lán)延蘭的記錄摘抄的部分圖案寓意)。按照傳統(tǒng)習(xí)俗,畬族男女定情之時(shí)女方會(huì)送上自己精心織成的彩帶作為信物,這一風(fēng)俗作為畬族服飾婚嫁文化的代表在大型歌舞表演《詩(shī)話畬山》中有精彩的表現(xiàn)。雖然“畬族彩帶編織技藝”已經(jīng)進(jìn)入浙江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遺憾的是現(xiàn)在年輕畬民中會(huì)織彩帶的越來(lái)越少,彩帶傳情的古老習(xí)俗也隨之逐漸淡化了。據(jù)1999年的資料,浙江彩帶傳人藍(lán)延蘭能回憶起的字符圖案有60余個(gè)[10],相隔十年,筆者走訪藍(lán)延蘭,她能記起的彩帶圖案僅剩17個(gè)。目前政府及文化單位都已經(jīng)意識(shí)到了彩帶的文化價(jià)值,也認(rèn)識(shí)到它所面臨的危機(jī),相繼組織了一些年輕人進(jìn)行學(xué)習(xí),在浙江景寧雙后降村還設(shè)立了畬族彩帶作坊。但新的學(xué)徒看不到彩帶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而僅憑興趣難以堅(jiān)持復(fù)雜細(xì)致的學(xué)習(xí),彩帶作坊也由于缺乏經(jīng)濟(jì)效益轉(zhuǎn)為服裝作坊了。這些精美的彩帶圖案和工藝在畬族婦女中一代代口手相傳至今,現(xiàn)在隨著學(xué)習(xí)織帶人數(shù)的減少和應(yīng)用空間的縮小,正面臨失傳的窘境。

表2 畬族彩帶圖案寓意Tab.2 The implied meaning of ribbon pattern of the She nationality
3 對(duì)服飾現(xiàn)狀的反思與建議
3.1 反思和警示
在田野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浙江省內(nèi)景寧畬族自治縣、桐廬莪山畬族鄉(xiāng)等地除了重大主題活動(dòng)和文藝演出,畬民日常生活中很少穿戴民族服飾(有時(shí)活動(dòng)中穿著的也不是沿襲本地的鳳凰裝),僅有極少數(shù)老人還保留穿大襟衣、系攔腰扎彩帶的習(xí)俗。福建一些山區(qū)偏遠(yuǎn)的村莊中有少數(shù)老婦人還保留著傳統(tǒng)發(fā)式發(fā)髻、在春秋季及節(jié)日期間穿著傳統(tǒng)服裝的習(xí)俗(冬夏兩季主要因面料厚度及舒適性原因而選擇現(xiàn)代服飾)。造成這種現(xiàn)狀的原因,一是由于老式盛裝造價(jià)高且少有裁縫師傅會(huì)做;二是年輕人不再愿意靜下心學(xué)習(xí)祖輩的刺繡、編織等手工藝術(shù);三是在現(xiàn)代時(shí)裝新潮沖擊下,年輕的畬民和漢族一樣穿新潮時(shí)裝[10]。現(xiàn)代表演和活動(dòng)中的畬族服飾隨著時(shí)代發(fā)展,從面料到工藝都有了許多變化,傳統(tǒng)的自織土布、麻布被現(xiàn)代滌棉混紡面料替代,刺繡和彩帶的花邊也變成了現(xiàn)代機(jī)繡花邊。筆者在一些民族服裝作坊甚至看見(jiàn)銀泡、絨毛飾邊等具有典型其他少數(shù)民族服飾特點(diǎn)的元素出現(xiàn)在當(dāng)代畬族服飾上,當(dāng)?shù)禺屆裉寡赃@些并非畬族傳統(tǒng)服飾元素,覺(jué)得好看便拿來(lái)用在民族服裝制作上了。在“三月三”歌會(huì)現(xiàn)場(chǎng)各地畬族參賽團(tuán)體均穿著盛裝出席,但仔細(xì)研究他們的服飾可以發(fā)現(xiàn),上衣的樣式有立領(lǐng)、無(wú)領(lǐng)、交領(lǐng)等不同式樣,下著長(zhǎng)裙、短裙、長(zhǎng)褲甚至連身裙,頭飾則以綴珠的鳳凰冠和紅絨布鳳凰冠為主,兼有筒帽、錐帽等樣式。除因各地畬族服飾本身固有的地區(qū)差異外,各地傳統(tǒng)服飾元素出現(xiàn)混淆是造成這種樣式混雜現(xiàn)象主要原因。
這種不同民族間、不同地域間的服飾元素雜糅現(xiàn)象有兩點(diǎn)值得引起反思和警示:首先是當(dāng)?shù)鼐用駥?duì)本民族服飾的自我意識(shí)比較淡漠,對(duì)于服飾中的異化元素并無(wú)排斥和警惕,覺(jué)得好看就拿來(lái)用,并沒(méi)有考慮到是否會(huì)給畬族服飾帶來(lái)異化。其次是不同支系的畬族服制已經(jīng)出現(xiàn)混淆現(xiàn)象。不同地區(qū)的畬族服飾元素由于民族遷徙和自身演變導(dǎo)致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又有共同的文化基因,現(xiàn)在由于缺乏引導(dǎo)和梳理導(dǎo)致同族不同支系之間的服飾混淆也應(yīng)當(dāng)引起足夠的重視。
3.2 建議與展望
民族服飾文化具有固態(tài)的物質(zhì)性和活態(tài)的非物質(zhì)性,在實(shí)際的保護(hù)工作中主要是通過(guò)博物館形式對(duì)傳世實(shí)物進(jìn)行保存和展示,以傳承人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形式對(duì)其文化和傳統(tǒng)技藝的部分予以傳承[11]。博物館雖然以固態(tài)的形式對(duì)服飾進(jìn)行保存,但不可僅以標(biāo)本示之,其物質(zhì)性的外表下蘊(yùn)含的非物質(zhì)文化內(nèi)涵才是民族服飾的生命源泉,因此合理的民族服飾保護(hù)必須要給服飾提供必要的生長(zhǎng)環(huán)境和發(fā)展空間。
傳承本身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傳遞和繼承。傳遞的方式不僅是生硬地封存,陳列于博物館的服飾僅僅是一種文化的標(biāo)本,作為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載體,服飾也應(yīng)該隨著社會(huì)和民族的不斷發(fā)展而進(jìn)化;繼承的方式多種多樣,可以在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創(chuàng)新繼承。在未來(lái)的畬族服飾保護(hù)傳承工作中,除了大力保護(hù)維系民族服飾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外,還可以通過(guò)保“舊”創(chuàng)“新”兩種手段并行。保“舊”即對(duì)傳世服飾遺存進(jìn)行系統(tǒng)性的整理、發(fā)掘和保護(hù),建立服飾資料庫(kù),并通過(guò)展示宣傳弘揚(yáng)民族服飾文化。創(chuàng)“新”則是結(jié)合服飾設(shè)計(jì)專(zhuān)業(yè)領(lǐng)域的力量,對(duì)畬族服飾進(jìn)行符合時(shí)代發(fā)展觀的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對(duì)于畬族民族服飾的現(xiàn)代轉(zhuǎn)化設(shè)計(jì)就是一種創(chuàng)新繼承的方式,可以嘗試和設(shè)計(jì)院校、機(jī)構(gòu)合作開(kāi)發(fā)視覺(jué)藝術(shù)產(chǎn)品,通過(guò)轉(zhuǎn)化設(shè)計(jì)使古老的服飾文化煥發(fā)新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出具有時(shí)代印記的服飾。在傳承過(guò)程中,教育是兼顧“傳”“承”的良好途徑,通過(guò)教育不但可以將民族文化的精髓傳遞給下一代,還可以鼓勵(lì)基于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
4 結(jié)語(yǔ)
民族服飾發(fā)展的歷程就是文化濡化與涵化兩種力量交替作用的過(guò)程,通過(guò)田野調(diào)查走訪對(duì)當(dāng)今畬族服飾的保留及穿著現(xiàn)象進(jìn)行了初步摸底,可以發(fā)現(xiàn)浙閩兩地的畬族服飾既存在對(duì)盤(pán)瓠文化和鳳凰崇拜的共同文化基因,也存在地區(qū)差異帶來(lái)的細(xì)節(jié)差異。這種差異應(yīng)當(dāng)成為各地的民俗特色,但必須警惕不同元素的混淆、雜糅情況。當(dāng)今社會(huì)經(jīng)濟(jì)一體化帶來(lái)的文化趨同現(xiàn)象應(yīng)當(dāng)引起警示,畬族的民俗、服飾、民藝等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研究不僅有利于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和服飾文化保護(hù)傳承之間的共生和良性互動(dòng),而且可以為設(shè)計(jì)應(yīng)用提供靈感來(lái)源和設(shè)計(jì)元素,通過(guò)保護(hù)性發(fā)掘和整理、經(jīng)濟(jì)開(kāi)發(fā)和服飾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等方式維持民族服飾文化健康發(fā)展,保持中國(guó)民族文化多樣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有重要的意義。
[1]李艷.加強(qiáng)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弘揚(yáng)民族優(yōu)秀文化:淺談畬族文化的現(xiàn)狀與保護(hù)[J].科技創(chuàng)新導(dǎo)報(bào),2008(5):196.LI Yan.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excellent culture: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tection of She nationality culture [J].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2008(5):196.
[2]孫芳.文化濡化與場(chǎng)域視閾下的大學(xué)生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體系教育探析[J].道德與文明,2009(4):83-85.SUN Fang.Analysis on culture change and field affect in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J].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2009(4):83-85.
[3]劉秀麗.基于文化保護(hù)與傳承的旅游工藝品開(kāi)發(fā)[J].江西農(nóng)業(yè)學(xué)報(bào),2010,22(5):207-208.LIU Xiuli.Study on culture tourism handicraft's c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J].Acta Agriculturae Jiangxi,2010,22(5):207-208.
[4]王克旺.畬族一些風(fēng)俗習(xí)慣消失的思考[J].麗水師專(zhuān)學(xué)報(bào),1998,20(1):50-51.WANG Kewang.A thinking of some customs'disappearing of She nationality[J].Journal of Lishui Teachers College,1998,20(1):50-51.
[5]方李莉.從藝術(shù)人類(lèi)學(xué)視角看西部人文資源和西部民間文化的再生產(chǎn)[J].民族藝術(shù),2006(1):6-17.FANG Lili.On western human resour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olk culture from art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J].Ethnic Arts Quarterly,2006(1):6-17.
[6]李調(diào)元.炳燭偶鈔&卍齋璅錄[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37.LI Diaoyuan.Bing Zhu Ou Chao& Wan Zhai Suo Lu[M].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37.
[7]李化民.浙江景寧敕木山畬民調(diào)查記[M]//中國(guó)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huì)議景寧自治縣委員會(huì)文史資料委員會(huì).景寧文史:第4 輯,1989:1-5.LI Huamin.A Survey on Zhejiang Jingning Chimu Mountain's People[M]//Jingning History Material Council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Jingning's Literature and History:4th Album,1989:1-5.
[8]尹艷梅,朱寒宇,徐麟健,等.服飾手工藝在現(xiàn)代服裝中的設(shè)計(jì)應(yīng)用[J].浙江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27(1):84-86.YINYanmei,ZHUHanyu,XULinjian,et al.The application of clothing handicrafts in the knitwear design[J].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2010,27(1):84-86.
[9]陳敬玉.景寧畬族服飾的現(xiàn)狀與保護(hù)[J].浙江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28(1):55-58.CHEN Jingyu.The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of She's costume in Jingning[J].Journal of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2011,28(1):55-58.
[10]金成熺.畬族傳統(tǒng)手工織品:彩帶[J].中國(guó)紡織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9,25(4):99-106.JIN Chengxi.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sash of She ethnic group in China[J].Journal of China Textile University,1999,25(4):99-106.
[11]陳敬玉.民族服飾的固態(tài)保護(hù)與活態(tài)傳承:以浙江景寧畬族為例[J].絲綢,2011,48(5):48-50.CHEN Jingyu.Study on the solid protection and live inheritance of ethnic costume:take a case of She nationality in Jingning Zhejiang[J].Journal of Silk,2011,48(5):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