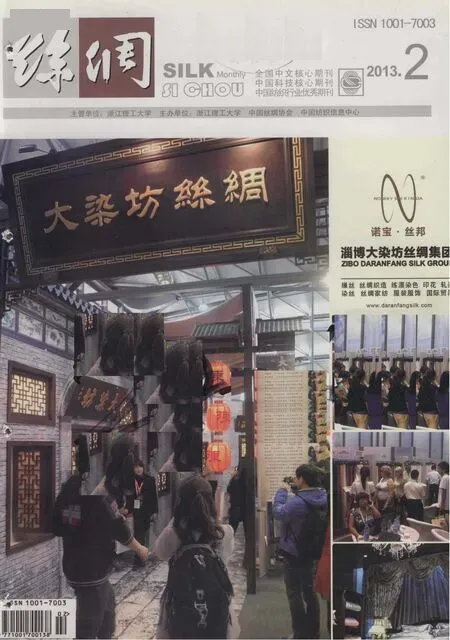“萬物有靈”宗教觀對佤錦土布圖案的影響
王 靜,王宏付
(江南大學紡織服裝學院,江蘇無錫214122)
佤族是一個比較古樸的民族,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常常處于一種“物我混一”的狀態,認為是自然界賦予了他們生命和意識。于是在佤族先民看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植物和動物都被神化,成為了他們崇拜的對象,形成了“萬物有靈”的宗教觀。佤族織錦以其特有的圖案特征及色彩特征,體現了佤族人民的智慧與想象力,是中國少數民族織錦的一個重要品種。將“萬物有靈”宗教學說中對自然和動植物的崇拜,以圖案的形式表現在土布上,是佤族織錦的獨特魅力所在。關于佤族“萬物有靈”宗教觀和佤族織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宗教文化的研究[1]118,或者對佤族織錦的簡單紋樣和工藝流程的研究[2],鮮有對佤族織錦紋樣進行詳細解說,以及將“萬物有靈”宗教觀中體現的物體崇拜和織錦紋樣結合起來的研究。本文通過兩者的結合分析,深入研究其佤族紋樣的多樣性和文化寓意性,充分發揮佤族紋樣對現代工藝設計的借鑒作用。
1 佤族宗教——“萬物有靈”說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250中提到:“宗教是最原始時代,從人們關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佤族先民在漫長的原始社會階段,也產生了自己最原始的宗教觀念——“萬物有靈”。
“萬物有靈”宗教觀的形成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地理環境的閉塞。佤族居住在怒山山脈南端的阿佤山區,這里的山嶺海拔大都在1 000~2 500 m,多森林,多云霧,這種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你的情形,充滿了神秘氛圍,為宗教的產生提供了環境氛圍。2)主觀意識形態的作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4]384一書中提到:“當需要、恐懼、羨慕等種種心理交織在一起時,原始人類不僅不把自己同動物對立起來,反而在很多場合下愿意承認動物高人一等。”佤族原始時期,先民對于自然的力量無法應對和理解時,就會對大自然產生一種畏懼心理,先民們就會把其看作神圣的東西進行崇拜。對自然力的恐懼和不解是其產生的心理因素。
在這種“萬物有靈”的原始觀念下,佤族產生了一些獨具特色的原始圖案,如波形紋、十字紋、牛頭紋、菱形紋、松鼠牙紋、茅草紋等。每一種紋樣都代表著一種較抽象的觀念,這是佤族圖案的獨特之處。
2 宗教影響下的佤族圖案
2.1 自然崇拜
2.1.1 波形紋
波形紋源于人們對火的崇拜,是火具象圖案的抽象表達[5]。在佤族先民看來,火能夠給予人們熱量、溫暖和光明,具有驅散黑暗和一切鬼邪的威力。《司崗里》[6]77記載:“會取火后人類好生活……光明和溫暖掌握在人手中。”體現了佤族人民對火的崇拜,佤族人民對火崇拜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以摩擦取火的形式舉行的盛大儀式“新火節”。在《滇云文化》[7]374中記載:“祭祀火神是新年開始的重要宗教活動……是祈求新年萬事如意,幸福安康的一種形式。”
在佤族織錦圖案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波形紋樣,以并行的多條折線紋為造型,并以曲線伸展的長條出現,體現了佤族人民對火的崇拜(圖1(a)),更體現了日子長長久久的美好寓意。例如圖1(b)[8]135波形紋遵循了圖案的變化與統一,運用橫式二方連續將紋樣織成不同的色彩來體現圖案的變化,但相同的紋樣又將織錦完整的統一起來。波形紋樣使畫面整體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律動感,但又不失其統一性。

圖1 波形紋樣的演變Fig.1 Evolution of waveform pattern
2.1.2 十字紋
“十”字是佤族人民對太陽和星星的崇拜(圖2(a)),在“萬物有靈”的原始觀念下,佤族先民認為太陽是生命的源泉,也是雨水的吸附者,太陽體內蘊含著偉大的靈氣,是萬物眾生的制造者;而星星象征著繁衍與眾多,它們是太陽與月亮的兒女,佤族人民將代表太陽與星星的十字紋印織在織錦上一方面體現佤族人民對太陽和星星的崇拜,同時也是對自己兒孫后代宛若繁星的一種希冀。

圖2 十字紋的演變Fig.2 Source of cross pattern
十字紋樣在服飾上的運用帶有一定的巫術和宗教色彩。從圖2(b)[8]141所示佤族織錦上可以感受到這種氣息,紅與黑的搭配再加上象征太陽和星星的“十”字符號,使佤族織錦充滿宗教色彩。佤族人民穿上織有十字紋圖案的織錦,就會得到太陽和星星的保佑和庇護,使人民健康長壽,多子多福。佤族的十字紋一般是以單獨紋樣的形式出現,紋樣的特點又屬于單獨紋樣中的對稱紋樣,即圖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且能夠單獨的用于裝飾,其次圖案形象依中軸兩邊或依中心多向對稱。像十字紋這種對稱式單獨紋樣給人一種平衡的穩定的感覺,適合用于表現莊嚴、平和、穩重的氣息。
2.2 動植物崇拜
2.2.1 牛頭紋
牛頭紋代表著佤族宗教文化中的對牛的崇拜(圖3(a))。牛在阿佤人心目中是吉祥、神圣、高貴、莊嚴的象征。在佤族的創世神話中,人和動物都是母牛的后代,佤族是在水牛的幫助下才找到生命繁衍的地方[1]8。佤族創世史詩《司崗里》[6]43描述:“為什么巖佤人說話拗嘴拗舌?因為他們愛學牛說話。”可見佤族先民的語言也是向牛學來的,佤族先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深深打上了“牛”文化的烙印,牛在阿佤人的心里是勤勞、憨厚和善良的代表。佤族村寨的中央栽有“丫”形牛角樁,佤族一年一度的新米節節徽上的牛頭圖案無不反映了牛在佤族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圖3 牛頭紋樣的演變Fig.3 Evolution of ox-head pattern
牛頭紋樣在服飾上的應用一般也是采用單獨紋樣的形式,同時它也屬于單獨紋樣中的對稱紋樣。例如圖3(b)[8]67佤族男子上衣中間織制的牛頭圖案,以門襟為中心對稱軸左右對稱,同時以黑色為底色牛頭圖案采用紅色的印織方法,既體現了濃重的宗教氣息也彰顯了佤族人民對牛的崇拜。
2.2.2 菱形紋
菱形紋是佤族服飾最常用的一種紋樣。菱形紋中間加個圓點代表“小米雀”的眼睛,以此來表達佤族人民對小米雀的崇拜(圖4(a))。小米雀在佤族神話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佤族的人類起源文化中有這樣的記述:佤族的第一代神路安神和利吉神造了人后,把人放到了一個石洞里,并用石門封住洞口,人出不來。小米雀飛到石洞上啄起來,漸漸地石洞裂開了一條縫,里面的人用力一推,打開了石門,人就從石洞里走了出來。佤族人民認為小米雀挽救了人民的祖先,使得生命得到繁衍。因此佤族人民將小米雀作為他們的救命恩人進行崇拜。《司崗里》[6]179記載:“哎——哎——是黑米雀啄我們出來,我們要給它們吃地里的谷子,不要忘記,不要忘恩。”將小米雀的眼睛用菱形紋的形式織在織錦上,同時體現了佤族人民對小米雀的信仰之情。

圖4 菱形紋樣的來源及“七只眼”挎包Fig.4 Source of diamond pattern and the“seven eyes”bag
菱形圖案在佤族服飾的應用是極其普遍的(圖4(b)[8]135),它是由全封閉的一圈圈的菱形紋樣組成,圖案的排列形式主要是以一個菱形或多個菱形作為單元紋樣進行二方連續和四方連續的排列組合,圖案疏密有致,極富變化。如圖4(c)[8]142所示是佤族挎包上的“七只眼”圖案,即將用不同的顏色將菱形圖案以一定的秩序性織在挎包上,“七只眼”是佤族挎包極具代表性的圖案,美觀的同時也體現了佤族人民對小米雀的崇拜。
2.2.3 松鼠牙紋
松鼠在佤族先民看來是可愛、乖巧、馴良、勤勞、聰明、靈巧的,在佤族創世史詩中記載松鼠協助小米雀將阻擋人類走出洞口的老虎趕跑,將人類從石洞里救出。在佤族先民看來,松鼠同樣是人的救命恩人,并且松鼠的主要食物是杏仁、榛子等,由于這些事物都具有堅硬的外殼,所以佤族人民判斷松鼠的牙齒是極其鋒利的,佤族人民將松鼠的牙齒抽象成幾何圖形的形式織在織錦上(圖5(a))。一方面體現了佤族人民對松鼠的崇拜,同時也賦予了一種愿望即遇到困難與挫則時佤族人們能夠象松鼠牙齒一樣勇敢堅強。
松鼠牙紋(圖5(b)[9]129)是以松鼠的牙齒為題材提取變化而來。六邊形為基礎造型語言,以二方連續的形式出現,體現一種格律之美。這種紋樣以單獨紋樣的形式出現是比較少見的,一般將單位紋樣向左右或上下的方向進行擴散,排列比較集中,稠密,使其具有很強的秩序感。

圖5 松鼠牙紋的演變Fig.5 Evolution of squirrel teeth pattern
2.2.4 茅草紋
在佤族先民看來,茅草的生命力極強,象征剛直與樸實。在《司崗里》[6]111一書中提到佤族原始部落突發洪水,部落被沖毀,佤族神母帶領先民一路南巡,途經茅草之鄉,茅草為落難的先民解饑渴,使先民重新振作精神繼續前行,找到了可以定居的居所。在佤族先人看來,茅草在其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了佤族,是佤族的功臣,并奉以神來崇拜(圖6(a))。
茅草紋(圖6(b)[8]122)在織錦上的運用多采用二方連續散點式形式,它具有一定的節奏和韻律,符合服飾的形式美法則。例如佤族婦女筒裙上茅草紋樣散點式的分布形式將點綴的裝飾美與對茅草的象征之意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圖6 茅草紋樣的演變Fig.6 Evolution of thatch pattern
3 宗教影響下的圖案色彩
佤族崇尚紅色與黑色,圖案多數以黑為質,以紅為飾,基本保留著古老的山地民族特色。據史料記載,佤族對于黑色的偏愛是情有獨鐘的,這與他們的生活環境和風俗習慣是分不開的:佤族自古以來就是從事體力勞動的民族,在長期的風吹、日曬和雨淋中,練就了他們壯實的體魄和頑強的意志,同時造就了他們對黑色的敬仰與崇拜,形成了佤族在審美觀上的一大特點;佤族人民以紅作為裝飾,是因為紅色是血與火的代表,是威武、權貴和顯赫的象征。血代表著生命和勇敢,而火能夠給予人們熱量、溫暖和光明,具有驅散黑暗和一切鬼邪的威力。因此以黑為質,以紅為飾的民族特色一直被佤族人民延續下來。紅與黑的搭配在佤族人看來既帶有極其濃重的宗教色彩,也是莊穆、古樸的一種表現形式。
佤族色彩染料一般就地取材,以天然染料為主。紅色是用紫梗做染料,再加上酸性植物的水汁混合而成;黑色是先用藍靛草將其染成藍色,再用麻栗樹皮染成;少數的黃色和赭色則分別是用黃花煮水和麻栗樹皮熬水作染料,即可染成。有的村寨還會把白線埋在井邊泥塘,6到7天后會變成淡青蓮色[2]。對大自然作物的運用,體現了佤族人民的智慧。
佤族圖案的主要色彩是黑色和紅色,以黑為質,以紅為飾,是佤族服飾圖案的特色。例如佤族十字圖案的處理是以黑色作為底色,運用紅色加以襯托;牛頭圖案也是在黑色底色的基礎上織出來的。
4 佤族土布圖案對當代設計的影響
佤族圖案承載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其內容豐富、題材廣泛,為現代藝術設計提供了一定的視覺藝術資源。若將其很好地與現代設計相結合,利用它進行再創造,會使現代人群既能體驗到傳統圖案所傳遞的文化寓意和形式美感,又能收到一份具有強烈現代藝術氣息的視覺美感大餐[10]。表1是對其幾種紋樣進行的分析總結,將佤錦土布的實物進行紋樣結構剖析,使圖案更加形象地展現佤族宗教“萬物有靈”對自然和動植物崇拜。

表1 佤錦紋樣的造型分析Tab.1 shape of Wa brocade patterns analysis
佤族織錦紋樣是對不同種類的自然事物進行抽象變形來進行的編織,如火的抽象變形紋樣波形紋、太陽和星星的抽象變形十字紋、牛頭的抽象變形牛頭紋、小米雀眼睛的變形紋樣菱形紋、松鼠牙齒的抽象變形紋樣松鼠牙紋樣,以及茅草的變形紋樣茅草紋(表1),其紋樣的內容非常豐富,為現代設計提供了更加新穎和獨特的設計題材;其次是佤族圖案的民族寓意和意境,可以豐富現代設計的內涵。將在佤族宗教觀“萬物有靈”影響下的織錦圖案運用到現代設計中,可以使設計實現對美的創造,更加豐富地表達藝術思想,從而達到實用功能和精神享受的高度統一;佤族圖案色彩紅與黑的運用是一種比較和諧的色彩搭配,它會顯示出與鄰近色搭配效果不同的色彩和諧,這種富有特色的配搭方式也是值得現代設計師借鑒和創新的。
5 結語
通過對在佤族“萬物有靈”宗教觀影響下的織錦圖案的紋樣和色彩進行解析,既加深了人們對佤族“萬物有靈”宗教觀的了解,同時也使人們更加具體地感知了佤族豐富的織錦紋樣和色彩運用,對現代設計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杜巍,白應華.文化宗教民俗[C]//首屆中國佤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DU Wei,BAI Yinghua.Religious folk culture[C]//The First China Wa Culture Symposium.Kunming:Yunnan University Press,2008.
[2]王莉,楊兆麟.滄源佤族服飾手工藝的傳承面臨挑戰[J].民族藝術研究,2008(5):60-63.WANG Li,YANG Zhaolin.Cangyuan Wa clothing crafts heritage faces a challenge[J].National Art Research,2008(5):60-63.
[3]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Marx,Engels,Lenin,et al.Marx and Engels Selections:4th Volume[M].Beijing:People's Press,1972.
[4]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M].上海:三聯出版社,1974.Plekhanov.Plekhanov Philosophical Works Selections[M].Sanghai:Sanlian Press,1974.
[5]洪潘,羅戒蕾,陳慧.基于數學圖形的染織圖案設計研究[J].現代紡織技術,2012,20(3):18-21.HONG Pan,LUO Ronglei,CHEN Hui.Studies on dyeing and weaving pattern design based on mathematical pattern[J].Advanced Technology,2012,20(3):18-21.
[6]畢登程,隋嘎.司崗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BI Denghua,SUI Ga.Secretary Kong Lane[M].Kunming: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
[7]馮天瑜,林干.滇云文化[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FENG Tianyu,LIN Gan.Yunnan Cloud Culture[M].Hohhot: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2003.
[8]彭曉,趙耀鑫.云南民族民間藝術[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PENG Xiao,ZHAO Yaoxin.The Folk Arts of Yunnan Ethnics[M].Kunming: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4.
[9]陳力.云南民族包[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CHEN Li.Yunnan Ethnic Bag[M].Kunming: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
[10]楊永慶,亓延.魯錦的文化性與應用創新研究[J].絲綢,2011,48(11):45-49.YANG Yongqing,QI Yan.The culture,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of Lu brocade[J].Journal of Silk,2011,48(11):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