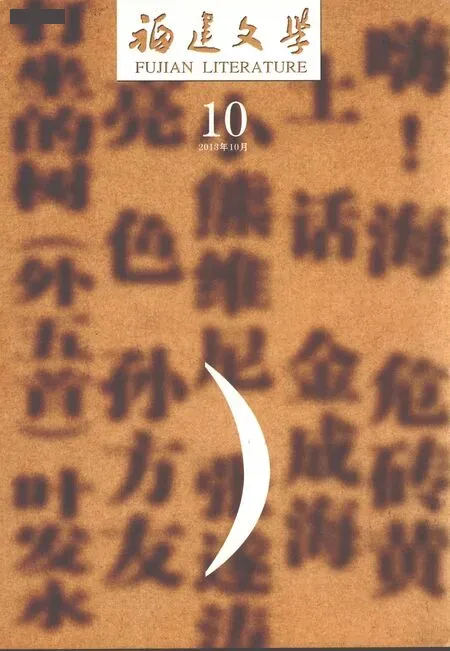水珠亮的影子
□ 方 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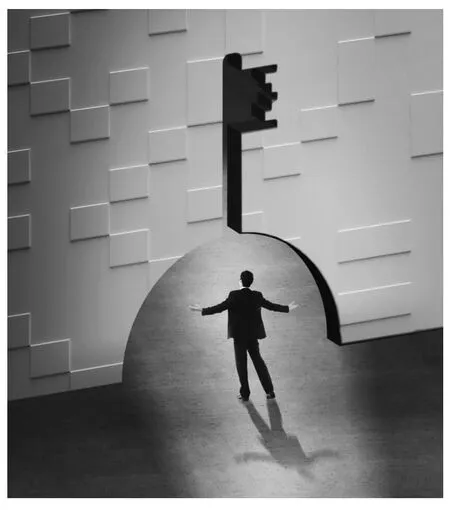
水珠亮拉提琴
水珠亮是大約兩周后才發現,自己丟了影子的。
按照周圍人對水珠亮的評價,水珠亮就屬于那種先天發育不齊全的品種。譬如,大家在所有的才能上都差不多,吃飯也好,說話也好,喝酒也好,演講也好,開車也好,拍馬屁也好,寫文章也好,穿衣服也好……總之,一般的人,往往都能找到均衡感,因為均衡而感到平衡,因為平衡而感到生活的和諧,感到舒適,從而覺得活得有聲有色,活得美、滋潤而快活。
但是,水珠亮是先天發育不良的。這種不良,就表現在找不到均衡感。譬如,在男女搭配這種自然規律上,水珠亮就表現得笨拙而不擅長。水珠亮簡直就忘了,他是怎么跟前妻離婚的。他們在婚姻登記所對面的離婚接待室門口分手,他只聽得妻子一聲感嘆:哎呀——,哪能想到呢!是啊,哪能想到呢,孩子才五歲,剛認識的時候,是妻子倒著追,百般溫柔賢淑,感動了水珠亮的父母,最后才成了親。哪能想到,過了沒幾年,妻子就鬧著散伙呢。妻子是跟人家黏搭上了,與其埋怨自己過于笨拙,不如責怨妻子過于水性楊花。是的,就那種黏勁,水珠亮這樣笨的男人都吃不消,何況稍稍正常的懂得風情一點的男人呢。
妻子走了,水珠亮一個人帶孩子出,一個人帶孩子進,就顯得失去均衡感了。這要換了一般的男人,比如生意失敗,窮困潦倒,或者五大三粗,動不動打老婆,賭個博,失個業,也就罷了,可是,攤到水珠亮頭上,就真是不均衡,不和諧了。
水珠亮是一個出奇俊俏的男人。個頭一米八,往哪兒一站都玉樹臨風,跟著名男模胡兵、影星邵兵有得一拼。這么一副現代版賈寶玉的模子,卻是沙僧的心性,這就太不均衡,太不和諧了。唉,可惜啊!任誰與水珠亮處久了,都會發出一聲跟前妻相同的感嘆:哎呀——,哪能想到呢!是啊,哪能想到呢!
而且,水珠亮其實并不笨,笨的人怎么能學成小提琴呢。水珠亮拉起小提琴來,琴聲那個悠揚,那個如泣如訴,如怨如慕,怎么能讓人相信他笨得像沙僧呢。每當傍晚,大家離開辦公室了,走得遲的人還在樓下的車位里倒車,水珠亮的琴聲就從窗戶里飄飄散散出來了。有時候是舒伯特的《小夜曲》,有時候是李斯特的《安慰》,有時候是德彪西的《幻想》,大家猜水珠亮練琴花了多少年,都猜不出。水珠亮從來都不言語。不像有些男人,會唱兩首歌也炫得不行,每次輪到卡拉O K,就跟麥霸一樣,不鬼哭狼嚎個夠就下不來。水珠亮只是坐在一邊,聽別人唱。唱完了,他也鼓掌。水珠亮上臺,整個觀眾席都會突然靜下來,這倒并非他演奏得好,眾人都像看到郎朗一樣,而是,水珠亮這么一副嚴肅孤清的樣子,就像在千年冰窟墳墓里陪伴小龍女多年的楊過,一出場,周圍的氣氛都跟著降溫。
一年到頭,水珠亮難得有笑臉,一點也不像劇團出來的。在劇團里,水珠亮就是拉琴的,大提琴。換到縣文化館,他就不拉大提琴,改為小提琴了。有一次,縣文廣局的領導問起他來,他說,大提琴那家伙太大了,辦公室找不到地方練,聲音太沉,會把人家嚇壞的。倒也是,這幾年機關里部門越設越多,漸漸地場地不夠用,十來個平方的辦公室,常常擠著三四個人。何況,水珠亮這么一高大的個子,往哪兒塞都顯得體積龐大。
水珠亮在劇團職稱已經評到高級,他也沒花多少力氣,仿佛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自從文化單位改制,事業轉企業,不到一年,劇團就難以生存下去,解散了。一天,水珠亮看到縣里的報紙上文化館在招人,就背著一把琴進來了。
進來才知道,其實文化館不需要拉琴的。看看周圍的同事,歌手余倩倩四十多歲了,原先是唱地方戲的,已經十多年不唱了,但她的真實身份是縣著名企業家、某政協委員的第三任太太;畫手施文昌的桌上也放著筆墨紙硯,但那完全是裝模作樣,只有縣里要搞書畫展了,施畫家才鋪開宣紙,三下五除二,也就刻把鐘,兩三枝墨梅就畫成了,自水珠亮來后,從來沒變換過題材,年年一幅墨梅,這也難怪,人家是縣領導的小舅子;作家侯啟文據說寫了民間故事三四本,小學畢業文化程度,完全自學成才。
水珠亮就跟這三個人處一個辦公室。剛進來的時候,因為缺少練琴房,水珠亮背一把大提琴就上露臺練,沒拉十分鐘,文化館領導朱館長就把他叫過去了:“小水啊,你真勤奮啊,那琴聲是很好聽,但是會影響到其他人休息,對不對?”水珠亮拼命說,他試過,露臺空曠,聲音一下就會飄散,影響不到辦公室里的人。領導的臉就稍稍暗了下來,說:“完全不影響是不可能的,多少總有聲音吧?”小水只好說:“好,我知道了,不練得了,但是吃手藝飯的,不練不行啊,俗話說,琴不離手。”領導這下真生氣了:“嗨,我跟你說,你還不信!你問問看,一年才輪到你拉幾場啊?”水珠亮瞪大眼睛,越發想不通了:“就是拉幾場也得練啊,平時不練熟,到時候怎么上場啊,要砸場子的啊?”
“好好好,你先出去。要練回家練去吧,反正不能在露臺上練了,啊,不是我不告訴你啊。”領導說完,看著水珠亮走出去,就嘖嘖地感嘆了一聲:“唉,這什么腦子啊……”領導說歸說,對水珠亮還是網開一面的,因為,第二天中午飯后,午休時間,底下人向領導報告,水珠亮又上露臺了。領導從窗戶里對著露臺望了一眼,搖了搖頭,嘴里嘀咕:“算了,隨他去吧!現在不是午休嗎,讓他練半個小時,你再去叫他吧!”
水珠亮背后生出了多個影子
一天早晨起床,太陽朗朗地照在馬路上,水珠亮走著走著,隨意地往身后一看,發現不知什么時候開始,自己背后生出了多個影子。
雖然水珠亮一年到頭,難得有笑容,但是,這一點也不影響水珠亮的形象。水珠亮的形象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時刻彌散出一種自然的光澤。進縣文化館后不久,私底下就傳播著關于他的一種流言,說,到底是劇團出來的,那舉止,那風度,那氣質,完全有明星相。他不笑,那是深沉,是酷。他蹙著眉頭,那是憂郁,是神韻。
進來兩周后,水珠亮終于搞清楚,他當時是如何通過文化館招考的了。兩周后的一天,傍晚時分,朱館長突然打電話跟他說,等會兒有個飯局,請他去作陪。“酒會喝嗎?你那么大的體量,不成問題吧?”水珠亮聽到“啵啵”的聲音,好像領導在拍自己的肚子。“會一點,不過不多。”水珠亮老老實實地回答。“會喝就成。”領導爽朗地表示。
水珠亮的酒量是有限的,因為喝酒的機會并不多,從小在家里也沒養成習慣。水珠亮的父親是中學音樂老師,母親是小學音樂老師,一個彈風琴和鋼琴,一個拉手風琴和彈電子琴,他們兩個人的遺憾都是沒學提琴,于是水珠亮從小被安排學小提琴,但是到了小學六年級,水珠亮身材開始躥個,眼看著他的長勢,父母就轉變心意,讓他學大提琴了。身材太高大,拿著小提琴顯得不怎么均衡,就好像拿一個玩具一樣,看上去太不和諧了。所以,水珠亮的家庭教育是遠離酒精的。進了劇團,也只管練琴評職稱,并不懂什么應酬往來。
跟著朱館長落座,才發現,自己被安排坐在靠近門口的座位,右邊就是朱館長。與館長相對的是一個什么博物館館長來著,再上去相對的是兩個副局長,再上去是局長,中間靠窗的上方席位還空著。
大家落座,局長開始打電話,顏笑逐開,歡天喜地的樣子,聲音高八度:“哦——,到了,到了,終于到了,不急,不急,慢慢來,我到門口去接您!”說著就跑出去了。兩個副局長也立即站起來迎出去。兩個館長也站了起來,端出滿臉的盈盈笑意。水珠亮就跟著站起來了,這是誰要來了呢,這么大的架勢,水珠亮一臉惶惑。
“啊,不要客氣,大家坐,坐!”領導進來了,笑容可掬,一進門就打了個手勢,一臉豪氣地說。
等坐下,水珠亮一看,才明白館長叫他來的原因。博物館館長、副局長、局長、領導都是女的。聽稱謂,水珠亮算搞明白了,是分管文教的副縣長。水珠亮不由倒抽一口涼氣,這年月,女人能頂大半邊天啊!
盡管水珠亮學不出人家的樣子,端出個笑容。但他一臉恭敬的樣子,還是得到了女領導們的欣賞。“你呀,還不快感謝毛縣長!當初,就是毛縣長的朱筆欽點了你的大名,你才能招進來呢!”局長乜斜著眼,朝他說笑道。
毛縣長微笑著,并不說話,拿眼睛輕輕地掃了他一眼,便垂下眼瞼,眼神落在眼前的一盤三文魚上。“吃,小水,多吃點,三文魚營養好!”
一個副局長馬上把轉盤轉動起來,將三文魚轉到他前面停下。水珠亮就夾了一片蘸了芥末吃。沖味太重,嗆得水珠亮差點就兩眼汪汪了。這狼狽相,招引得局長首先就忍不住,撲哧一聲笑出來了,于是一桌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毛縣長將愉快抑制在肚子里,但皮膚滲透著滿懷的喜悅。
氣氛突然變得輕松愉快起來,話題就圍著水珠亮轉。從水珠亮的爸媽,到水珠亮的學琴,到水珠亮目前的單身狀態,到水珠亮五歲的孩子所讀的幼兒園。不過半小時,水珠亮發現,就像查家譜一樣,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在飯桌上,仿佛眼前杯盤里裝的菜肴就是他水珠亮家世的林林總總做成的。水珠亮后背都冒冷汗了,這是什么時候,通過哪些途徑調查的,怎么自己還糊里糊涂的,卻被人家了解了個底朝天啊,水珠亮不知道這一切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小水,你知道毛縣長為什么朱筆欽點了你嗎?我說小水啊,你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局長依然乜斜著眼,故意沉著臉問。
“是啊,這是什么原因呢?先讓我來猜猜。”朱館長突然用孩子猜字謎似的口吻說。
“那還用猜,還不是我們小水琴拉得好,是藝術家。”一個副局長馬上應和。
“人家是貨真價實的藝術家呢,評了高級職稱的!”另一個副局長用夸張的語氣立即作了補充。
“是嗎?文化館引進人才工作做得好!我們博物館也要向你們學習!”那個館長這時候也一本正經地恭維。
“因為……”副縣長這時候直了直脖子,看看左右認真猴急著等待公布答案的表情,才鄭重其事地說:“大家說對了,小水真的是貨真價實的藝術家,我在劇院曾經看過他的演出,他當時拉琴的神態如醉如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對藝術家要由衷地尊敬!現在我們創文化大省,創文化強縣,靠的不光是我們這些干部,還需要大量有才華的文化人,有才華的藝術家!來,我們敬藝術家一杯!”
局勢變化太快,眾多的酒杯突然湊到水珠亮面前,眾星拱月一般,水珠亮有些惶然,輕輕碰了一轉,在館長的敦促下,破天荒喝了滿滿一杯。
看著水珠亮滿杯落肚,局長貌似跟朱館長說:“嗯,酒風好,有培養前途!我看這個藝術家不僅琴拉得好,搞行政也一定是好手!朱館長,年輕人要注意培養,這個光榮任務就交給你了!”
水珠亮的影子是彎的
水珠亮自從發現身后有幾個影子之后,養成了老回頭的習慣。他仔細看這些影子,一度覺得奇怪,明明自己的身材玉樹臨風、高大挺拔,怎么影子總是歪歪扭扭,直不起腰來的樣子呢,水珠亮琢磨了多少天,都始終不清楚這到底是為什么,后來也就懶得去想它了。
飯局過后,每個星期水珠亮都得上門為領導服務,毛縣長和局長家都是獨生子女,都是十來歲的女孩子,一個叫格格,一個叫露露,不管是格格還是露露,水珠亮都得把她們倆教好,伺候好。教什么?小提琴。
這下水珠亮有得忙碌了,他的英雄才略有了用武之地。但是,水珠亮喜歡的是在公眾面前拉一首如癡如醉的長曲,而不是在兩個女孩面前從“哆唻咪發”開始,這些最基礎的繁瑣的音部教學,簡直能讓水珠亮發瘋。
兩個女孩,格格文靜清秀,不但模樣長得好,而且,蕙質蘭心,學得很快。而露露無論怎樣耐心地點撥,哪怕手把手地教,她也一副無動于衷的樣子,聽說在班上成績也糟糕。一天,兩個人一起練習《開塞》第一首練習曲,訓練手指的靈活性,學習左手指的音準和不同的換把位技巧,格格的手指纖細修長,壓在琴弦上就是好看,對音準的把握也相當到位,水珠亮很滿意;而露露的手指粗大,人也長得肥肥胖胖的,怎么看都不是一個學音樂的材料。但是,水珠亮有什么法子呢,難道跑到局長大人面前說,不行,你的女兒就是不行,這個徒弟我不想收。水珠亮思前想后,覺得自己的嘴實在說不出什么動聽的話來,要推辭掉這門差使,肯定是不行的。自從水珠亮接了這兩項活以后,看朱館長對自己的態度,那簡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以前,他練琴要獨自上天臺,還被叫下來。而現在,只要往稍稍空曠的地方一站,他端起琴就可以完全陶醉地拉下去,路過的人都伸出大拇指。水珠亮一度想不明白,為什么這前后,人們的態度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但是,水珠亮就是再笨,到后來,他也終于還是琢磨明白了,他眼下的飯之所以吃得還順當,靠的可不就是這兩個小姑娘?
跟格格在一起,露露顯得自卑。她吃力地用闊大而肥的巴掌肉夾著腮托,左手彎彎地伸出去,按在弦上。由于手臂短,扛得很吃力的樣子。水珠亮看著,心里想,這真是活受罪啊,練的人受罪,教的人也受罪。看看露露的神色表情就知道,她一臉羞赧地漲紅著巴掌肉,看格格拉的時候,就吧嗒吧嗒地睜大著兩眼,一副虛偽地艷羨的樣子,嘴里不住地說,格格姐姐,我什么時候才能像你一樣呢?這樣的話說多了,連她自己也感到碎煩。因為開始念叨的時候,格格還好,還敷衍應承兩句,“大家基礎都差不多啦,你努力努力一定超過我啦”,后來,這樣的話都懶得回了,即便是一個“嗯”也懶得搭理了。露露就自己說,自己笑,完全是一副受鄙棄的模樣。因此,學了兩個月,露露自己就打退堂鼓了。
局長一心想要用好這塊資源,自己的女兒卻不想學下去了,局長心里就有點不舒服。
“這是怎么了,人家格格也不想學了嗎?”
“怎么會,格格學得可好呢!”
“那你怎么不想學了呢?”
“不想學,就不想學了唄!”
“是老師教得不好嗎?”
“我覺得他不是太適合我吧!”
“什么叫不是太適合你啊?”
“是我不太適合他吧!”
“少跟我煩這些適合不適合的,那格格適合嗎?”
“格格當然是適合啦,他們是彼此都適合,一個教得樂,一個學得勤。”
“我聽明白了,也就是他教你就沒這份熱心,是吧?”
“這個自然啦,人家看格格和看我的表情都不一樣,那當然,我哪能跟格格比?”
“哎喲,還真看不出來,這水珠亮人模人樣的,原來是這樣一個馬屁精。我的官比格格她媽小,他對你就這樣的態度。”
“那倒也不是,是我自己不行吧。”
“看你出息的,年輕孩子哪有自己承認不如人的。我看你在他那兒真的不能再學下去了,以前你可沒有這股自卑勁!”局長不知道是由于工作任務過于繁重,還是女兒的事情真的讓她生氣了,她突然不知哪里窩著一股火,嗶嗶啵啵聽著就像要燒起來了。
她抓起電話,就撥給了下面的朱館長:“我說老朱啊,我女兒最近身體不是很好,那個學琴就停掉了吧!您跟小水說一聲哈!”
朱館長一聽口氣,就知道局長窩著火來了。這要換了別人,天底下都撈不著的馬屁機會,還不跟踩樓梯似的蹭蹭地往上走。也只有水珠亮這樣頭腦少了點什么的人,把好端端一樁事搞砸了。身體不好,一般是一兩次不去什么的,哪有停掉的,可見就是沒教好,沒把局長千金給伺候好。人家成績再差,腦子再不好使,還得看出身啊,人家畢竟是局長的閨女嗎,這一片土地有幾個局長來著,能當一般的學生教嗎?看看,這是什么腦子。估計再過不了幾個月,另一個也教不下去了,那時候,他可要看看你水珠亮還能在走廊上把琴拉得這么響嗎?眼里完全沒有這個館長似的。
事情沒有朱館長想得這么不順利。人家格格畢竟不一樣,在學校里成績響當當之外,拉起琴來,那模樣,那姿態,也有了水珠亮的風采。不僅左手指的指位非常到位,而且,右手的彈簧弓位也漸漸自如起來。
學了四個月,正好趕上學校的元旦慶典,格格就上臺亮了相,拉了一首《瓦爾法特》。毛縣長也坐在臺下,看得心里喜歡,兩眼都流了淚。瞧,官做得再大,也是母親不是?水珠亮就挨在毛縣長身邊,再過去一點才是湊熱鬧來的朱館長。水珠亮一把年紀了,自己也沒買個車,朱館長為了表達殷勤,特意將水珠亮送到了學校演出會場。毛縣長顯然也心領神會,感激之情因為女兒的演奏溢于言表,特別是對水珠亮,又是拉胳膊,又是拍后背的,這些微小的動作都沒逃過朱館長的眼睛。他心想,啊呀,可別小看了水珠亮,副縣長和局長比,當然是伺候大的了,大的伺候好了,啥事都解決了呀。這水珠亮,在教學上,肯定是偏心了的,要不,格格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登臺演奏,而露露卻要退學不上了,這一定是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這教學可不是游擊戰,而是需要長期作戰的。那么,水珠亮顯然已經抱上一棵大樹了。再怎么著,即使將來格格不學了,他水珠亮也是副縣長大人孩子的老師,就這身份,也夠他朱館長抬捧的。
可是,局長的臉色就不一樣了。雖然臉上也還是微笑著的,但是,說話的語氣究竟是涼颼颼的了。但是,他水珠亮現在成了副縣長的人,她一個局長能怎樣呢,還不是照樣得把馬屁拍好。朱館長知道其中的利害,在副縣長面前,把水珠亮吹成一朵花似的,在局長面前,又偷偷把他說成一泡屎。這些,水珠亮都漸漸覺出來了,覺出來了,能怎樣呢,啥也不能,也不關他的事,他只消拉好琴,教好琴就是了。
水珠亮的影子丟了
這樣紅紅火火的日子過著,水珠亮也沒想到為自己謀一點利益,譬如撈個職位什么的。這人的木和呆就是這樣,看上去好好的一大個子,有模有樣的,一到臨事,就分出個子丑寅卯來了。大約兩周后,水珠亮猛一回頭才發現,路上沒影子了,原來自己后面有多個影子,后來只有一個影子,現在唯一的一個影子也弄丟了。
職場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沒個準信,不久,副縣長的任命書到期,這些頭頭腦腦又該輪著換地盤了。格格也要準備中考,沒有時間精力再來學琴了。水珠亮重新回到了以前剛進門的狀態,而且,因為局長的關系,這日子突然就過成夕陽西下了。
先是練琴的時候,同事們過來過往不再有熱情的招呼了。水珠亮有時覺得不好意思,人家沒開口,就打算還禮來著,停下弓腰,點個頭什么的來著,可是,就有那么幾個人突然身板都直了幾分似的就走過去了,頭也沒朝這邊轉轉。也有的轉過頭來,打著哈哈地說:“還拉啊——!”那樣子,仿佛是說,你這手藝該停一停了,是啊,你拉和不拉有什么區別呢,現在滿院上下都知道你能拉琴了,可是,拉個琴究竟算個什么呢?關鍵是有沒人稀罕你會拉。現在稀罕你拉琴的人走了,或者你沒本事伺候好,那你再是狂拉還有什么用。凡是萬物,都講究個用字,跟老莊說的那樣,一棵樹長成參天大樹,不能拿來派用場,又有什么用,但想久了,水珠亮也知道用“無用之用”來安慰自己。是啊,無用,也是一種用啊!
原先,副縣長在的日子里,自己是那樣忙,除了要勻出時間教格格拉琴,還有各種各樣縣里組織的晚會、演出,都有邀請他的帖子送來。而今,卻是門前冷落鞍馬稀,換了光景了。光會拉琴有什么用呢,綜合能力不高,也只有拉拉琴吧,可是,你要拉,回家去拉呀,何必在單位里拉呢,在單位里拉給誰聽呢,誰不知道誰幾斤幾兩啊?這不是顯擺錯了地方嗎?
時間長了,朱館長就把水珠亮叫到了辦公室,說是找他談心。“水珠亮啊……”,館長一開口的語氣就是這樣語重心長,“你到館里來的時間也夠長了,可是,做人做事方面,我覺得還是很有欠缺啊!你那個琴,就不能不拉嗎?你大白天在那邊拉,雖然是休息時間,可是影響大家休息啊!這個我已經跟你反復強調多少遍了,你還在堅持,你這是跟大家唱反調,這樣的工作氛圍不和諧呀,是不是?那,交給你一個正經任務,明天有個會議,有許多人要來參觀,你去把瓶裝礦泉水抬上來,在樓下碼著呢!還有,會議要用的文件、編印的冊子、光盤都要在信封里裝好,礦泉水最好分發在位置上,接著把信封裝好。”
原來第二天是有個文化論壇什么的。現在全國都在講要建文化強國了,省里就提出文化強省,到了區縣,就成了文化強縣。怎樣體現文化呢,人人都在說文化,都在提文化,都在探討文化,這論壇就是為了探討如何建設文化強縣來著,當然其本身也是一種尚佳的文化形式的體現。這么多人到縣里來探討文化、交流文化、繁榮文化,就得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是相當瑣碎而紛繁蕪雜的。譬如,需要人人一瓶礦泉水擺上桌面,這些礦泉水就得有人去訂,去搬運,去分發呀。人家來了,總要有東西讓人家看看吧,印些小冊子、光盤之類的就免不了。除了這些,還得讓人家乘興而來,滿意而歸,總得送點精致的小禮品什么的吧。那就得裝好禮品盒。客人來了,總要表示歡迎,橫幅什么,以及再高級一點的電子屏什么的,就更是少不了。而這些林林總總的瑣碎的事情都得有人去做,去完成。水珠亮現在是藝術家嗎?他在臺上就是一藝術家,在臺下,就該少擺藝術家的譜不是?誰說藝術家只能搞藝術創作、表演的,藝術家難道不要吃喝拉撒?既然藝術家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的,就得會做吃喝拉撒的事。
舉行論壇的會場在六樓,礦泉水一箱箱的碼得整整齊齊,在底樓。水珠亮得先把一箱箱水推進電梯,到了六樓,又得把它們一箱箱拉出來,抱到會場門口。水珠亮再是玉樹臨風,干起這些事情來,怕也只能是昨夜西風凋碧樹了。這些粗重活,水珠亮一生從未干過,朱館長有話在先,就水珠亮這么大號的個子,不讓他去搬誰去搬。水珠亮脫了平素的一身行頭,黃色風衣,褐色的圍巾什么的,只留了薄薄的一件棉織單衫就下去了。礦泉水25瓶一組來著,是整體用尼龍塑料外殼包裝的,雖然少了紙箱的重量,但拎起來著實不方便了,搞不好,就把塑料膜外殼撕裂了,所以,只能蹲下腰,一包包地把它抱在懷里,送到電梯,先壓在電梯門口子上,使電梯不至于自動閉攏,然后,才能回轉身去抱第二包。水箱堆離電梯門大致有五米的距離,水珠亮想,沒事,不就是十來包東西嗎,沒干過的事情也是要慢慢學起來的。水珠亮就一次又一次地蹲下,把水一次次地抱在懷里,再一次次地放下,這一趟活干下來,水珠亮背上都濕了,汗水貼著內衣,棉織單衫懷前已經起了一個個小絨球,熱,水珠亮后來把單衫也脫了,只剩下內衣。等這些活終于干完,他穿過走廊,去上廁所時,清了清喉嚨,朗聲唱起了《長江號子》:“喲—嗬—嗬……喲—嗬—嗬……,一聲號子我一身汗,一聲號子我一身膽……”
上廁所的時候,水珠亮看到自己的尿撒出去,比平素都長都遠。是的,許久未勞動了,這一番折騰,使自己精力充沛呢!是好事。水珠亮安慰自己。接著又去裝禮品。裝禮品的人可多了,不止他水珠亮一個。每個禮品盒裝好,還要分發到座位上。剛才水珠亮抱來的礦泉水,也需要一瓶瓶放到會場桌上去。水珠亮就先發礦泉水。這礦泉水雖然只是一瓶水,發起來也是有講究的,譬如,都放在左上角,地方是不能亂動的,放倒了,放歪了,都不行,不美觀,不漂亮,不精神。會場是講究精神的地方,細節決定成敗。所以,不光是礦泉水要放好,其他禮品盒也是要放好的。禮品盒就放在會場的每一張椅子上,但是既然要講究整體效果,禮品盒就不能有的正面朝外,有的反面朝外,要將能顯示文化強縣的那一面朝外,每一個禮品盒除了要清點里面物品的數量,都要一個個放正來,不能東倒西歪。水珠亮于是就一張桌子一張桌子地放礦泉水,完了,再一張椅子一張椅子地放禮品盒。
影子丟了就丟了唄
這樣的瑣碎的雜務漸漸充斥了水珠亮的生活,水珠亮多少有些變化了,原先那種逼人的帥氣,說到底就是云遮霧罩的藝術氣質漸漸淡去了,一種說不清楚的紛亂的味道混繞在水珠亮身上,那是一種他自己也說不清楚,說不明白,不夠情愿,但只能任其發展下去的氣味。水珠亮對此深有察覺但毫無辦法。水珠亮現在走在馬路上也從不回頭了,他想,影子丟了就丟了吧,去找回來,那是要花力氣、動腦筋的,他也這個年紀了,再混上一兩年,也人到中年了,還有什么指望。
現在,水珠亮也基本不再照鏡子了,很少再在圍脖上套上他的褐色圍巾了。不再有什么晚會和表演來邀請他,那些花花綠綠的邀請帖遠離他的生活了,他就像是過早地過氣了,背時了,被遺落在某個角落了。而他每天所能面對的只能是這樣的生活。
有時候,半夜里醒來,水珠亮也想想,明天是不是給毛縣長打個電話,或者到她那里去訴說訴說自己的處境,看看有沒解決的辦法。但是,毛縣長畢竟是個縣長呀,格格也不再學琴了呀,像這樣的縣長千金,多少人等著排隊上門教呢。這人情跟距離是成反比的,遠了就涼,人走茶涼。水珠亮想,不去麻煩人家指不定還給人家留個好印象,搬出以前的交情再去麻煩人家,那就像是吃隔夜菜喝隔夜茶,味道總是兩樣的了。而且,說起來,自己不是還在單位里呆著嗎?還不是照樣拿著工資嗎?人家怎么你了?不就是演出少了,多出了一些碎活嗎?哪個單位沒碎活啊,哪個演員能保證做常青藤啊?人總有背時背運的時候,為了這些小事去麻煩人家,就顯得拎不清了。
其實,要把影子找回來,水珠亮也想過,不是沒辦法。露露不是還閑著嗎?把好意傳達到,多上幾次門,工作做到家,人心總是肉長的。可水珠亮就是水珠亮啊,這孩子不是學琴的料,能當牛一樣教嗎?人家學著累,自己教著也累啊,還有,究竟是丟不起這個份,涎不起這個臉啊!那么,就這樣下去吧,做做雜務,練練身體,也很好。人總得自我安慰吧,不然,怎么活下去呢。
水珠亮現在也不再想練琴了,一是因為不能再練,朱館長已經嚴肅地找過他幾次了,而且,來來往往的同事都拿他做透明的玻璃人了,這琴拉給誰聽呢。有時候,水珠亮下班路上遇到高架橋下自己擺個音箱就在那里吼的年輕人,水珠亮真羨慕他們那種年輕的干勁,那種生猛的不按照章法出牌的大膽。水珠亮想,自己他媽的都混到啥份上了呢,都不如瞎子阿炳呢,阿炳抱了個破琴,還能以琴謀生,還能有來來往往的路人做觀眾,自己到哪里拉去呢。水珠亮也不是沒想過,要不要開辟第二職業,晚上去咖啡吧或者高級會所拉拉琴,兼賺些外快收入,但是,這消息必然會傳到館長耳朵里,文化干部到消費場所賺外快,像什么話,這頂帽子到時候吃不了還得兜著走呢。
辭職不干,水珠亮也想過,可是,自己這不是費了九牛二虎才考進的事業單位嗎?這人啊,有幾個十年呢,這不,再混個十來年,就日暮西山了嗎?捧著體制內的金飯碗不要,再到外面瞎闖蕩,畢竟不是年輕時候了。這不上不下的,這不正是尷尬的年紀嗎?上有老下有小的,總要有交代吧。
琴不練了,最主要的是練習了也沒有用武之地了,琴藝就荒疏了許多,就像缺人照料的菜地,漸漸地雜草叢生了。回頭想起來,有時候水珠亮也有些不甘心,眼見著女兒漸漸長大了,他想,對呀,把女兒教會,不就有共同語言了么。所以,手癢的時候,他就回家撥弄撥弄,他現在啊,每天只盼著下班了。
水珠亮現在走路頭也不回了,他不關心影子的存不存在,他知道也許這樣反而更好,雖然他連穿著也不再講究了,鏡子都不再照了,但是,他套著一件長久未洗的羊毛衫,一副落魄潦倒的樣子,也能感覺出腰桿的硬朗。他想,沒有影子的生活也是很好的。
有一天,水珠亮被身后小汽車的喇叭聲嚇了一跳,他一回頭,眼光不經意地落地上,一看,瞧,什么時候,自己又有影子了,那影子長長瘦瘦的,不修邊幅,有些毛糙。那可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嗎?他想,唉,這影子跟人的脾性還是相通的。人起了變化,影子肯定也會起變化,他知道自己的影子一定不夠好看,管它呢,反正都這個年紀了,這人生,到哪兒不是混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