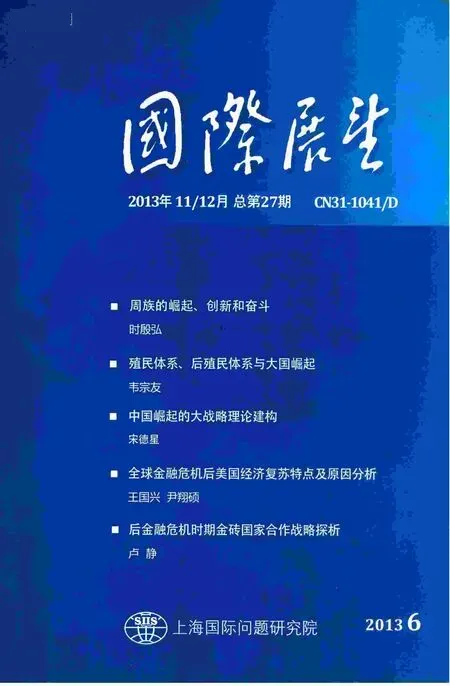殖民體系、后殖民體系與大國崛起
韋宗友
大國崛起是國際政治中的核心議題之一。一直以來,主流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大國崛起多持悲觀看法,認為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下簡稱“和約”)創立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以來,大國崛起往往伴隨著沖突乃至霸權戰爭,和平的權力轉移寥若晨星。1648年以來的國際關系史似乎也佐證了這一看法,英國、法國(路易十四和拿破侖)、德國(威廉一世和希特勒)以及日本等一個個大國的崛起無不伴隨著“血雨腥風”。西方學者據此認為,在主權國家體系下(即西方學者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由于缺乏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權威來提供秩序與安全,國家間關系是恒久不變的“零和性質”,一國的權力和財富增長必然會引發崛起大國與既有大國之間的緊張關系,最終沖突與戰爭便不可避免。①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9, pp.102-128.基于這一理論邏輯,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崛起前景極為擔憂,認為中國崛起很可能會引發中國與西方大國及既有秩序之間的矛盾乃至沖突,“大國政治悲劇”難以避免。②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2001, Chapter 10.
本文認為,將大國崛起時的戰爭與沖突歸因于主權國家體系或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并進而以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預測大國崛起的“悲劇”,顯然具有誤導性,這過于“簡約”。主權國家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大國崛起的“悲劇”是否存在必然聯系,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演繹或理論抽象,而是一個實證問題。具體地說,主權國家體系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含有豐富歷史內容及邊界的規范結構,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規范結構下,大國崛起的路徑將截然不同,戰爭與沖突并非大國崛起的宿命。
一、主權國家體系、殖民體系與后殖民體系
1648年和約被廣泛認為開啟了現代國際關系,也是主權國家體系誕生的標志。波切爾(David Boucher)提出,和約“正式承認了歐洲現代國家體系并為其奠定了基礎”,“確認了諸多國家行為體的正式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同時將均勢原則確認為阻止霸權的機制”。霍爾斯蒂(Kal Holsti)也指出,“和約使得主權觀念合法化,王朝不再受到等級控制而獲得自主。它創造了一個可以讓歐洲政治維持碎片化的架構。”摩根索宣稱,和約“……使得主權國家成為現代國家體系的基石”,“國際法規則得以牢固確立”。斯普魯特(Hendrik Spruyt)宣稱,和約“正式承認了主權國家體系”。扎切爾(Mark Zacher)則認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承認了國家在其疆界內的最高權威或主權,終結了教會的跨國政治權威。”①All cited from 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2, Spring 2001, pp. 260-261.
近年來,上述觀點正日益受到質疑。有學者指出,和約并沒有確立國家主權原則,也沒有由此創立一個基于主權國家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②Randall Lesaffer, “Peace Treaties from Lodi to Westphalia,” in Randall Lesaffer ed., Peace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pp. 9-10; Derek Croxton, “The Peace of Westphalia of 1648 and the Origins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1, 1999, pp. 569-591.奧珊德(Andreas Osiander)通過對三十年戰爭及和約內容的詳細分析,認為和約并沒有確認任何國家的主權,更沒有確立主權原則。針對被學者們視為國家主權原則獲得明確確認的荷蘭及瑞士獨立,奧珊德指出,荷蘭的獨立是在1648年1月荷蘭與西班牙國王簽署的《明斯特和約》中確定的,但該和約不是1648年10月簽署的和約的一部分。換言之,荷蘭的獨立在和約簽署前已經獲得確認。至于瑞士,早在和約簽署前,瑞士也已經事實上獲得了相對于神圣羅馬帝國的完全獨立,若不是瑞士一個稍晚加入的州希望在和會上進一步確認其獨立,瑞士甚至根本不想與和會發生任何關系。奧珊德還特別分析了神圣羅馬帝國內各邦、自由城市的獨立問題,指出盡管和約規定了諸侯邦、自由城市的實際領土管轄權以及對外結盟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獲得了主權地位,因為根據和約,這一結盟權不能用來損害皇帝或帝國及其公共安全,而且1648年后歐洲其他行為體也并沒有承認他們的主權地位。③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 Myth,” pp. 262-273.
奧珊德的批評細致入微,但過于苛刻。盡管從技術角度看,荷蘭、瑞士的獨立與和約的關系或許還可斟酌,但不可忽視的一個總體圖景是,經過三十年戰爭及和約,中世紀以來的羅馬教皇神權統治體制的世界主權論被正式拋棄,承認了新教與天主教享有同等權利,也為世俗國家的君主或國王行使境內的最高統治權(主權的一個重要標志)掃除了法律障礙。而且,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力被進一步削弱,加劇了帝國境內的諸侯“割據”局面。此后,越來越多的中央集權式的民族國家,如荷蘭、瑞士、法國、瑞典、英國、西班牙等,成為歐洲國際關系中的獨立乃至主要行為體,對內行使最高統治權,對外享有結盟、宣戰、締約等獨立權與平等權。從這個意義上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實際上開啟了歐洲主權國家體系的新時代。
不過,這一“主權國家體系”與其當代含義有很大不同。自16世紀以來,經過博丹、格老秀斯、霍布斯等人的闡釋,主權概念已經具有“對內最高統治權”和“對外獨立權及平等權”兩大基本含義。但由于直至一戰以前,戰爭一直都被視為執行一國對外政策的合法政策工具,以武力獲取領土以及征服非但未被視為非法,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被視為一國擁有主權的顯著標志。因而,在對外關系方面,這一主權觀念更多是強調一國不受外來約束,必要時以武力開疆拓土的能力,而不是基于主權平等原則對他國主權的尊重。
從地理空間角度看,此時的主權國家概念僅限于歐洲一些大國,即便是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境內的諸侯邦也不能被視為具有完全主權的國家。至于歐洲之外的廣大地區,則完全被排除在主權資格之外,它們反而是歐洲大國行使主權的對象及檢驗主權能力的場所。①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國家先后以宗教及文明標準,將歐洲以外的世界視為可以合法占領(occupation)及征服(conquest)的囊中之物。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開啟前的一個多世紀,即所謂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開歐洲近代海外殖民風氣之先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曾在羅馬教皇的鼓勵下,對新世界的“異教徒”進行征服,對其領土進行瓜分。1452年,羅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權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令其享有進攻、征服、臣服撒拉孫人、異教徒以及所有基督敵人的權利。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向西班牙國王及王后頒發詔書,正式確立基督教對新世界的統治權,要求征服土著居民及其領土,并將所有新發現或尚待發現的土地的征服和統治權分別授予西班牙和葡萄牙。1495年,英國國王亨利七世也授權約翰·考伯特及其三個兒子探尋并發現世界上任何被異教徒占有的島嶼、國家或區域,令其加以征服、占領并納入國王統治之下。①M. F. Lindley, The Acquisition and Government of Backwar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Being A Treatise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Colonial Expansion, London: Longmans,Green and Co. Ltd., 1926, pp. 24-26.他們將這些占領或征服的目標大致分為兩類:無主地和可征服的領地。所謂無主地,主要是指美洲大陸、澳大利亞以及一些土著人居住的島嶼。歐洲法學家及神學家認為,由于這些土著居民沒有在其居住地區建立起有效的政治組織,也沒有對其土地進行有效的利用,因而不能認為這些土著對居住地區擁有主權,這些地區屬于“無主地”,歐洲人可以合法占領。再后來,特別是歐洲進入了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體系后,它們進一步將目光投向非洲、亞洲等已經擁有政治或政府組織形式、達到較高“文明階段”的廣大地區。在歐洲列強眼中,雖然這些地區不屬于“無主地”,但由于它們依然沒有達到歐洲的文明標準,不是“國際社會的大家庭”成員,因而其土地可以被視為征服和割讓對象。②Ibid., pp. 24-31.正是以宗教和文明標準為借口,歐洲國家不僅“發現”和“占領”了美洲新大陸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廣大地區,而且在非洲、亞洲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殖民狂潮,建立起龐大的殖民體系。
顯然,這一時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體系),并不是當代理解的主權國家平等、獨立的國際體系;相反,它是一個歐洲國家向外部擴張、占領、征服的不平等體系。它是歐洲國家消滅土著民族、占有其土地,征服“落后民族”、割讓、吞并其領土的殖民體系,也是一種基于種族優越論、以武力奪取“落后民族”領土的歐洲列強主權體系。換言之,它是一個奉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不平等的殖民體系。
從時間上看,這一殖民體系始于地理大發現,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開始走向沒落,而其消亡則遲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亞非獨立浪潮。該體系的最大特征并不是國際關系學者宣稱的“主權獨立”,而是其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它只承認歐洲國家(特別是歐洲大國)的領土主權,其余國家和地區則是殖民和征服的對象。它不僅不反對以武力奪取他國領土,相反還將這一能力視為國家擁有主權的重要指標。它隱含了這一推論:一個歐洲國家如果不能在歐洲之外以武力“開疆拓土”,那么其主權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隨著殖民體系在二戰后的最終瓦解,國際體系進入了后殖民體系時代。
在后殖民體系時代,主權原則真正覆蓋全球,國際體系不再是一些國家擁有主權,另一些國家被剝奪主權的不平等體系。《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明確規定,各成員國主權平等是聯合國賴以成立的基本原則。其次,以武力奪取他國領土被明確禁止,行使主權不再意味著對“落后地區”或“弱小民族”的征服,而是對任何此種企圖的“自衛”或在聯合國授權下的集體防衛。《聯合國憲章》第二條規定: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第五十一條規定,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到武力攻擊時,在安理會采取必要行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①聯合國官方中文網站:《聯合國憲章》,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相對而言,這一體系至少在形式上確立了主權平等和獨立,也明確廢除了殖民掠奪和戰爭、并對武力使用施加了嚴格限制。
綜上所述,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所描繪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或主權國家體系,實際上涵蓋了兩個前后相繼的次級體系:殖民體系和后殖民體系,盡管前者在時間起點上早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前者從地理大發現直至二戰結束后,后者則自殖民體系瓦解后直至當今。前者的最大特征是不平等性和暴力性;后者則是主權獨立與平等原則真正涵蓋全球的體系。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將這兩個階段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或主權國家體系統稱,實際上掩蓋、模糊了其中存在的重大差異。
二、殖民體系與大國崛起
殖民體系是一個不平等、充滿暴力的等級體系,也是將殖民掠奪與征服視為大國行使主權題中應有之義的弱肉強食體系。居于金字塔之上的是擁有巨大暴力能力和殖民能力的歐洲列強,居于金字塔中間的則是較弱一等的歐洲國家以及擁有主權或半主權的亞洲和非洲國家,居于金字塔底層的則是完全喪失主權的亞非拉被征服、掠奪和占領的“落后民族”和“野蠻地區”。
這一體系下,大國的崛起與殖民掠奪密不可分,殖民掠奪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它往往以兩種方式進行:一是歐洲列強對非歐洲地區的殖民征服和掠奪;二是歐洲列強之間因殖民矛盾而發生的殖民爭奪或爭霸戰爭。
歷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歐洲列強的崛起之路無不伴隨著海外殖民與擴張,伴隨著對美洲、非洲和亞洲人民敲骨吸髓般的掠奪與剝削。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新大陸的發現者和近代殖民主義的開拓者。如同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的,美洲對歐洲和資本主義的崛起具有重要意義。自1492年第一次與美洲進行接觸之后,“立刻開始了一個爆炸式的、大規模的對美洲國家和文明的毀壞,對貴金屬的掠奪,對當地勞動力的剝削,以及歐洲人對美洲土地的占有。”①J. M. 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譚榮根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頁。它們通過武力摧毀了印第安文明,殺戮了印第安人口,占領了它們的土地。與此同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還從美洲攫取了巨額的黃金、白銀。據不完全統計,1561—1580年間,全世界生產的白銀有約85%來自美洲。從地理大發現到1640年間,至少有180噸黃金和 17000噸白銀被運往歐洲,而真實的數據可能至少是這一數量的一倍。此外,歐洲人從美洲的奴隸種植園及非洲奴隸貿易中也聚斂了巨額財富。②同上,第239—249頁。除了搶占了美洲新大陸,它們還將觸角延伸到亞洲沿海地區,建立起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龐大殖民帝國。后起者荷蘭、法國和英國如法炮制,也在美洲、亞洲和非洲建立起殖民帝國。特別是英國,通過十七至十九世紀一系列的殖民征服和殖民戰爭,建立起一個覆蓋全球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占領了地球陸地面積的 1/3,統治了全球人口的近 1/3。廣大的海外殖民地,不僅為歐洲列強的崛起提供了可供掠奪的資源(如葡萄牙、西班牙在美洲掠奪了大量的貴金屬)和廉價的勞動力(非洲黑奴和亞洲苦力),為其國內日益增長的人口拓展了新的“生存空間”,還為其商品找到了廣闊的外部市場,彌補了國內市場的不足,刺激了國內工業的發展。英國19世紀著名的殖民理論家威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就指出,由于工業經濟體系的內在邏輯,僅靠自由貿易,英國的工業將難以為繼,英國必須進行海外殖民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繁榮,才能避免國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①Bernard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美國學者布勞特甚至認為,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大發現后對美洲、非洲和亞洲人民的殘酷殖民掠奪與盤剝,是殖民地人民的累累白骨和美洲等地的貴金屬及種植園造就了西方世界的整體崛起。②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第249—252頁。
隨著一批批歐洲國家加入海外殖民饕餮盛宴,它們在征服掠奪亞非弱小、落后民族的同時,彼此之間因不可調和的殖民矛盾和殖民爭奪而時常兵戎相見,戰爭頻仍。如表一所示,通過一系列殖民戰爭,歐洲傳統的殖民大國西班牙、荷蘭和法國先后被英國打敗,被迫將大片殖民地割讓給英國。英國成為這一系列殖民戰爭(除了美國獨立戰爭)的最大贏家,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和重要的海上交通線,建立了一個日不落帝國。也正因為這些戰爭,老牌殖民大國西班牙、荷蘭逐漸走向衰敗,潛在挑戰者法國也遭受重大挫敗。英國取代西班牙、荷蘭成為海外殖民大國,并逐漸獲得了海上霸權地位。換言之,英國崛起為世界性大國和海上霸權國與殖民戰爭密不可分。
到19世紀末,隨著德國、日本等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殖民瓜分的行列,要求分享“陽光下的地盤”。它不僅引發了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在非洲和亞洲的瓜分狂潮,也間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畢竟,可供殖民掠奪的土地越來越少,而參與殖民爭奪的國家及其殖民欲求卻日益上升,不可避免地導致后起大國與既有殖民大國的矛盾與沖突,最終兵戎相見。殖民戰爭和爭霸戰爭是殖民體系內在邏輯的延伸和大國崛起的必然產物。
即便美國的崛起被認為總體上是和平的,但事實上也與殖民戰爭和爭霸戰爭有著不解之緣。盡管美國在其崛起過程中沒有從事大規模海外殖民擴張和殖民掠奪,但通過對境內土著印第安人的殺戮和驅逐以及狂飆突進式的“西進運動”,美國占有了與其人口極不相稱、令其他歐洲帝國相形見絀、具有洲際規模的廣袤國土。換言之,美國是通過國內殖民替代了海外殖民,走上崛起之路的。而且,在世紀之交,美國與沒落的西班牙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占有了西班牙在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的殖民地,向歐洲老牌殖民帝國展示了肌肉,并通過參加兩次世界大戰而崛起為全球性大國。筆者整理制作。資料來源: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82—272頁。
不過,這一殖民體系也孕育了促使其自身最終走向滅亡的種子。首先是地理空間的限度。殖民體系的邏輯前提是有足夠的地理空間可供大國殖民和掠奪。然而,隨著歐洲國家經過幾個世紀持續不斷的占有和殖民,地球上的“無主地”和落后地區已經被占領和瓜分殆盡,不再有新的“無主地”或“落后地區”可供歐洲殖民和瓜分。殖民體系面臨無地可殖的尷尬境地。這種基于對土地及其人口的物理占領的體系受到地球物理空間的限制。①張春和潘亞玲將這種基于對他國領土和人口物理占領的戰爭,稱為“尋求生存必需型戰爭”,這與本文提到的殖民體系下的殖民掠奪戰爭有相似之處。參見張春、潘亞玲:《戰爭的演變:從尋求生存必需到維護生存質量》,載《國際論壇》2002年第4期,第14—21頁;潘亞玲:《試論全球化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生存能力》,載《教學與研究》2011年第7期,第89—96頁。
其次是主權規范的普及。西方國家全球殖民的過程,也是主權規范由歐洲向全球擴散的過程。歐洲列強通過發現、占有和建立殖民地,來印證和強化其主權意識和主權地位,但同時也喚醒了亞非拉被掠奪和被剝削地區人民的主權和民族國家意識,極大促進了主權規范的拓展。當亞非拉國家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和努力,在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中獲得行使主權的能力時,主權就不再是少數西方國家的特權,而逐漸成為全球性規范,也成為亞非拉國家反對西方列強掠奪、侵略和干預的利器。主權規范的普及,從根本上動搖了殖民體系的根基和合法性,消解了西方國家以文明標準構建的主權等級體系,破除了“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殖民神話。②感謝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張春副研究員的提醒。他指出,當主權民族國家制度及理念的擴散和推廣到極致,達到全球普及階段,殖民體系本身也就宣告結束了。另可參見潘亞玲:《“文明標準”的回歸與西方道德霸權》,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3期,第39—45頁。
最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是殖民體系最終走向滅亡的加速器。這兩場造成上億人口死亡的世界大戰,不僅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災難,使殖民國家陷入道德破產,無法再以文明傳播者或文明標準制定者自居,同時也極大削弱了它們對亞非拉廣大殖民地的控制能力,促進了亞非拉人民的覺醒,喚醒了它們的主權意識,加快了殖民體系的沒落和最終的滅亡。
三、后殖民體系與大國崛起
如前所述,后殖民體系是一個主權規范在全球普及,各國至少在國際法意義上獲得主權獨立與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它明確將殖民戰爭和殖民掠奪視為非法,并將國家單獨及集體自衛權之外的武力使用權威由單個國家收歸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在這一體系中,出現了防止大國通過武力實現崛起的三重保障。首先,規范保障。主權規范得到公認和全球普及。主權不再是少數西方大國的特權,而是不論大小、強弱之所有國家的普遍身份和權利。盡管冷戰結束后,在一些西方國家出現了超越、弱化主權觀念的聲音和現象,但在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主權意識不是淡化了,而是強化了。在這一規范體系下,即便是打著人道主義旗號的軍事干預,在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下也不具有國際合法性。因而,很難想象一國會公然挑戰主權規范,進行以開疆拓土為目的的軍事入侵和占領。其次,國際法保障。《聯合國憲章》規定了所有成員國主權一律平等的原則,并明確規定除自衛及安理會授權的戰爭外,所有其他類型的戰爭都為非法。在此,除了自衛外,戰爭不再是單個國家可以自行其是的自由度量,而是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的集體裁決。最后,制度保障。通過聯合國安理會這一集體安全機制,任何戰爭行為都必須獲得安理會五常的集體同意或默認。而一旦發生侵略行為,通過安理會的授權,入侵者將面臨國際社會的集體制裁,包括武力的行使。雖然這一集體安全機制在冷戰時期因美蘇之間的尖銳對立,其作用大打折扣,在冷戰后也因人道主義干預問題而飽受詬病,但總的來說,它在制止侵略和限制使用武力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此外,由于主權規范普及和與之相伴隨的民族主義的覺醒和復興,使得歷史上的征服戰爭變得極為困難甚至難以想象,因為任何征服和入侵必然遭到民族主義的誓死抵抗,軍事入侵和占領的成本大大提升了;而軍事技術革新、特別是核武器的出現,使得任何大規模戰爭、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霸權戰爭,變得幾乎不可能。因為這無異于自殺。
與先前的殖民體系相比,在這一主權平等的后殖民體系下,后起大國很難指望通過殖民掠奪或武力開疆拓土實現崛起,只能依靠內部發展及和平的對外貿易。在這一體系規范下,大國崛起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模式:貿易國的興起①關于貿易國興起問題,美國學者理查德·羅斯克蘭斯曾有專著論述了貿易國的興起,指出了貿易國與領土國家之間在對待征服問題上的根本差別。See Richard Rosecra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以及大國門檻的提高。在殖民體系下,由于海外殖民掠奪可以有效彌補國內資源和財富的不足,同時排他性的殖民地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國內市場的狹小,因而像諸如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土狹小、人口規模不大的國家,都可以通過強取豪奪、開疆拓土而崛起為全球性大國。在后殖民體系下,盡管海外貿易可以彌補一國國內市場的不足,但上述國家顯然已被注定無法崛起為全球性大國。只有那些具有廣袤國土面積、擁有可觀人口規模(在人口爆炸的今天,這意味著要擁有約一億左右的人口)的洲級大國或巨型國家才可能成為擁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大國的門檻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由于不能開疆拓土,大國崛起更多地依靠內部建設及自由貿易來積聚財富,這為貿易國的興起創造了條件。盡管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等人早在18世紀就意識到自由貿易對財富增長的重要性,并鼓吹建立一個基于自由貿易之上的“非正式帝國”,而不是建立排他性的殖民地,①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7;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pp. 1-27.但在殖民體系下,自由貿易受到排他性殖民地的頑強阻擊,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當二戰臨近結束、歐洲老牌殖民大國已經被戰爭嚴重削弱時,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開始為戰后的國際經濟秩序謀劃,最終簽署了基于自由貿易原則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為自由貿易的實施提供了國際法依據,也為貿易國的興起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雖然由于冷戰開始阻撓了東西方貿易,但在西方國家內部,自由貿易原則基本上得到貫徹執行;而隨著冷戰在20世紀90年代的結束,自由貿易原則真正在全球得到貫徹。德國、日本在二戰后的崛起某種意義上正是貿易國的崛起。而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也受益于自由貿易,一定程度上也屬于貿易國的崛起。中印等新興大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本國人民的辛勤與汗水,通過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為世界打工”成為“世界的工廠”和“世界的辦公室”而逐漸走上崛起之路。特別是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不僅國內生產總值(GDP)躍居世界第二,而且由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一躍而成為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全球貿易大國。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僅比美國少156.4億美元,達38,667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為 47%。中國已是亞太諸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引擎之一。①《商務部反駁“中國貨貿總額首超美國成世界第一”》,中國商務部網站,2013年2月17日,http://ccn.mofcom.gov.cn/swxw/show.php?eid=42271。
后殖民體系為非西方世界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殖民體系下,西方世界憑借其堅船利炮和技術優勢,將非西方世界變成其可以肆意妄為的“自家菜園”。西方世界的每一次重大技術革新,特別是軍事技術的革新,都會激起西方世界新一輪殖民和瓜分的狂潮,給非西方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和痛苦,把他們推向更深的殖民深淵和窮困潦倒境地。在后殖民體系下,技術進步除了增加軍事威懾力外,更多地是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創造商機和改進普通民眾的生活,用于增加一國的財富。而即便是軍事威懾能力的增加,也無法轉化為赤裸裸的暴力侵略和殖民掠奪,甚至不能用它來打開他國的市場和商機。在此背景下,那些具有廣袤面積、巨大人口規模的非西方世界,如中國、印度、巴西等,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技術引進、模仿與創新,借助于規模經濟,將最終在和平競賽中趕上、超越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國土面積都相對狹小的傳統西方強國,實現非西方世界的歷史性崛起。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的和平崛起,已經初步展示了非西方世界在這一體系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與前景。
后殖民體系時代也是國際制度史無前例地大發展的時期。二戰結束后,聯合國、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關乎國際和平、國際金融與貿易穩定的國際制度先后創建起來。各國被編入一張相互依存的國際制度大網之中。這些制度的創立及演進,不僅頗為有效地維護了國際和平,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際權力格局的演變,一些新的制度被創建起來,舊的制度也不斷進行演進。如七國集團/八國集團、東盟、歐盟、亞太經合組織(APEC)、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的成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現有制度的改革等。這些國際制度既為渴求發言權及國際威望的國家提供了表達自身訴求的場所,也為約束少數大國的單邊行為提供了集體保障,同時還為解決國際沖突和矛盾提供了非暴力工具。②G. John Ikenberry, “Asian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U.S. Strategic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Abraham Denmark and Nirav Patel eds.,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 2009,pp. 97-108.某種意義上,二戰后的“長和平”得益于該體系密集的國際制度網絡。它與主權規范的普及和貿易國的興起一道,為二戰后大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和保障。盡管仍無法杜絕戰爭,但相對于殖民體系,該體系為大國的和平崛起及國際和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結 論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國際體系大致可以分為殖民體系和后殖民體系兩個階段。前者從地理大發現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獲得殖民解放和國家獨立,后者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延續至今。在殖民體系下,主權既是歐洲列強的特權,也是它們對歐洲以外地區“落后民族”進行野蠻殖民掠奪、占領和侵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依據。這一體系是一部分國家享有主權、大部分國家被剝奪主權的等級體系,也是大國通過武力掠奪、殖民而實現崛起的暴力體系。在后殖民體系下,主權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確立并在實踐中得到較好的貫徹。殖民掠奪和通過武力開疆拓土被視為非法,戰爭也被嚴格地加以限制。在這一體系下,國家的崛起只能通過內修政治、外興貿易的方式和平實現,它為貿易國的興起以及具有廣袤國土或眾多人口或兩者兼備的國家的和平崛起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稠密的國際制度網絡,也為約束大國的行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為后起大國實現其抱負和提升國際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場所,也為大國國際威望等級的調整提供了制度化工具,從而更有利于大國在體系內的和平崛起。德國、日本在二戰后作為經濟巨人的崛起以及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在新世紀的群體性崛起,部分證明了后殖民體系的彈性及該體系下大國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預示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與既有大國繼續和平共處的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