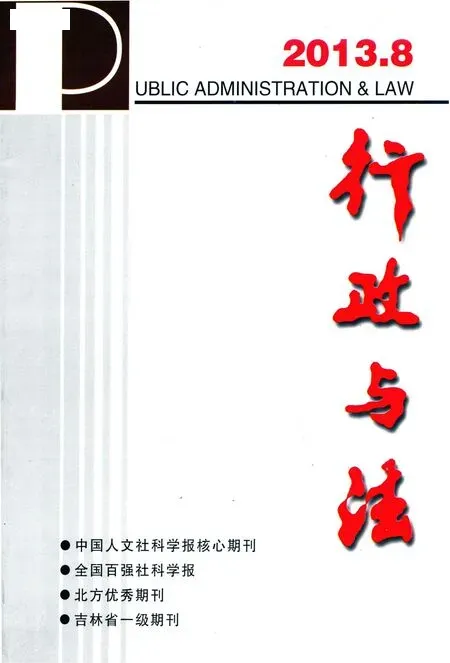論隱私權的憲法保護——以自媒體時代為分析背景
□ 儀喜峰
(上海海事大學, 上海 201306)
在互聯網上,每一個賬號都像一個小小的媒體,發帖子、轉微博、評新聞、頂信息、拋觀點、表態度等數量云眾的信息流共同營造了互聯網上的比特之海。[1]自媒體——自我的小媒體,在億萬網民的努力之下,煥發出巨大的能量。我國現有的50 余家微博客網站,每天更新的帖文數以億計。 從某知名企業家秘密戀情的公布,到“人肉搜索”引擎的強勁啟動,我們看到民間草根通過微博充分實現了言論自由, 但同時公民隱私權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 自媒體在彰顯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權之時,也打開了一扇偷窺公民隱私之窗。在這種背景下, 探討自媒體時代的隱私權及其憲法保護路徑成為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一、自媒體時代的隱私權
(一)隱私權的人權屬性分析
1890年塞繆爾·沃倫和路易斯·布蘭代斯在 《哈佛法學評論》上發表的《論隱私權》一文最早提出隱私的概念,文中將隱私界定為免受外界干擾的獨處權利。之后陸續有學者對隱私的概念予以充實, 逐漸演進到了涵攝信息隱私、空間隱私及自決隱私等內容。我國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隱私是指私人秘密、私人信息、生活安寧和秘密,即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私人信息保護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開等。[2](p16-18)該觀點將隱私界定為私人生活安寧與信息秘密。 但在互聯網背景的映襯下,無疑透出濃郁而鮮活的時代氣息。隱私權應為公民所享有的、保持生活安寧狀態、使私人信息得到保護,免于外界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公布乃至販賣的一種人格權。
在憲法視野下, 隱私權的本質已經超越了民法所構筑的部門法疆域而上升為一項基本人權。《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規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7條規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非法攻擊。”[3](p21)這兩部最重要的國際人權法文件對隱私權作出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規定,它們并沒有明確使用“隱私權”的術語,但卻是通過調整“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對隱私權予以隱性的保護。我國《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這些條文雖然和國際人權法文件一樣,并沒有使用“隱私權”的措辭,但同樣從不同的角度對公民的隱私權加以規制,通過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等間接體現出來。
美國政治學者薩托利認為, 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完整的自由可以說含有以下五個特征:⑴獨立;⑵隱私權;⑶能力;⑷機會;⑸權力。”[4](p341)在薩氏眼中,獨立地位和隱私權屬于消極自由, 因此他更寧愿精確地將其稱為防衛性或保護性自由, 也即古典憲法所規定的“第一代人權”。基于自由權的視野審視隱私權,筆者認為, 隱私權的本質屬性不能局限于從對抗私人或國家權力侵犯的角度來理解, 實際上可能對其遭致侵害的主體包括了國家、社會組織和個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勝任對隱私權予以全方位保護的只有憲法, 因此更應該把它視為單獨存在的一項憲法基本人權。 從隱私權的內容來說,它涉及公民私人活動領域的自由,這些領域不僅涵蓋擇偶、婚配、生育、墮胎、撫養子女等,更包括自主地選擇生活方式、進行價值判斷,自主地進行精神創造活動的自由。從隱私權的功能來說,社會的發展進步離不開社會成員的個人創造, 而公民的創造性主要源于自由,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人們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斷提高, 更加重視對于公民隱私權的憲法保護,正是尊重獨立的個體價值的良好體現。在基本人權視角下, 隱私權在憲法中的功能就是確保公民個人的私人信息與私人秘密不被外界非法獲得和利用,對私人事務和活動具有完全自決權。
(二)自媒體時代的隱私侵權特性
自媒體時代, 侵犯公民隱私權的表現已與往昔迥然有別。一是隱蔽性。在互聯網上,大多數人不會使用真實身份, 使得很多侵權行為發生后無法查找侵權主體;并且侵權手段極為隱蔽,侵權人可能會利用網絡運營中不被用戶知悉的跟蹤軟件非法搜集用戶隱私,盜取網民的個人數據。二是侵財性。“自媒體”時代對隱私權的侵犯除以窺探他人隱私為目的外, 還包括很多以營利為目的,以經濟利益為驅使的侵權。網絡服務商會利用網絡跟蹤軟件來跟蹤網絡用戶在其網站內的一舉一動,他們會以為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為借口,而實為大量收集用戶的個人信息,包括用戶的上網喜好、上網習慣等。單一用戶的信息自然價值有限,但如果將眾多用戶的信息予以匯總、分析,即通過對收集來的用戶個人信息進行整合, 從中提煉出對網絡服務商自身或第三方有利的信息, 則網絡服務商就可以從中獲得經濟利益。 三是侵權的便捷性和嚴重性。 在傳統媒介時代下,新聞信息能否傳播以及靠何種渠道傳播,基本上取決于媒介的監管人或把關人, 他們一方面要應對大量信息, 另一方面要篩選信息, 決定著新聞的初始信息源。一個人即使想向公眾傳播、發送含有他人隱私的信息,但經過報紙電視等傳媒嚴格的層級過濾,侵犯隱私的事情并不容易發生。然而在自媒體情境下,基于互聯網不受時空限制的擴張性, 含有隱私的信息傳播變得異常便捷,只需輕點鼠標,就可將該隱私信息變為盡人皆知的公開秘密;與此同時,一般的社會大眾既是信息的生產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普通大眾缺少專業媒體人的新聞直覺和職業素質, 他們在面對侵犯他人隱私的信息時不能很好地從職業規范以及新聞專業的角度充分考量, 而使這些隱私有披露和在更大范圍內傳播的隱患,傳播的速度越快、范圍越廣就意味著他人隱私權被侵害的后果越嚴重,救濟也就越難以實現。
二、我國隱私權法律保護的現狀
我國的民法、 刑法和行政法等部門法對隱私權的保護已經作出了一些規定。《民法通則》 對公民的生命權和名譽權等予以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的隱私,或捏造事實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侵犯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條第3款規定:“對未經他人同意, 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 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上述司法解釋在字面上明確使用了“隱私”一詞,通過保護名譽權等民事權益的方式,間接地對公民隱私加以保護。2009年頒布的《侵權責任法》則直接把隱私權作為單獨的人格權加以規范。該法第2條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隱私權……等人身、財產權益。”該規定奠定了隱私權獨立的法律地位, 在我國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與民法保護相近,刑法、行政法也是通過保護住宅和身體健康的方式,間接調整了隱私權,訴訟法則明確地規定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不予公開審理。
自媒體時代, 全球化的信息網絡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快速而徹底地改變和塑造了社會,推動著社會關系的變遷和發展, 其中隱私權的傳統法律保護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戰。在自媒體的推動之下,個人信息漸漸成為隱私權重要的客體, 而網絡媒體的盛行和政府對公民權利的干預, 又使個人信息極易被濫用和侵犯,現有法律的零星規范,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出現的隱私侵權問題。 這種缺少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狀況,也正是目前最根本的局限或缺陷,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亟需一套完整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規范加以調整。基于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0年通過的《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第4條規定:“為了保護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人身、 財產等合法權利, 對有下列行為之一, 構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二)非法截獲、篡改、刪除他人電子郵件或者其他數據資料, 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2005年信息產業部制定的行政規章《電子認證服務管理辦法》 第20條規定:“電子認證服務機構應當遵守國家的保密規定,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電子認證服務機構對電子簽名人和電子簽名依賴方的資料, 負有保密義務。”這些法律規范對現行的網絡侵權問題作出了初步規制。
三、憲法保護隱私權的必要性與路徑選擇
(一)憲法保護隱私權的必要性
憲法對公民隱私權加以保護存在著合理性與必要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刑法、行政法和民法作為部門法,在保護公民個人隱私權時有其天然的局限性。部門法受自身價值本位所限, 只能在局部領域內以單維度的努力使隱私權得到最大保護, 部門法的不自主性決定了它們應該從憲法那里獲得滿足其自身存續的必要條件, 而要使隱私權保護的范圍和內容盡可能得以擴展和延伸, 只能尋寄希望于更高位階法律即憲法來承擔。憲法所構造的“法秩序”具有自治性和整體性,“各部門法必須被一個法律網絡調整和控制著,任何超越法網的行為都將受到國家機構的有效制裁, 憲法的主要作用在于調整這個法網。”[5](p4)憲法通過營造“法律之網”安排各種社會關系,彌合部門法之間權利保護的間隙所導致的隱私權保障的空白區域, 使隱私權保護從單行法律鋪墊的平面場域提升至由憲法引領、部門法拱衛的立體結構。憲法保護隱私權,不僅提供了最高法的依據,而且還將有效整合現有分散零碎的資源。另一方面,從客觀現實來看,對隱私權加以憲法保護也為一些國家的憲政實踐所證實。自媒體時代,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政府對公民權利的干涉, 公民的隱私權受到損害的可能性來自于包括國家、 社會組織和個人在內的任何一種侵權主體, 為對抗各種侵害所設立的實體法與程序法保障在屬性上只能是憲法保障。 出于對抗國家公權力的需要, 憲法保護隱私權能賦予公民個人更加充分的自治空間, 個人自治作為個人自決權的價值形態呈現, 其終極目標就是在于對不可侵犯的人格尊嚴的極力肯定。就國外而言,德國憲法對隱私權的保護可謂是良好的楷模。在德國,尊重人格和人格尊嚴是隱私權的核心, 人格尊嚴寫入憲法并經多年憲政實踐之后, 以人格尊嚴作為隱私權憲法保護的終極價值終于得以確立, 它是個人有尊嚴地生活包括個人生活安寧不受侵擾、個人私人秘密不受窺探的權利支撐,而其支撐的對象是絕對的, 涵蓋了公民之間平等的民事權利及政府的公權力。[6]美國憲法“隱私權”觀念的生發,則是聯邦法院通過解釋憲法第4條修正案中“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產的權利”的相關內容,結合大量涉及隱私權的司法案例,在1965年確定隱私權為美國憲法權利之一。[7](p1117-1118)
(二)憲法保護隱私權的路徑選擇
隨著互聯網科技的不斷進步, 公民隱私權的表現方式隨之有了更加復雜的形態, 據此賦予憲法中的隱私權更加豐富全面的內涵是當務之急。在我國,憲法作為根本法,它對隱私權的保護屬于“隱性”而非“顯性”的保護,也即沒有采取隱私權“入憲”的列舉方式,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隱私權的憲法保護路徑作出選擇。
⒈完善隱私權保護的憲法依據。憲法以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為根本宗旨。 在當前大量侵權事件不斷涌現的情形下, 人們的精力似乎都集中在把重要權利寫入憲法,自媒體時代所凸顯的侵犯隱私問題,順其自然地令人想到了“隱私權”入憲。通過立憲主義來強化對于公民隱私權的保護, 把隱私權從普通法權利上升到憲法上的權利, 從而確立公民在合理范圍對抗政府公權力的合法性, 這對于個人價值的肯定與尊重極為重要。但筆者認為,相比“入憲”論,通過憲法解釋方法明確隱私權是一種未列舉的人權更為重要, 此舉不僅避免了動輒修憲、僅注重憲法權利宣告的學齋式沖動,而且充分發揮了憲法規范自身的彈性空間, 使其在維護基本人權方面更富活力。因此,在憲法規范中尋求隱私權保護的直接依據, 并不一定要在憲法之中設立隱私權的條款。 我國憲法已經確立了對基本人權和人格尊嚴的保障,故而可以把“人格尊嚴”解釋為隱私權保護的最高價值目標,把“保障人權”的基本條款視為隱私權保護最直接依據, 由此隱私權保護獲得了明確的價值導向和直接的憲法依據。 同時, 通過憲法解釋方法, 通過強調公民對憲法的守護, 使公民住宅不受侵犯、 通信自由和通訊秘密受保護的憲法條款擁有一定的開放性, 根據憲法的精神和原則漸漸培育和生成隱私權這項未列舉基本權利的保障條件。
⒉強化違憲審查制度的執行。 違憲審查在保護憲法基本權利方面居于核心地位, 保障憲法基本權利不被侵犯是違憲審查的主要任務。 對隱私權予以憲法保護, 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防御立法權和行政權等國家權力對隱私權的侵犯。 隱私權的法律保護訴求在自媒體時代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 不斷有新的隱私利益涌動,也不斷有花樣翻新的侵權形式出現,而國家權力的行使隨時都可能觸犯各種隱私利益和私人生活自由權,因此更需要強化違憲審查制度的貫徹執行。具體而言,主要是審查立法部門(包括權力機關立法和行政立法)是否侵犯了憲法隱私權,通過人權和人格尊嚴條款解釋立法是否侵犯了未明確列舉的隱私權利益, 這不僅能有效地化解隱私權客體或內容被國家權力侵越的風險,直接保護基本人權意義上的隱私權,而且可以適應隱私權的自身發展需要, 營造一個隱私權憲法保護的開闊空間。 這種保護體現了隱私權的延伸性與憲法人權保護的有機融合, 滿足了自媒體時代權利拓展與權力擴張雙重驅動態勢下基本權利保護的需要。
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房地產登記材料查閱暫行規定》第7條明確規定了查閱房屋登記原始憑證的權利人的范圍, 即必須是房地產所有人和抵押權等相關權利人,其他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均不得隨意查閱涉及房地產原始憑證的信息。如果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要查閱房地產信息資料,也只能局限于和這些部門調查、 處理的案件有關的原始憑證。 該項規定自覺地落實了我國憲法和立法法設定的違憲審查制度,換句話說,國家權力主動地承擔了消極不侵犯隱私權的責任。另外,國家機關尤其是行政管理部門不能隨意要求行政相對人提供與行政行為無關的信息,對依法收集到的涉及家庭住址、電話、車輛、金融、保險、醫療、銀行賬號等信息應予保密,政府部門不得泄露或曝光個人隱私,以免被不法分子獲取。這些信息一旦被其他組織或個人非法獲取, 則權利人將面臨不可預測的巨大風險。
⒊通過部門法落實和實施憲法隱私權。 通過法律的憲法實施體現為一種內在的生活方式和外在的社會秩序,憲法將其文本規范、價值精神、基本制度和政策性宣言等融合于立法權、 司法權和行政權的行使過程中,且不發生合憲性質疑,憲法就得到實施。[8]就憲法隱私權保護而言, 將其價值和精神貫徹到部門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活動中,通過部門法的適用來保障憲法基本權利,最終實現對隱私權的憲法保護。也就是說,隱私權的憲法保護還需要依靠部門法的適用來實現。
關于自媒體環境下隱私權保護的法律不完善問題,我們可以借鑒一下歐洲國家和美國的一些做法。總體而言,關于隱私權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兩種,即以歐洲為代表的統一立法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歐盟先后頒布了《個人數據保護指令》和《電信事業個人數據處理及隱私保護指令》,之后一些主要國家相繼依指令分別規定了本國的《個人數據保護法》,形成了以政府主導特征的歐盟個人數據保護制度。 美國沒有采用統一的立法模式, 也沒有統一的個人隱私方面的執法機構, 而是采取了針對不同的行業予以立法與行業自律相結合的分散模式, 陸續出臺了 《信息自由法》、《公平信息報告法》、《隱私權法》、《金融隱私法》和《兒童網上隱私保護法》等法律。
目前,我國電子政務發展十分迅速,已成為最容易侵犯公民隱私權的領域, 制定個人隱私保護法已成為當務之急。我國正在醞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對政府掌握的紙本和電子文檔形式的個人信息記錄予以了調整, 建議稿還確立個人對于私人記錄的收集、利用的知情權、變更權、修改權、監督控制權。須指出的是,政府保護個人資訊隱私的義務是與政府政務公開密不可分, 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的落實必須與我國現行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相結合。
⒋完善行業自律等民間法規范。 行業自律等民間規范的確立是以業內的執業標準和執業道德規范為依據的。具體而言,網絡服務商應當制定相應的隱私權保護聲明,將其公布于其網站主頁的顯著位置。該聲明應當說明收集個人資料的范圍和使用方法, 并告知其對于個人數據信息所應有的權利。 自律主體不僅包含網絡服務商,還應包括政府、公共事業部門等所有在互聯網上提供商品、服務或信息的主體。此模式最大優勢在于倡導和貫徹自律自治原則, 創造一個開放的行業發展空間,以鼓勵和促進網絡產業的發展。我國是網絡使用大國,但在網絡行業自律方面處于初級階段,這就需要借鑒外國的先進經驗,建立完善的行業自律機制,促進我國網絡產業健康發展, 為公民的個人信息的安全營造一個和諧的網絡環境。
在自媒體時代, 保護公民隱私權應當建立一個由憲法統領的、靠部門法具體實施的、多層級和全方位的立體保護架構。 基于憲法人權的視野探究隱私權保護問題,需要完善隱私權保護的憲法依據,同時克服“隱私權”入憲的學齋沖動,而是將其置于信息社會和互聯網背景之下綜合考量,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違憲審查制度的執行和部門法落實方面。 互聯網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標志,由網絡自媒體產生的隱私權侵權行為,也需要國際間的共同合作加以維護。 我國在致力于維護網民隱私權的同時,應當積極吸收外國經驗,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只有與世界接軌,我國才能最終實現公民隱私權的切實維護。
[1]http:/ /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1-12/02/c_122365343.htm[EB/OL].
[2]張新寶.隱私權的法律保護[M].群眾出版社,2004.
[3]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國際人權文件匯編[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馮克利,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8.
[5]張千帆.憲法學導論[M].法律出版社,2004.
[6]龍衛球.論自然人人格權及其當代發展進路——兼論憲法秩序與民法實證主義[A].許章潤.清華法學(第二輯)[C].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7](美)保羅·布萊斯特等.憲法決策的過程:案例與材料[M].張千帆,范亞峰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8]儀喜峰.論通過法律的憲法實施[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