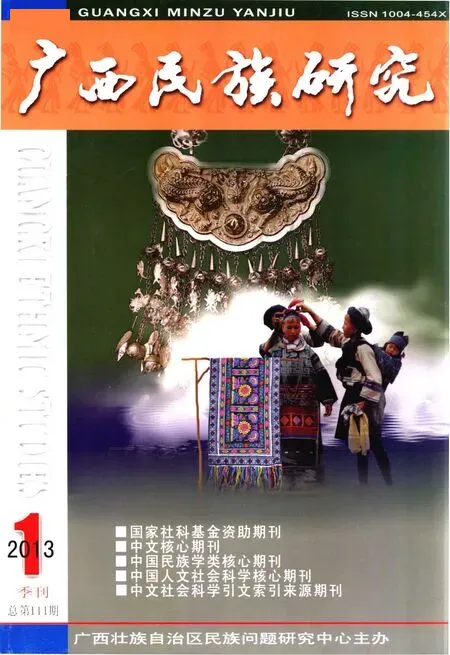我國民族民間藝術的歷史文化價值*
崔鴻飛
一、民間藝術的界定及意義
民間藝術最早是作為民間傳統文化的分類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的,直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正式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民間藝術才正式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自此,民間藝術成為人們的關注點,掀開了它神秘的面紗,其對于族群、人類、社會的影響與作用也逐步被人們認知、理解與主張。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曾強調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偉大文明的結晶和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是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展示,是人類文化整體內涵與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蘊涵著該民族傳統文化的最深根源,保留著形成該民族文化身份的原生態,以及該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心理結構和審美概念等”。[1]79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演化與產生過程,可以說就是對其重要性認識的過程,它的價值自然附著于這種重要性意義之中。《公約》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2]22直觀理解這個概述,可以發現其功能意義體現在多個方面:概念涵蓋面的廣泛性及規定性;遺產的傳承性與創造性;持續的支撐性與強化性等。其實,概念隱含的涉及空間向度的意義以及概念構成元素之間相互作用呈現的意義遠遠超越我們的直觀認識,它更加寬泛、深厚。概念產生背景所揭示的意義已經突破概念本身的劃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始終伴隨其意義指向,“存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與人類的相互關系中,存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人類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中。”[1]77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在于它直接關系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它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保證。”[2]20事物的功能往往決定其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意義自其概念建立之時就已被植根其中。
二、歷史文化價值體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體系中
近些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持續升溫,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對其進行“搶救與保護”的高潮。其中,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評估、考察與論述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涌現出大量的學術著述。這些相關的著述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實例闡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為我們建立了體認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體系的清晰視角。如王文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系統劃分;烏丙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方法》中涉及眾多保護對象所揭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還有菅豐著、陳志勤譯的《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蔡清泉的《文化遺產價值論析》、張世軍的《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等等。歸結起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比較系統的劃分當屬王文章主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一書。書中首先強調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系統性,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它們不是單一、靜止的,而是多樣、動態、系統的,構成了一個多維、立體的價值體系。”同時也強調“這些多種多樣的價值既不是完全等值,也不是互不相干,而是有著深層與表層、歷時與共時、基本與特別之分。”[1]81在其構建的價值系統中,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劃分為基本價值與時代價值。基本價值是指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直接發生作用并產生效果的價值;而時代價值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乃至后現代與時代精神對應的意義所體現出的作用與效果,如教育價值、經濟價值、創造價值、紀念價值等。書中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自身特點,為全面、準確揭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方面入手,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價值分為歷時性基本價值與共時性基本價值。其中歷時性基本價值包括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共時性價值包括科學價值、社會和諧價值和審美價值。這種劃分不但兼顧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多樣性和系統性,也為我們構建了以立體、綜合、全面的視角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結構體系。顯然,歷史文化價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體系中最核心的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系統是對其系統元素價值的總體概括,或者說,這個價值體系是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叢結而成,具有公式化和模式化的效果。但是,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可以發現,對于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其所呈獻的價值在空間與時間的向度上都是有差異的。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歌舞類項目與手工類項目的價值向度就明顯不同,雖然都強調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但歌舞類側重娛樂性,手工類則更多體現出美術性。同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歷史時期作用于不同的人群,其價值也迥然不同。在實踐中,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體系的認識與構建,不能照搬照套,要避免以價值找內容的行為,要善于捕捉住其核心價值。“要找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不能像目前的有關文化政策中所表示的那樣,從遺產本身那里去尋找,而應該在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與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之中,才能找到其新的價值”。[3]盡管民間藝術的遺產價值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體系的關照下呈現出鮮明的歷史文化價值取向,但是對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歷史文化價值評析,應該置于傳承、保護的場景中去觀察,審視其與環境 (指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共同構成的環境)的關系,從互動中去發現價值所在,這樣才會具有針對性和準確性。
三、歷史文化價值體現在歷史演進過程中
2005年6月,我國開始進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與評審工作。經評審、公示,報國務院審批,2006年5月20日,國務院正式批準了51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并向全國公布。這些被列入名錄的項目,以其不同的表現形式成為該領域的文化精華,我們可以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的評審標準中窺見它們的歷史文化價值。《辦法》明確規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應具有展現中華民族文化創造力的杰出價值;具有促進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增強社會凝聚力、增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紐帶;具有見證中華民族活的文化的獨特價值;對維系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具有重要意義。顯然,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杰出的價值意義,它是多方面和多維度的,并在其意義指向中構建與功能對應的價值體系。
我們以土家族擺手舞、蒙古族長調民歌、侗族大歌、川江號子四個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例,通過追溯其發生、發展的活態歷史流變過程,來反觀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價值體現。
土家族擺手舞流行于湖南、重慶、湖北、貴州等土家族聚居區,是土家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表現。擺手舞產生于土家族古老的祭祖儀式中,距今已有近千年歷史。它集歌、舞、樂、劇于一體,具有廣泛而豐富的歷史和社會生活內容,對研究土家族的族群構建、文化歷史、社會生活、民風民俗、宗教信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蒙古族長調民歌的產生歷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額爾古納河兩岸山林地帶向蒙古高原遷徙,生產方式也隨之從狩獵業轉變為畜牧業,長調這一新的民歌形式便產生、發展了起來”。[4]長調民歌充分體現了蒙古族的歷史文化特征,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與蒙古族人民的社會生活相伴而行,它全面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勞動生活和歷史文化;研究與保護長調民歌就是對草原文明有力的傳承與保護。
“侗族大歌歷史久遠,早在宋代已經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宋代著名詩人陸游在其《老學庵筆記》中就記載了‘仡伶’(侗人自稱)集體做客唱歌的情形。至明代,鄺露在其所著《赤雅》一書中更加明確地記載了侗人‘長歌閉目’的情景,這是數百年前侗族大歌演唱的重要文獻”。[4]侗族大歌是我國民族民間音樂中的奇葩,其多聲部合唱極其罕見,具有很高的音樂欣賞與研究價值。這種演唱方式是侗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過程和生產勞動中創造的民族文化,是侗族歷史文化價值的體現。它不但是人們交流情感、傳遞文化的媒介,也把侗族的歷史文化融鑄其中,成為侗族人民的精神符號而不斷延續。
川江號子流傳于金沙江、長江及其支流一帶,具有悠久的歷史。近期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期的“石錨”和東漢時期的“拉纖俑”等文物,可以印證川江水路運輸業的歷史。川江號子刻畫了船工與江水搏斗、抗爭的場景,生動地表現了勞動人民戰勝自然的堅強意志,歌頌了人類不屈不撓、團結奮進的精神。川江號子的旋律伴隨湍急的江水而出,曲調起伏高亢、一領眾和,好像在展示人們團結協作的力量,把人們戰勝自然的智慧與無畏表現得淋漓盡致。川江號子是用汗水和生命凝鑄而成的畫卷,更是用歷史和文化雕刻而成的人類化石。
作為民間藝術的代表,不管是土家族的擺手舞、蒙古族長調民歌、侗族大歌還是川江號子,它們都源自社會生活,是各族人民生產生活的真實寫照,是各族人民勞動智慧的結晶。它們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與歷史文化相伴,表現出強大的活力,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自身的價值也體現在這個演進過程中。雖然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在述說、傳遞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但都反映了各族人民生動的實踐場景,展現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傳承歷史文化、促進社會穩定、規范人們行為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其對于人及社會作用的效果,才一直被人們重視,其價值也在這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體現出來。
民間藝術的歷史文化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的產生與當地的歷史過程、族群構成緊密關聯,是人們世代沿襲傳承下來的歷史文化;它不但記錄、保留了人們生產生活習慣、民風民俗、倫理觀念等歷史文化元素,也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是歷史文化的遺存,具有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內容;它融入了當地人的生產生活,是人們情感的再現,在社會發展與政權更替中成為活態的、流動的歷史文化見證。值得強調的是,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源于民間、以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使其積累與傳承帶有一定的隨意性、經驗性,是比較脆弱的文化形態。在文化變遷過程中,很多脆弱的文化被歷史覆蓋,但流傳至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是文化中的精品,是當之無愧的活態文化。作為活態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但可以讓我們回顧歷史、借鑒歷史,也為彌補官方正史典籍的不足、遺漏或諱飾提供依據,更有助于人們真實、全面接近歷史文化的本原。正是源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記錄、傳承、表現歷史文化的功能、特征,具有作用于人類、社會所表現出的文化先進性,它必然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文化價值。
四、歷史文化價值體現在展演與贊譽中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留給我們的財富,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它把鮮活的歷史與人類文明進步的生動歷程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對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化創新具有重要意義。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體系性與豐富性,其文化價值就表現出層次化與多向度。文化價值不但體現在非物質文化價值結構體系中,體現在歷史演進過程中,也在不斷的展演與人們的贊譽之中體現出來。
以“花兒”為例。“花兒”是流傳于我國西北部民間的一種山歌,亦稱“少年”,主要流傳于甘肅、青海、寧夏與新疆等省區,在回、漢、東鄉、保安、藏、裕固等民族中廣泛流傳,被譽為“大西北之魂”、“活著的《詩經》”。2006年,經國務院批準,被列入我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從“花兒”申報地區或單位來看,有寧夏回族自治區申報的寧夏回族“山花兒”;有甘肅省康樂縣蓮花山“花兒會”、和政縣松鳴巖“花兒會”、岷縣二郎山“花兒會”;有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老爺山“花兒會”、互助土族自治縣丹麻土族“花兒會”、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七里寺“花兒會”、樂都縣瞿曇寺“花兒會”等三省區的廣泛區域。一種民間藝術形式多個地區同時申報,足以證明其流行區域的廣泛性,這樣的覆蓋面不但可以反映出“花兒”具有廣泛性、民族性、認同性、區域性等典型特征,也體現了它的極其珍貴的價值。對于不同展演區域的“花兒”,其表現形式、藝術風格雖然體現出差異性,但是從中獲得的評價與贊譽卻都是源于“花兒”本身。
蓮花山“花兒”具有獨特性、民俗性、依存性、程序性、群體性、娛樂性和通俗性等特征,被譽為“西北之魂”、“西北的百科全書”。岷縣二郎山“花兒會”所唱的“洮岷花兒”,除了具有音樂價值和即興演唱價值外,歌詞的文學價值也極高。它與湫神祭祀一樣,凝聚了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研究岷縣社會發展歷史和民俗文化的寶貴資料。因而洮岷“花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聯合國民歌考察基地”榮譽稱號。老爺山“花兒會”的“河湟花兒”語言生動、形象、優美、明快,多用賦、比、興等修辭手法,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代表曲目有《大通令》、《東峽令》、《老爺山令》等。丹麻“花兒會”是展示土族民俗風情的一個重要文化場所。代表曲目有《尕聯手令》、《黃花姐令》、《楊柳姐令》等。丹麻“花兒會”演唱的內容蘊含著豐富的土族文化內容,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七里寺“花兒”演唱者一般一手輕捂耳朵,根據內容需要用不同的“令”來演唱,代表曲目有《古鄯令》、《馬營令》、《二梅花令》等。瞿曇寺“花兒會”演唱曲令有《碾伯令》、《白牡丹令》、《尕馬兒令》、《水紅花令》、《三閃令》等。它的最大特點是兩個陣營的對歌。瞿曇寺“花兒會”是研究大型民俗活動與地方文化發展關系最好的典型個案。“山花兒”是廣泛傳唱于寧夏回族聚居區的一種代表性民歌體裁。具有復合性、多元性文化特征,其代表曲目有《黃河岸上牛喝水》、《看一趟心上的尕花》、《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兒本是心上的話》等。
從上個世紀40年代初起,“花兒”就被專家、學者關注,其音樂文本逐步展現在世人面前。新中國建立后,對“花兒”的理論研究不斷升溫,除了國內大批學者的理論著述外,也吸引了國外學者的目光,使得“花兒”成為中國代表性民間藝術傳播到海外。20世紀50年代,“花兒”先后被改編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藝術作品,享譽海內外。如小提琴獨奏曲《花兒》、歌舞《花兒與少年》等。著名歌唱家胡松華就曾在27個國家演唱過“花兒”;由寧夏歌舞團創作的大型民族舞劇《花兒》可以說是“花兒”的杰出代表,它集民間藝術、現代藝術、文學故事為一體,生動呈現了“花兒”所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資源,體現出傳統民間藝術的優秀文化價值。迄今為止,寧夏的《花兒》在國內公演百余場,并應邀出訪了韓國、馬爾代夫、塞舍爾、土耳其等國,受到好評。該劇榮獲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戲劇會演大戲金獎,是2009-2010年度、2010-2011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資助劇目,喜獲“五個一工程獎”;《花兒》片段“金色湯瓶”獲第二屆中國·寧夏回族舞蹈展演表演一等獎、第九屆全國舞蹈比賽群舞表演一等獎。2012年7月,在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中,《花兒》獲得表演金獎,并獲最佳音樂獎、最佳演員獎、最佳新人獎等獎項。
從參與“花兒會”的人群構成來看,可以說它就是一個民族團結的盛會,對于“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花兒會”不但增進文化交流,也增強民族認同感,體現出民間藝術的文化交往、傳播與認同價值。“花兒會”上演唱的形式不同的優秀作品不但呈獻出“花兒”的藝術特征,也反映了一段時期的歷史文化。“花兒”在地區、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展演獲得一致好評,這足以證明“花兒”的藝術魅力。
歷史文化才是支撐民間藝術提升、發展的堅實平臺。僅僅從“花兒”展演過程中的一個片段,就已凸顯出其藝術表現的深度與廣度,以及民間藝術的歷史文化價值。人們對“花兒”的贊譽,與其說是對其藝術表現的稱贊,不如說是對“花兒”歷史文化價值的褒揚。
五、歷史文化價值體現在具體事件中
在當代,人們越來越重視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尤其是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認知,體現出前所未有的自覺。人們對文化認知的趨同,不但表現在保護與傳承上,也表現在對文化價值意義的審視上。我們可以通過某些事件去感知人們對于傳統文化的崇尚與追求,從而印證民間藝術的歷史文化價值。
流傳于重慶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秀山花燈,是集宗教、民俗、歌舞、雜技、紙扎藝術為一體的一種古老的民間歌舞說唱藝術和民間文化現象。2006年5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秀山花燈已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秀山花燈作為當地重要的民俗活動,歷經數百年的發展、演變,已經成為秀山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1957年,林祖炎、謝必忠、金干、潘琪幾位藝術家首次到秀山采訪花燈音樂和舞蹈,就聽到了“黃楊扁擔村”(原白粉墻村)民間花燈藝人嚴思和唱的《黃楊扁擔》。他們如獲至寶,贊不絕口:“萬萬沒有料到秀山花燈唱腔竟如此優美!”1958年1月,《四川花燈戲曲》首次刊載了《黃楊扁擔》詞曲;朱寶勇首次演唱《黃楊扁擔》,并由中國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從此以后,優美抒情的秀山花燈歌曲《黃楊扁擔》一直被人們傳唱。李雙江、蔣大為等歌唱家都曾演唱過《黃楊扁擔》并灌制成唱片在全國發行。1987年春節期間,中央電視臺播映了交響樂《黃楊扁擔》,把秀山花燈曲調推向更大的平臺。同時,《黃楊扁擔》也被《中國民歌選集》收錄,成為中國民歌的精華,體現出巨大的文化藝術價值。
然而,正是由于《黃楊扁擔》的文化價值,2002年發生了《黃楊扁擔》所屬權爭議的“文化事件”。雖然事件很快在有關部門的干預下得到解決,但是留給人們的思考卻很多。它的直接原因或許是利益驅使,是企圖獲得文化資源的行為,或許是想利用優秀文化資源實現其經濟的發展,但是,明確了其傳統文化的價值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對于文化的重要性,布迪厄指出:“當代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不同于早期資本主義的地方,就是文化因素已經深深地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部門,以致可以說,當代社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文化在整個社會中的優先性以及文化的決定性意義。相對于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等其他領域,文化已躍居社會生活中的首位。”[5]14傳統社會經濟注重物質生產,以商品生產為主要形式,其價值體現在使用和交換兩個方面。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非物質性集中表現為文化價值,其核心是追求文化的附加值。可以說,非物質文化的附加值因素決定了文化在社會中的優先性以及決定性意義,也是整個社會及各個階層看重文化并依托其發展的根由。文化的價值又是如何體現的呢?布迪厄認為:“資本是累積性的勞動 (以物化的形式或具體化、肉身化的形式),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這種勞動 (資本)使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6]127很顯然,文化也是資本。“文化資本”是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核心概念。《黃楊扁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高度重視的時代背景下成為了“文化資本”。地方政府意識到文化資源在發展經濟中的優先性和決定性價值意義,都努力尋找屬于自己的文化資源。把目光投向《黃楊扁擔》是看重其良好的文化資源優勢,對于經濟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來說,文化資源的占有與建工廠、開礦山、辦農業等具體的投入相比較,顯然對高附加值的無形資源的利用比創造有形的、具有投入風險的具體物質經濟行為更環保、更容易,可持續發展的“內動力”更強大。從這一點上看,爭議雙方都看到了“文化資本”里隱藏著巨大的“經濟資本”,是一個地區得以持續、快速發展的有力保證。這一事件也映射出,在文化引導消費的當今時代,歷史文化資源對地方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優勢,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文化價值的開發將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導。
總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藝術的歷史文化價值體現在歷史時空中,也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多維關系中,我們不可能列舉出其所有功能,也很難全面評估其價值,因為它的功能伴隨時代發展、變遷而被不斷地擴展。但是,它對于當地經濟社會建設的作用、對文化藝術的影響,以及它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典型代表的價值體現,都是顯而易見、不可替代的。它“是鮮活的文化,是文化活化石,是生活中的文化智慧,是原生態的文化基因”;也是“活的歷史,提供了我們直觀的、形象生動的活態形式認識歷史的條件”。[1]86新時期,民間藝術必將在地方文化、經濟、社會建設中發揮越來越強大的作用,體現出更多更珍貴的價值。
[1]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公約選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3]菅豐,陳志勤譯.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J].文化遺產,2009,(2).
[4]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EB/OL],http://www.ihchina.cn/inc/guojiaminglunry.jsp?gjml_id=034,059.
[5]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
[6]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利: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