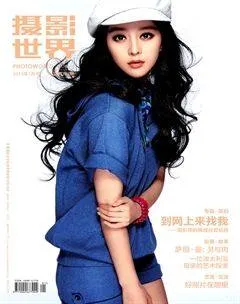加沙日記




戰火中加沙的天際線,對我來說就像是夢境與現實的交割線:在空中的是夢,F16戰機隆隆的盤旋聲,導彈尖銳的發射聲,騰空升起的火箭彈,我因親眼目睹這些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而感到熱血沸騰;在交割線以下,爆炸的導彈散發著蒸騰的氣流,到處是被炸毀的廢墟,散落一地的肢體碎片,殘留的烏黑血跡。這是活生生的現實世界。
簽完“生死狀” 才能進加沙
2012年11月15日,也就是巴以沖突升級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接到任務,收拾了最簡單行李,從約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市火速趕往加沙地帶。
顛簸的山路走了4個小時,在離埃雷茲檢查站(外國記者從以色列進入加沙的唯一通道)還有數公里的地方,我們被以色列士兵攔了下來,一位負責接待媒體的女兵語氣親切地告訴我們,由于附近交火激烈,檢查站暫時關閉。
于是我們決定去附近的加油站簡單吃頓午餐。從點餐開始,防空警報就此起彼伏,每次響起,周圍人都放下手中刀叉緊張地搜尋著火箭彈的位置。我一邊大口吃著意大利千層面,一邊看著眼前空中的“鐵穹”(以色列的火箭彈攔截系統)攔截火箭彈后火光四射的爆炸場景,感覺像坐在電影院第一排看戰爭片。我懊惱地想:這應該是這個月最后一頓像樣的午餐了。
一直等到臨近傍晚,我們才被告知交火減緩可以通過。進入檢查站后以軍沒有立刻放行,而是先把所有人帶到了邊上的一個小房間里。
在那里我們每人都收到一份2頁的文書,并被要求簽字。我瞄了一眼標題,是《對以色列國防軍軍事行動的承諾書,暨對媒體公司的警告、免責書》(“Letter of compliance to be embedded in IDF combat operations,Letter of warning,undertaking and waiver for Media company”)。天哪!這不就是傳說中的“生死狀”嗎?
同事要我仔細看看各項條款,我說:“還看啥啊,不簽也不會讓你進去的!”于是我們趕緊簽完,一溜煙地過了檢查站。(圖2)
血色殘陽下的加沙新年
進入加沙后,本應在哈馬斯的邊檢辦入境手續,但平日里用集裝箱改裝成的小辦公室早已人去樓空,我們的巴勒斯坦司機說:“哈哈,別急,馬上讓你們看到他們的藏身之處。”他繼續向前開,左拐右拐來到一處民宅,在民宅背后,我們找到了正蹲在地上給外國記者做登記的哈馬斯邊檢人員。他們神色匆忙而慌張,場面也很混亂,在給我們快速辦完后,不耐煩地揮揮手:“快走吧,快走吧!”
隨后,我們坐著“天價”出租車向以軍轟炸最猛烈的加沙城前進。一路上,哈馬斯武裝人員不斷從加沙各個角落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加沙原本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有將近200萬人生活在這個面積還不及北京市海淀區的狹小地帶(海淀區面積426平方公里,加沙地帶365平方公里)。
這天是伊斯蘭歷新年第一天,原本車水馬龍的大街卻空空蕩蕩,成了那些膽大的孩子們的足球場,天真無畏的孩子們在殘陽下歡笑著踢球的身影,和遠處天空火箭彈與導彈交織殘留的軌跡,構成了加沙人充滿血色的新年回憶。
戰地的“危險區”與“安全區”
在加沙采訪最讓我緊張的,往往不是在新聞現場,而是趕往現場的路上。
每次上車前,我都會跟司機反復強調,選安全的路走!在加沙的司機都明白,安全的路指的是視野開闊、目標明顯的大路;要遠離哈馬斯建筑,因為那是以色列戰機重點“照顧”對象;要遠離人口稠密、街道狹窄的難民營,因為那里遍布著武裝分子;要遠離邊境地帶和海濱大道,因為這里暴露在以軍坦克和軍艦的炮口下。
盡管有意識地降低風險,但危險還是時刻潛伏在身邊。在我剛拍攝完已經被炸毀的哈馬斯內政部大樓后不久,以軍又開始對其反復轟炸;每次行駛在非常靠近邊境的薩拉丁大道上時,都嚇得踩死油門拼命開,祈禱著邊境上無數的以軍坦克手不要把炮彈打歪;采訪途中一有火箭彈升上天空,就得趕緊上車轉移到安全地方,因為隨后以色列戰機的反擊是不長眼睛的。
聽說我們居住的Arc Med酒店與以方有“秘密保護協議”,但因位置靠近以軍轟炸最密集的加沙北部邊境,所以轟炸聲總是從夜幕降臨一直持續到隔日清晨。每次都是一爬上床,就看到窗外突然火光四射,接著就是震得人膽顫的巨響,一股氣浪打我臉上,整個房間都跟著晃動。時不時還有爆炸產生的碎片落到酒店樓下的露臺上。這段期間,轟炸成了我最特殊的“叫早”服務,基本上每天我都是被“炸”醒的。
鏡頭下的“人間地獄”
除了人間地獄,我再也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去形容戰火中的加沙了。
巴勒斯坦平民達盧一家9口被炸死的慘劇震驚了世界。隔天我在加沙城希法醫院的停尸房遇到了達盧和他的大兒子。他們兩人因當時冒險出門為全家購買口糧,僥幸逃過一劫。在看過親人的尸體后,他們哭著走出了停尸房。我穿過人群,發現他們癱坐在門外的角落里默默流淚,我將鏡頭對準了這個讓人心碎的畫面。達盧看了我一眼,然后深深地埋下了頭。這個眼神讓我心跳不已,真不愿意因拍攝再次傷害到他們。
11月20日我去拍攝一個葬禮,遇難者是一位父親和他的兩個孩子(一個兩歲,一個4歲)。在這里,我遇到了兩名同行——哈馬斯下屬“阿克薩”電視臺的攝像記者。這兩個穿著媒體背心的大胡子走進暫時停放遺體的清真寺,與在一旁等待報道葬禮的我閑聊了兩句便分開了。我記得他們是乘坐雷諾旅行車離開的,車頂上貼著“PRESS”(媒體)的字樣。他們準備去聯合國學校,采訪逃到那里的難民,卻不想當天下午就傳來了他們的死訊。
當時在聯合國學校采訪難民的同事目睹了一切,這兩個記者的車剛開到聯合國學校門口,一架以色列戰機突然向汽車發射了一枚導彈,引發了巨大的爆炸。同事立刻跑過去,發現車里的兩人早已燒成了黑炭,司機的手還緊緊扒著方向盤。
在加沙那幾日,每天在鏡頭前發生的都是這樣的慘劇。稍有分心,就有可能因感情決堤而無法好好工作,我知道當下最重要的責任是記錄。盡管如此,在我拍攝完最后一具尸體后,胃里泛上的惡心和暈眩感,還是讓我從停尸房奪門而出。如今沖突已經結束,但那些戰爭場面依然會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
停火后持續的傷痛
在苦熬了8天后,我們終于收到哈馬斯與以色列達成停火協議的消息。當最后一陣炮擊與轟炸結束之后,加沙城陷入一片久違的沉寂。我們圍坐在電視前收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新聞發布會,當他宣布代號為“防務之柱”的軍事行動正式結束時,在場所有人都發出一陣歡呼。我和同事看到這一幕后忍不住放聲大哭,是的,不管是對巴勒斯坦人還是我們,過去的8天是一場太長太壓抑的噩夢。
當我趕到8天來發生最多慘劇的希法醫院時,看到人們在醫院門口揮舞著巴勒斯坦國旗和各種派別的旗幟,瘋狂地吶喊著勝利的口號,所有人臉上都洋溢著笑容,有的人已然熱淚盈眶。清真寺的喇叭也高聲誦起《古蘭經》,有人開始向人群拋灑糖果,仿佛今天才是真正的新年第一天。
停火的第三天,我和同事從加沙撤離。媒體大軍走了,但加沙人不能走,也走不了,未來的歲月里,這些在這次戰爭中失去親人的巴勒斯坦人,要在這片被戰火燒得遍體鱗傷的土地上,反復體味孤寂和痛楚。巴勒斯坦桂冠詩人馬哈茂德·達維什的詩歌“Passing in Passing word”中有這么幾句:所以請離開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岸邊/我們的大海/我們的麥子/我們的鹽/我們的創傷/沾染了我們的鮮血,帶著它遠離。
是的,希望有一天戰爭能遠離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