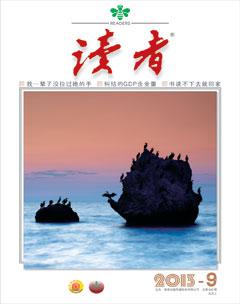迷惘的分工
岑嶸
中世紀的分工是這樣的,神父專事禱告,騎士專事殺人,農民專事供養所有人。不過這種分工并不太明確,作為公關顧問的神父如果處理不好和神的關系,他們就會把責任推給農民。當歐洲黑死病肆虐時,災禍的責任并非神父祈禱不濟,而是農民信仰不忠。那些神的公務員吃飽后站在布道壇上詛咒農民:“肉體為奴的人啊,你們該受神的懲罰。”
在1945年8月之前,裕仁天皇的分工是神,他每天坐在宮殿里扮演著天神。而在那個龐大的戰爭機器的金字塔分工體系中,有的家伙則比較倒霉,分到了人體魚雷或是自殺飛機。1945年8月,當一個叫麥克阿瑟的美國佬把锃亮的皮靴踏上日本本島以后,這個分工體系就徹底改變了,神和炮灰都成了一樣的普通人。
1944年,德國人為挽回頹勢,發明了V-2飛彈,這玩意兒可以從法國打到倫敦。當然,這條長長的V-2產業鏈要靠上萬人來分工完成。對于那個點火發射的家伙來說,他只是茫然地望著升空的飛彈,直到看不見,然后拍拍身上的灰,收工回家去喝啤酒,一切都不關他的事了。而在英國倫敦的某個地方,一幫倒霉蛋走在街上,忽然“轟”的一聲,莫名其妙被炸得粉碎。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理論,指出分工提高了效率。到上世紀初,亨利·福特就把生產一輛車分成了8772個工時。分工論成為企業管理的主要模式,也為規模化生產提供了可能。然而隨著產業鏈越來越長,分工越來越細,世界也彼此割裂,另一種迷惘從人們心底生出。
在經濟學研究上,專業分工也讓學術發展陷入迷惘。經濟學在1800年前后就達到頂峰,此后,經濟學變得更專業化了。不斷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養了大批對復雜的經濟模型和統計方法了如指掌的經濟學家,但他們對金融危機的到來一無所知。
美國經濟學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說:“自工業革命以來,我們陷入了一個陌生的新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華麗的經濟學理論無法解答普通人提出的簡單的經濟學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富有而另一些國家貧窮?”
精細的分工讓人陷入迷惘,而混亂的分工則讓人絕望。比如老舍先生,我們知道他應該搞創作,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不幸的是他分到的是當革命小將的批斗對象,于是他跳了湖。
沈從文先生是個天才,不但小說寫得好,做學問也是一流。他說:“除服裝外,綢緞史是拿下來了;家具發展史拿下來了;漆工藝發展史拿下來了;前期山水畫史拿下來了;陶瓷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扇子和燈的應用史拿下來了;金石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可惜他分到的是清掃廁所的工作,于是只能呆呆地看著天安門廣場人來人往的景象,然后回過頭對同伴說:“我去擦廁所上面的玻璃。”
當我們的分工鏈條越來越長時,也是走向自我異化的時候,我們無法明白自己到底是誰,無法體會別人的感受。于是,在遙遙不能相望的兩端,有人當神,有人當螻蟻,有人當圣人,有人當芻狗。
(冷玲玲摘自《北京青年報》2013年2月25日,劉 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