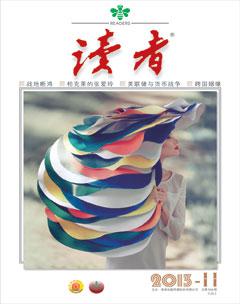用520套校服許下婚禮誓言
秦珍子

不買房子,沒有汽車,甚至也沒有特別的求婚儀式,2012年冬天,兩個因去貴州山區支教而相識的80后年輕人陳華信和吳文苑結婚了。
他們將“紅包”變成520套冬季校服,送給農村學校的孩子們。
“520套冬衣,為慶祝,也為感恩。”他們在微博上寫道。阿信附上了他創辦的支教助學公益組織的銀行賬號,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募捐的截止日期是2012年12月2日婚禮當天。
“元旦就回貴州發放我們募捐來的衣服。”文苑表示,那就是他們的蜜月之旅。
一
阿信的微博很快引來不少人認捐和轉發,這其中“七八成是親朋好友”,也有一些陌生人。
對這對新婚夫婦來說,這是最特別的儀式。
“我們彼此心有靈犀。”阿信說,當他提出要把婚禮和公益結合起來時,文苑告訴他,自己也一直這樣想。
他們的想法源于在貴州省大方縣油杉小學一段綿延5年的感情。
2007年,大二“五一”長假,新聞學專業的阿信和朋友去貴州“走訪”。他長期關注教育領域的新聞,而正好在那段時間,貴州出現了好幾個“感動全國”的教育界人物,他想親眼看看那些“新聞現場”。
在草坪鄉和星宿鄉同當地人聊天時,阿信得知,四里八鄉最窮的地方是懸崖那邊的油杉河村。
“沒有別人的指引,我根本看不出那是一所學校。”阿信回憶,當時的油杉小學,連一根旗桿都沒有,毫不起眼的3間平房是附近唯一一套磚瓦結構的房子,村民們住的還都是木屋。
即使是5月,山中下起雨來依然寒氣逼人。學校里,鄉村教師趙鵬聽說來了廣州的大學生,興奮極了,圍著火爐,嗑著瓜子,他向阿信介紹了油杉小學的情況:
一百來個學生,兩名教師,每年只能收到三分之一的學費,數學成績卻在全鄉數一數二。整座學校除了屋子和桌椅,什么都沒有。墻壁突出的部分被涂黑,當黑板用,每學期都有孩子輟學。
“有的家庭連鹽巴也吃不起,哪來的錢交學費。”趙鵬對阿信說。面對山村的貧窮,出生在廣東湛江農村的阿信坦言自己并沒有什么傷感憐憫,而是“直面它的存在”。但同時他也覺得,自己得做點什么。
這年暑假,阿信在校園網上招募了4名志愿者,來到油杉小學支教。同年10月,他創立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學公益組織。又過了半年多,社團招新,阿信和文苑相遇并相愛了。
二
第一次支教的經歷讓文苑這個在城市里長大的獨生女吃足了苦頭。她第一次坐了20多個小時的硬座車;第一次和同學裹著潮濕發霉的棉被,擠在課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而這珍貴的“洗澡水”則讓她和幾個女孩身上長滿了奇癢難忍的皮疹。
文苑并不認為這樣的生活是吃苦。在她眼中,油杉河村的人們雖然貧窮,但他們的生活并不顯得苦悶。外人來到村里,會受到熱情的款待,說起未來,他們也總是非常樂觀。
在她家訪的過程中,一個三年級的小女孩不斷地要求“老師抱抱”“老師和我說說話”。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愛是任何方式都無法再彌補的。”這是文苑最為揪心之處。
當她結束家訪離開時,女孩在山上大聲喊著:“老師,一定要回來啊!”
阿信對他的團隊管理得非常嚴苛。從備課、上課到家訪、交談,每一個和孩子有關的環節阿信都要求志愿者們力求完美。他同時會注意到當地的“禮儀風俗”,在觀念比較傳統的老鄉面前,志愿者“大大咧咧”的行為會被隊長嚴肅批評。
“那里見證了我們的感情,也讓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20歲的文苑對著大山暗自許下諾言,如果將來真的能嫁給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當時已經是阿信第三次去油杉河村。此后,他又回去過4次,有時哪怕只待一兩天,只夠教孩子們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農家樂,不是游樂場,也不是讓你體驗的地方。”阿信嚴肅地回憶著自己的支教經歷。作為隊長,遇到以美化簡歷或滿足好奇心為目的的報名者,他總是直接刷掉。在他看來,“打游擊”式的所謂支教,走了不知何時再來,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會對孩子們的心靈造成傷害。
有段時間,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的認可,也找不到體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所有年輕人一樣”。然而,文苑始終和他站在一條戰線,從未抱怨或要求過什么。
5年下來,阿信收到的學生來信足足攢滿了一大箱。
“在那里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強烈。”阿信說,那種滿足感是都市無法給予他的。
三
2012年11月2日,這對情侶登記結婚。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時,他們商量著,可以用紅包購買冬季校服,作為新年禮物,讓孩子們的小手不會被凍傷,也不用再背著煤去上學。
新婚第二天,阿信和文苑就回到了油杉河村。阿信想在那里拍攝結婚照,給孩子們發喜糖。站在山頭的老樹下,文苑穿著潔白的婚紗,她的心里感受到“意義非凡的熱烈”。
這對新人并沒有想到,在結束拍攝回到學校后,他們得到了“高規格”的迎接。學生家長們自發操辦了婚慶的酒席。
女人鉆進廚房,切菜燉雞,男人端起白酒,點起鞭炮。教室里的課桌被臨時“征用”,在場院里拼成4張大桌。全村來了100多人,從下午5點到晚上8點,足足吃了4輪流水席。當霧氣散去,夜晚來臨,他們在山谷里燃放起煙花。所有人都仰頭看著那穿透黑暗的光彩,一個孩子寫紙條給阿信:“你們來了我很高興,煙花真美。”
像所有傳統婚禮上的新人一樣,新婚夫婦穿著紅衣服,挨桌敬酒。一位大叔把紅包塞進阿信手里,阿信執意拒絕。看著大叔“黑著臉”走掉,阿信趕緊召集老鄉“開會”,說12年是一個輪回,紅包就包12塊錢。有些家長來了并不吃飯,把紅包放下就走。臨走前,阿信和文苑總共收到3456元。
阿信把錢悄悄壓在趙鵬老師的枕頭下,帶文苑返回廣東。然而很快,他接到了趙老師滿腔不樂意的電話,“我們之間已經不用談錢,這是大家的心意,把你的銀行賬號發過來。”
阿信無法推辭了,但他已經想好了應對的辦法——把鄉親們的紅包用來給孩子們購買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獨行、不善交際”的阿信覺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了這件事情”,而且會繼續做下去。而在文苑看來,公益正是他們共同的追求。這個女孩覺得,跟著阿信去支教的經歷讓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理所當然”,應該倍加珍惜。
在香港讀研和實習時,文苑曾穿過國際名牌,卻“并不向往”。她甚至沒有把“甜蜜校服計劃”告訴同事,因為“小小的虛榮心”已經在貴州大山里的那場婚宴上得到了滿足。
在離開之前,文苑又一次站在了講臺上。這個還沉浸在新婚喜悅中的新娘子,把手語“我喜歡你”教給孩子們,她希望他們抱著“有愛”的心態,堅強勇敢地面對未來。
趙鵬老師的妻子張梅回憶起初次見到阿信的樣子,“瘦瘦的,背著一個大包”。那時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這個大學生來山溝里做什么。“走的時候他說他會回來,”張梅說,“我們誰都不相信。”
(趙紅星摘自《時代郵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