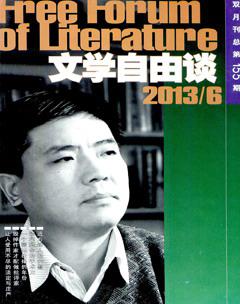對(duì)蔣子龍們的遺憾
徐兆淮
這天,我隨意翻閱剛寄來(lái)的《炎黃春秋》,忽然映入眼簾的兩個(gè)人名字:戴煌與顧準(zhǔn),立刻引起了我的閱讀興趣。及至急匆匆地讀過(guò)《我反對(duì)神化與特權(quán)》(戴煌)和《<顧準(zhǔn)文集>出版的曲折》(盧惠龍),頓時(shí)便在我心扉升騰起一股遺憾之情,并久久縈繞于腦際,揮之不去。它不僅勾起了我對(duì)戴煌與顧準(zhǔn)的記憶片段,還由此引發(fā)了我在三十年編輯生涯和七十多年人生長(zhǎng)河里的諸多慨嘆與遺憾。
在河南息縣“五七”干校里,在駐馬店軍營(yíng)的修整中,也許我與顧準(zhǔn)都曾有過(guò)共同的經(jīng)歷與痛苦的思索。1973年至1974年從干校回到北京學(xué)部大院,我住在六號(hào)樓,他住在八號(hào)樓,同為單身光棍,也許我與顧準(zhǔn)也曾有過(guò)見(jiàn)面不相識(shí)的機(jī)遇。當(dāng)這位有著革命經(jīng)歷的老干部,這位有著獨(dú)立思想的學(xué)者和思想家形單影只、獨(dú)處斗室地思索中國(guó)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尋求探索救國(guó)之路而孜孜不倦地寫(xiě)下那些絕命之作時(shí),年過(guò)三十、一事無(wú)成的我在干什么呢?我卻在為調(diào)離學(xué)部返回南京作準(zhǔn)備,經(jīng)常冒著嚴(yán)寒酷暑,關(guān)在大院六號(hào)樓一間鐵門辦公室內(nèi),打著方桌碗柜,忙著為自己將來(lái)的小日子作準(zhǔn)備,全然不知學(xué)部大院八號(hào)樓內(nèi),還有一個(gè)憂國(guó)憂民的學(xué)者,正在寫(xiě)著關(guān)乎國(guó)家命運(yùn)的專著。而他的病逝于1974年11月,恰恰也正是我調(diào)離北京,返回南京之際。
就這樣,我與顧準(zhǔn)同處在北京建內(nèi)一個(gè)學(xué)部大院內(nèi),同置身于偏僻鄉(xiāng)村一個(gè)“五七”干校里,在他生前,我卻一直與他擦身而過(guò)無(wú)緣相識(shí),更未及說(shuō)上一兩句話。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讀到他的書(shū),了解他生前的環(huán)境和死后的價(jià)值。如今,當(dāng)我讀著《<顧準(zhǔn)文集>出版的前后》和《顧準(zhǔn)尋思錄》,得知顧準(zhǔn)學(xué)說(shuō)、思想在學(xué)術(shù)界的巨大影響,尤其是得知我們?cè)幱趯W(xué)部大院困厄時(shí)期,而我竟與他失之交臂,我不禁遺憾之至。我不由得責(zé)怪自己的愚鈍與麻木。
而與此遺憾頗為相似的,還有作為文學(xué)編輯,我竟雖與大學(xué)者錢鐘書(shū)曾有十年同在文學(xué)所,同去干校走過(guò)兩三年“五七”道路的機(jī)緣,可待到我1974年調(diào)離北京,回寧從事《鐘山》編輯工作多年,竟然一再錯(cuò)過(guò)去北京拜望錢先生的機(jī)會(huì),以至直到錢離開(kāi)人世時(shí),我方才為自己的粗疏,引為深深的遺憾。我后悔不該因?yàn)殄X主要從事外國(guó)文學(xué)和古代文學(xué)研究,我編的是當(dāng)代文學(xué)期刊,而從未主動(dòng)拜訪、請(qǐng)教錢老先生,為他家鄉(xiāng)刊物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和幫助。作為一名文學(xué)老編輯,這實(shí)在是不容閃爍的過(guò)錯(cuò)。即使后來(lái)我寫(xiě)了幾篇憶念錢先生的短文,卻也彌補(bǔ)不了我內(nèi)心的遺憾。
我與戴煌相遇及文稿交往,又呈現(xiàn)出另一番情景。我與戴煌先生初次相見(jiàn),大約是在上世紀(jì)九十年代中期,南京新街口新華社江蘇分社的招待所里。那時(shí),我正在《鐘山》主持日常工作,我有意于適當(dāng)加強(qiáng)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辦刊思路,正想尋找組織這方面的作者與作品。此時(shí)適逢前幾年曾經(jīng)為《鐘山》“雜文作坊”專欄寫(xiě)稿的邵燕祥先生得知此事,遂主動(dòng)向我推薦了戴煌先生。那次拜訪的時(shí)間不長(zhǎng),這位江蘇老鄉(xiāng)卻給我留下了一定印象。出現(xiàn)于我眼前的,是一位個(gè)子略高,談吐和藹,口語(yǔ)里充滿蘇北鹽阜一帶口音的長(zhǎng)者。交談中我方得知,他是蘇北鹽城人,早在青年時(shí)期即投身革命,解放后曾擔(dān)任新華社高級(jí)記者,陪同胡志明主席采訪越南戰(zhàn)場(chǎng)。可是,因?yàn)闉槿苏泵舾校矣诼收姹磉_(dá)個(gè)人意見(jiàn),終于難逃1957年反右那場(chǎng)災(zāi)難。
在我的初訪印象里,戴煌先生乃是一個(gè)為人正直、平生迭遭磨難,卻又不改其志的值得尊敬的老人。回京之后,他即寄來(lái)一篇紀(jì)實(shí)文體的稿件,閱后我卻陷入犯難尷尬的境地:作品的文體與刊物的宗旨距離稍大,作品基本仍屬通訊報(bào)道紀(jì)實(shí)類稿件,與《鐘山》一向注重文學(xué)本體的要求不太吻合。最后幾經(jīng)斟酌,我終于忍痛退稿了。為此事,直到退休之后,我仍有不安,時(shí)常牽掛于心。尤其是,近幾年來(lái),我從《炎黃春秋》上,讀到他的那本自傳體著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經(jīng)歷》之后,我更不免有些為自己在編輯工作中處置不當(dāng),而時(shí)常感到不安和后悔。我的書(shū)生氣和膽識(shí),終于讓我嘗到了作為編輯無(wú)法挽回的遺憾。
從顧準(zhǔn)和戴煌這兩人兩事的遺憾延伸下去,我又不由得想起我的人生機(jī)遇,尤其是三十年編輯生涯中,所碰到的另外幾件遺憾之事。那大都是我從事編輯工作中,或有過(guò)多次接觸,或只知其名并不認(rèn)識(shí),卻接觸過(guò)作品,最終都與這些作家與作品失之交臂的往事。作為一個(gè)退休多年的老編輯,如今每每看到他們的名字或是讀到與他們有關(guān)的信息,便不由引起我從內(nèi)心泛起陣陣的遺憾之情,發(fā)出幾聲唏噓慨嘆。他們便是路翎、蔣子龍,還有上海女作家戴厚英。
觀之中國(guó)的文學(xué)期刊或報(bào)刊傳媒,主編和編輯或因政治犯忌,或限于水平膽識(shí)大約總難免會(huì)留下諸多的遺憾與尷尬。在我的三十年的編輯生涯中,自然也不例外。早些年,我曾寫(xiě)過(guò)一篇題為《主編之難與主編之惑》,敘述了我在編輯工作中所經(jīng)歷的幾種困惑與難題。現(xiàn)在要談及編輯及人生歷程中的某些遺憾之事,當(dāng)然也不只是顧準(zhǔn)與戴煌兩人了。此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與這三位作家及作品交往中的幾件憾事。那便是天津作家路翎、蔣子龍給《鐘山》來(lái)稿未采用之事,與上海女作家戴厚英未能兌現(xiàn)的稿約。
早在讀中學(xué)時(shí),我即知道,路翎是胡風(fēng)“反革命集團(tuán)”的重要骨干分子,是胡風(fēng)集團(tuán)中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代表作家。讀大學(xué)時(shí)又讀過(guò)他的代表作《洼地上的戰(zhàn)役》,其人可算是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有影響的作家之一。總之,“文革”前,對(duì)胡風(fēng)及其成員是不可能有正面評(píng)價(jià)的。“文革”后,胡風(fēng)冤案獲得平反,胡風(fēng)及其骨干成員大都年老體衰,很少再有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熱情和能力了。卻沒(méi)想到,大約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后期,胡風(fēng)集團(tuán)案件平反之后,編輯部忽然收到一件來(lái)自天津的頗為異常的稿件,打開(kāi)一看,竟然是署名路翎的一篇中篇小說(shuō)!作為從五六十年代走過(guò)來(lái)的中年編輯,我自然知道一些關(guān)于胡風(fēng)案件的平反情況,也久聞路翎之大名,遂滿懷興致地閱讀來(lái)稿,誰(shuí)知稿件字跡十分潦草歪斜,實(shí)在無(wú)法卒讀。無(wú)奈之下,我只好寫(xiě)了一封回信,將稿件寄回,并囑他請(qǐng)人代抄謄清后再寄來(lái)。不料此信稿就此石沉大海,再無(wú)回音。當(dāng)時(shí),倒也未曾十分在意,如今退休多年之后,我卻不時(shí)憶起此事,頗以為憾:當(dāng)時(shí)我為何不能采取更為妥當(dāng)?shù)霓k法閱處此稿呢?后來(lái),我曾聽(tīng)說(shuō),胡風(fēng)一案平反之后,路翎這位南京籍作家,早已是傷痕累累,精神也有些錯(cuò)亂了,然而,他卻忘不了為家鄉(xiāng)的刊物寫(xiě)稿,而我卻處理得如此草率,以致終于失去了與他及其作品面見(jiàn)的最后機(jī)遇。退休之后,每念及此事,作為一名老編輯,我不能不感到后悔和遺憾。
與失之交臂的路翎相比,我與另一位天津作家蔣子龍的交往、約稿,則又呈現(xiàn)出另一番情景。作為與新時(shí)期文學(xué)同步成長(zhǎng)的作家與期刊,《鐘山》與蔣子龍本是有許多合作的機(jī)遇與空間的。事實(shí)上。1980年前后,當(dāng)蔣子龍以《喬廠長(zhǎng)上任記》和《拜年》等中短篇小說(shuō)開(kāi)創(chuàng)了“改革文學(xué)”的新局面之后,我即把組稿方向移向了京津一些創(chuàng)作力活躍的作家。大約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期,我曾不止一次地赴京津組稿,并特地去天津拜訪過(guò)蔣子龍,其后,還與他有過(guò)多次書(shū)信往來(lái)。至今我手頭還保存著蔣子龍的幾封來(lái)信。然而,不知是因?yàn)闄C(jī)緣不合,還是我用力不勤,蔣子龍終于未能在《鐘山》發(fā)過(guò)一次作品。
事實(shí)上,大約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末期,經(jīng)我多次約稿,蔣子龍?jiān)慕o我一篇紀(jì)實(shí)體作品,所寫(xiě)的主人公乃是廣東特區(qū)的一位頗有爭(zhēng)議的市級(jí)領(lǐng)導(dǎo)干部。最終,又因編輯部?jī)?nèi)部的不同意見(jiàn),加之當(dāng)時(shí)正處于敏感時(shí)期,尤其是中央有關(guān)方面曾有過(guò)規(guī)定,有爭(zhēng)議的在任領(lǐng)導(dǎo)干部,需報(bào)上級(jí)有關(guān)方面審批,我斟酌再三,只好忍痛割愛(ài)退給蔣子龍了。我知道,對(duì)于像蔣子龍這樣級(jí)別的走紅作家,組稿多年始得一稿,如今卻又這樣退稿,其時(shí),作為責(zé)編的無(wú)奈與遺憾,也就可想而知了。記得寫(xiě)退稿信時(shí),筆端是那么沉重和為難,因?yàn)橹挥形抑溃以僖矡o(wú)顏向子龍約稿了,《鐘山》與子龍的“稿緣”也便到此結(jié)束了。
說(shuō)起編輯的遺憾,我又不由自主地憶起了與上海女作家戴厚英的約稿、交往經(jīng)歷。大約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自從戴厚英的《詩(shī)人之死》與《人啊,人》引起文壇的關(guān)注與熱議之后,我即主動(dòng)熱情地向戴約稿。先是在家鄉(xiāng)鎮(zhèn)江的一次紀(jì)念同鄉(xiāng)詩(shī)人聞捷的會(huì)上與戴見(jiàn)了面,接著又特地去上海巨鹿路市作協(xié)大院內(nèi)的一間平房?jī)?nèi)拜訪了戴,并熱情邀請(qǐng)她來(lái)南京做客。之后不久,我與《鐘山》主編劉坪先生特地安排她在雙樓門附近一家旅社內(nèi)食宿,并陪她游覽南京景觀。在寧期間,編輯部與她相處交談甚是融洽,離寧前她已應(yīng)允回滬后即著手為《鐘山》寫(xiě)稿。不料想天有不測(cè)風(fēng)云,她回滬不久即傳出她在家遇刺身亡的消息。這不啻是對(duì)戴厚英親友的沉重一擊,當(dāng)然對(duì)文壇和《鐘山》也帶來(lái)不小的傷痛和遺憾。為此,我曾經(jīng)寫(xiě)過(guò)一篇《無(wú)法兌現(xiàn)的稿約》來(lái)表達(dá)對(duì)她的紀(jì)念。
與以上作家約稿多年終未能在《鐘山》發(fā)稿的遺憾不同,還有幾位曾與《鐘山》相識(shí)較早且合作多年,也在刊物上發(fā)過(guò)不少作品的作家,后來(lái)卻因特殊原因,為一部待發(fā)稿件的閱處結(jié)果,也會(huì)招致作家或編輯的不快或遺憾。那是我主持《鐘山》工作期間,與賈平凹和張煒為一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的處理而引起的。
賈平凹與張煒都是新時(shí)期文學(xué)歷程中代表性的作家,也是與《鐘山》合作多年的重要作者。賈曾在《鐘山》發(fā)表過(guò)《九葉樹(shù)》、《商州初錄》等中短篇小說(shuō)和散文,張煒則在《鐘山》先后發(fā)表過(guò)《海邊的風(fēng)》等中短篇小說(shuō)和散文。我主持《鐘山》編輯工作期間,還曾分別到西安和濟(jì)南去拜訪、組約他們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事實(shí)上,他們倆也曾應(yīng)允過(guò)為刊物寫(xiě)長(zhǎng)篇小說(shuō)。大約在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末,一次全國(guó)作代會(huì)上,我去組稿時(shí),賈平凹曾提議將他被刪削壓縮后發(fā)在《收獲》上的一部長(zhǎng)篇重新修訂后,再交《鐘山》發(fā)表,后又來(lái)信說(shuō)及若重新刊發(fā),他可考慮少收或不收稿費(fèi)。而張煒想給《鐘山》的長(zhǎng)篇也是因在《收獲》擱置時(shí)間太長(zhǎng),他遂想收回給《鐘山》發(fā)表。我與張還商定發(fā)表刊期。
但《鐘山》與賈平凹、張煒的長(zhǎng)篇合作計(jì)劃,卻最終未能兌現(xiàn)成行。與平凹的合作因編輯部?jī)?nèi)意見(jiàn)不一,而只能婉謝作罷。與張煒的合作則因《收獲》不愿放棄,搶先發(fā)表的想法只能停擺。雖然這兩次的合作愿望未能如愿兌現(xiàn),雖然,這兩位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尤其是新時(shí)期的文學(xué)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仍然保持著與《鐘山》的友好合作關(guān)系,但作為策劃此事的編輯,我仍然十分惋惜,長(zhǎng)此耿耿于心。即使是退休多年,每念及此,我依然不免會(huì)引以為憾,不勝唏噓的。
說(shuō)罷三十年編輯生涯中的諸多遺憾之事,我不由又想起七十多年人生中的一些憾事。依照我七十多年的人生體驗(yàn),我以為,不管是權(quán)貴富有者,還是草根百姓,但凡人生一世,總會(huì)有歡樂(lè),亦有悲喜,有得意之時(shí),亦有遺憾之事。且遺憾還有片刻些微的小遺憾,與終生難忘的大遺憾之別;有可以挽回的遺憾,也有難以挽回的遺憾。盡管,不同職業(yè)不同文化層次的人,其對(duì)遺憾的理解與表達(dá)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消除和避免難以挽回的大遺憾,仍然是人們的共同的愿望。對(duì)于七老八十的老人而言,尤其如此。
在我看來(lái),如果說(shuō)遺憾本是在大的時(shí)代背景下,個(gè)人的一點(diǎn)小小的不稱心,淡淡的不滿意,那么,作為編輯的遺憾,不過(guò)是我在幾十年編輯生涯中,發(fā)生的某種不太稱心滿意的人和事。對(duì)我而言,在已經(jīng)逝去的幾十年編輯工作中,雖然發(fā)生過(guò)與同事的齟齬或不愉快,我都可以不糾結(jié)于心,不予計(jì)較,但在與作家的交往、組稿過(guò)程中,一旦發(fā)生與作家的不快不滿之事,甚至影響到稿件的組約,弄丟了原本可以得到的稿件,那便是我最大的失職最大的遺憾。雖然,這遺憾對(duì)期刊而言,也許并未帶來(lái)多大的損失,也不完全是我個(gè)人的過(guò)失,但那卻是永遠(yuǎn)難以挽回的機(jī)遇,永遠(yuǎn)找不回來(lái)的缺憾。
也許,每一種人生,每一種職業(yè),都會(huì)留下一些讓人難以忘懷的遺憾。也許,在我剩下的余生里,我總也忘不掉發(fā)生在幾十年前的這些讓我不太稱心滿意的遺憾,但我愿意與此遺憾為伴,走完剩下的日子,既是為了釋?xiě)眩彩菫榱思o(jì)念。當(dāng)然,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機(jī)遇里,對(duì)親友對(duì)工作,我尚另有諸多的遺憾,但比之以上編輯的遺憾,我以為都是不足介懷,不必記載的。人生如白駒過(guò)隙又如飄逝的白云,在人生大幕即將關(guān)閉之際,我愿留下一些沉思,也愿記下這些遺憾,既為自己,也為期刊與時(shí)代留下一些印痕。哪怕是淺淺的、淡淡的也好。這不是虛妄,也不是自夸,而只是一個(gè)老編輯的心語(yǔ)。如此而已,豈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