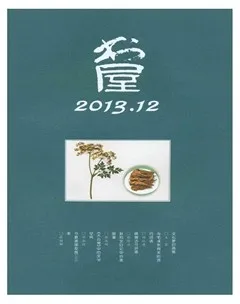趙烈文日記中的曾國藩
趙烈文是曾國藩的心腹幕僚和無話不談的弟子。他有一部《能靜居日記》,記錄了當時大量重要人物與著名歷史事件,內容關涉湘軍、太平軍以及清廷的諸多方面,尤其對曾國藩與清廷的矛盾,南京失陷時清軍燒殺擄掠之暴行,以及李秀成被俘等事實記敘頗詳,是研究太平天國和晚清歷史的極好材料。
另外,這本日記還記錄了曾與趙的大量談話,不僅內容包羅萬象、完整詳實,而且談話時兩人的一顰一笑都活靈活現地記了下來。通過他們的交談,我們可以認識和了解一個完整而又真實的曾國藩。
既為時局擔憂,又感到無能為力、悲觀失望
同治六年六月八日天黑不久,曾國藩來找趙烈文聊天,見有客人,就回去了。過了一會兒,又來久談。曾國藩說:因為捻軍竄到河南東部,未能堵截防御,昨天皇上發下措詞嚴厲的諭旨,對統兵的各位將領予以訓斥。沅弟(曾國荃)被摘去頂戴,與河南巡撫李鶴年一同交部議處。李鴻章戴罪立功。諭旨中還有這樣的話:“各疆吏于捻賊入境,則不能堵御,去則全無攔遏,殊堪痛恨!李某(李鴻章)剿賊,已屆半年,所辦何事?!”語氣非常嚴厲,是近來所沒有的。曾國藩為此擔心:李鴻章和曾國荃的胸襟和涵養還欠磨練,萬一焦躁憤慨起來,以致發生意外,則國家的局面更難預料。大局成這個樣子,決不允許再有什么差錯發生,否則,“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顧精力頹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為愈耳”。曾國藩說這話的時候,神氣凄涼,趙烈文一時竟找不到恰當的話語安慰。
八月六日下午,曾國藩又來和趙烈文久談。當說到捻軍進了山東境內,形勢越來越嚴峻,負責剿捻的李鴻章受到朝廷指責,剿捻的任務可能會再次落到曾國藩頭上時,趙烈文說:要徹底剿滅捻軍,必須把建立騎兵部隊作為優先考慮的事情,因此建議曾在江南開辟一處牧場馴養軍馬,另外在閑田多的地方大力開展屯墾,解決部隊的糧草供應問題。曾國藩聽了,雖然為之動容良久,卻無可奈何地說:“吾老且死,奚暇計久遠,足下休矣!”
感嘆國家選拔的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曾國藩到趙烈文處閑談,說到今天有個四川籍的翰林院庶吉士來見他,言談舉止根本不像一個士大夫;前天也有一個湖南籍的庶吉士送詩給他看,但排律不成排律,古體詩不像古體詩,國家選拔的人才居然是這個樣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文章與國運相關,天下事可知矣!”當時久旱無雨,曾國藩憂心忡忡,導致牙根上火。因牙痛得十分厲害,所以跟趙烈文閑談時,曾國藩常常捂著嘴巴,發出痛苦地呻吟,結果小坐一會就離去了。
九月十四日下午,曾國藩和趙烈文閑談時,再次說到科舉選拔人才:這次在貢院鈐榜時,與上江(安徽)朱學臺(負責一省教育事業的提督學政)挨著坐,朱學臺對考生的文章也不滿意,兩個考官的舉止尤其粗俗。朱學臺于是拉著曾國藩的手,在他掌上寫了一個“酸”字,曾國藩看后,會意地笑了笑。曾國藩又說:今年錄取的這些舉人,比甲子科(同治三年)錄取的差遠了。同治三年即1864年,這一年太平天國失敗,兩江總督曾國藩立即在轄境內恢復已經中斷十多年的鄉試,因此把這一年的考試稱為甲子科。
曾國藩言猶未盡,又說道:我駐軍祁門縣時,祁門城位于山腳下,形勢局促,不開闊,很難守衛。我于是對人說,這樣的城,又有什么用?不如毀掉它!城里有人知道了這件事,寫來一信說:大清朝初年,我們祁門曾經有人中過舉,康熙年間一位江西籍的官員來這里當縣令后,選定這個地方做縣城,到現在一百好幾十年了,再沒有考中一個舉人,您如果決定拆毀城墻,百姓沒有不樂意聽從的。我于是下令拆毀城墻,建造了不少碉樓,用來防御太平軍的進攻。工程竣工后,有人請我寫一段城邑記之類的文字,我在上面批了四句話:“拆去西北城,歲歲出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說來奇怪,自我做了這個批示后,甲子科鄉試,祁門考中了三個舉人,今年這一科又考中了兩人。曾國藩因此很有感觸地說:看來風水先生的有些話,是有它的根據和道理的。趙烈文于是和曾國藩開玩笑說:您有關拆城墻建碉樓這段佳話,應該刻一塊石碑,埋到祁門,數百年之后,便完全可以和諸葛碑相媲美了!曾國藩狂笑而去。
人才必須合理使用,有胸襟的人才能取得成功
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曾國藩又來和趙烈文聊天。此次談話內容非常廣泛,論完兵事,又說人才。曾國藩說:“世言儲才,不知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儲之,第一等人可遇而不可求。李少荃(李鴻章)等才則甚好,然實處多而虛處少,講求只在形跡。如元浦(曾國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歸功于己。余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今漸悟矣。”于是繼續發揮說:“人生無論讀書做事,皆仗胸襟。”趙烈文表示完全贊同。但當趙烈文建議曾把自己的文章拿出來,早日刻印成書,否則“千載以形跡相求,失公之神矣”,曾卻謙虛地說自己沒有什么值得留給后人的東西。
八月二十八日午后,曾國藩和趙烈文談話時,縱論宋、明時期人物。當說到王船山即使取得高位也未必能治國安民時,曾進一步發揮說:“世人聰明才力,不甚相懸,此暗則彼明,此長則彼短,在用人者審量其宜而已。山不能為大匠別生奇木,天亦不能為賢主更出異人……”曾話未說完,趙烈文馬上舉手打斷說:“大哉宰相之言!”曾掩面大笑說:“足下奈何掩人不備如此!”說完又鼓起掌來。正鼓掌時,有人送了一張紙條進來,曾看過后,點頭表示同意,然后故作神秘地對趙烈文說:“此何物?足下猜之。”趙烈文說他猜不到。曾說:“此吾之食單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為豐,然必定之隔宿。”趙烈文對曾的儉樸美德稱贊了一番,然后說:“在師署中久,未見常饌中有雞鶩(鴨),亦食火腿否?”曾回答說:“無之。往時人送皆不受,今成風氣,久不見人饋送矣。即紹酒亦每斤零沽。”趙說:“大清二百年,不可無此總督衙門!”曾說:“君他日撰吾墓銘,皆作料也。”說完,兩人在大笑中結束了這天的談話。
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
同治六年六月十六日午后,曾國藩邀趙烈文到內室談話,遍論咸豐末年清軍致敗的原因和諸位將帥的缺失后,曾說:回想周騰虎剛到我軍中時,曾對我說,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他又說:我普遍觀察了長江下游的統兵將領,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料定他們最終都會失敗。曾公您目前雖然兵微將寡,但最后能成就大業的人一定是您。曾國藩于是深有感觸地說:“余時深佩其‘用心’一語。其論世超出尋常者甚多,不可謂非異才。”周騰虎是趙烈文的姐夫和推薦人,當時正是有了他的推薦,曾才下決心從江西派人并帶著二百兩白銀,千里迢迢趕到江蘇陽湖,聘請趙烈文加入自己的幕府。如今周騰虎已去世六年,家眷全靠趙烈文照顧和接濟,曾舊事重提,自然會引起趙的傷感,于是話未說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住處。然而還沒有坐下,曾就跟過來與趙久談,至于談了什么,趙沒有詳記,估計是一些安慰開導的話語。
官場交情離合,有在情理,有不在情理
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趙烈文到曾國藩處閑談,問起郭嵩燾和毛鴻賓為何鬧矛盾的事。曾國藩說:毛鴻賓早年在京城時,看到郭嵩燾的文章很有文采,就想與他結交,后來毛出任湖南巡撫,又屢次請他做幕友;等到毛鴻賓擔任兩廣總督,就保舉郭做廣東巡撫。毛的能力平平,郭到任后,毛卻以恩人自居,兩人又彼此爭權,不和就這樣產生了。左孟星、王闿運、管才叔三大名士到廣東后,互相標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燾本質上是個文人,這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燾。左孟星甚至寫信詆毀毛鴻賓,說他“不齒于人類”。他們兩人最后鬧成這個樣子,平心而論是郭對不住毛,毛鴻賓沒有什么過錯。曾國藩接著說:因為我曾經保舉過毛鴻賓,郭嵩燾后來連我也怨怪上了,說“曾某保人甚多,惟錯保一毛季云”。我反唇相譏說:“毛季云保人亦不少,而惟錯保一郭蕓仙。”聽到這話的人,無不捧腹大笑。趙烈文于是說了幾句郭嵩燾不該這樣做的話。
此時有客人來,趙烈文只好告辭出來。不一會兒曾國藩跟過來了,接著剛才的話題說:“交情離合,有在情理,有不在情理。劉霞仙(劉蓉)之與朱石翹(朱孫貽),不啻子弟之于(與)父兄,而卒大番至刊詩相詬厲;蕓仙之于(與)毛季云,又少次;沈幼丹(沈葆楨)與余亦大番,然余數函修好而不答;李次青(李元度)一番之后,至克復金陵,余曾疏言其功,彼近時常通書問,庶幾復合;至左(左宗棠)則終不可向邇(靠近、接近)矣。”
七月五日午后,曾國藩到趙烈文處閑談,再次說到郭嵩燾和毛鴻賓的事。趙烈文說:郭嵩燾在廣東名聲狼藉,有人給湖南巡撫駱秉章寫信說:故鄉的高官大吏都好像豺狼虎豹一樣。民間又流傳這樣的諺語:“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燾);地皮刮盡,但余澗溪沼沚之毛(毛鴻賓)。”怎么會敗壞到這種地步!曾國藩說:這些壞名聲都是他們自取的。比如勸富人捐款捐物,贊助軍餉,是不得已而為之,本來就應該靠自愿,不能強迫;只有對那些為富不仁和向來有劣跡的人,才能采取強制措施。郭嵩燾在廣東卻不加區別,一概強制執行,所作所為,無不任意而為,怎么不遭反對和非議!郭卻悍然不顧,真沒想到他會荒謬到這種地步!
能做事的人都有脾氣,但不能由著性子來
曾國藩和趙烈文談話時,經常臧否古今人物。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下午,曾來和趙聊天,看到他還躺在床上,就站帳外等候;趙烈文發現后,急忙起來陪他坐下。這天兩人談話很久,涉及劉長佑、官文、胡林翼、左宗棠、李瀚章、李鴻章、吳棠、沈葆楨等眾多名人。曾國藩說:“劉印渠極長厚謙下,故做直督數年甚穩,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為保位之計。官秀峰城府甚深,當胡文忠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無險诐,外間傳言胡死后,官封提其案卷,則又言之過甚。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小荃血性不如弟而深穩過之,吳仲宣殊憒憒,沈幼丹自三年以前爭餉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狹……”
六月十七日,曾和趙談話時,再次歷數幾位部屬的優缺點:“沅浦(曾國荃)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余里內之人,事體安得不糟,見聞安得不陋!”接著又說:“李少荃(李鴻章)血性固有,而氣性也復甚大,與沅浦不相上下。李小荃(李瀚章)亦有脾氣,楊厚庵(楊載福)尤甚,彭雪芹(彭玉麟)外觀雖狠,而其實則好說話,遍受厚庵、少荃、沅浦之氣。”趙烈文說:“做事人總有脾氣,不然也做不成。”曾國藩說:“甚是!”
八月二十五日,曾國藩和趙烈文閑談時,再次說到自己的心愛弟子李鴻章:“李少荃在東流、安慶時,足下常與共事,不意數年間一闊至此。”趙烈文說:“烈(同治)元年冬到滬(上海),少帥猶未即真蘇撫,邀烈坐坑(炕),固問老師處有人議鴻章者否?意甚顓顓。不一月實授,從此隆隆直上,幾與師雙峰對峙矣。”曾國藩說:“湘、淮兩軍之始末區奧,足下殆無不洞若觀掌矣!”說完含笑而去。
對自己的耐性和倔強十分欣賞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到趙烈文處久坐。當說到李鴻章剿捻遇到麻煩時,曾說李性子急,遇事缺乏耐性,軍事成敗是常有的事,如果朝廷要求他盡快取得成效,或者言官對他抨擊一通,他一定不能忍受。說著說著,曾國藩情不自禁地自我表揚起來:“余自乙丑年(同治四年)起,凡七次被參,總以不變不動處之,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
對于自己的耐性和倔強,曾國藩確實十分欣賞。同年八月二十八日,當趙烈文談到李鴻章“事機不順,未必能如師宏忍”時,曾國藩立即不無得意地說:“吾謚法為‘文韌公’,此邵位西(邵懿辰)之言,足下知之乎?”
有一股誓不服輸的勁頭
曾國藩不僅性格倔強,做事有耐性,而且有一股誓不服輸的勁頭。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曾與趙烈文閑談時說:我最初在京城做官時,與許多名士有交往。當時,梅曾亮(字伯言,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因為擅長寫古文,何紹基(字子貞,清代著名書法家,尤長草書)因為擅長書法,在士大夫中間享有盛名。我經常觀摩他們的作品,覺得自己不比他們差多少,心想只要多讀書,勤努力,以后或許也能達到他們那樣的水平。但是沒過多長時間,我的學問沒有做成,官卻越做越大,每天與公務文書打交道,只能把讀書做學問的愿望和志向壓在心里。咸豐以后,我奉命討伐太平軍,戎馬倥傯,更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拿書本。如今再讀梅曾亮的文章,發現確有過人之處,說明自己當時的一些想法,還是意氣的成分居多。不過到現在我還是堅持認為:只要能夠給我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對梅曾亮、何紹基這些人,還是不甘拜下風的。曾國藩一停嘴,趙烈文就鼓掌大笑說:每個人的想法,真是難以說清!有的人做了皇帝,卻喜好臣下的稱號,于是漢朝有自稱為富平侯(漢成帝劉驁沉溺聲色犬馬之中,常常假借富平侯張放的名義在長安城內外玩樂)、明朝有自稱為鎮國公(明武宗朱厚照在佞臣江彬的慫恿下,自封為“鎮國公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到邊地宣府親征,回去后又給自己加封太師)的皇帝;老師的事業超越千古,唐、宋以下幾乎無人能比,卻遺憾自己的文章和書法技不如人,老想跟他們一比高低!不過從老師這番話語里,我也真切感覺到您的志向歷來不凡,有一股誓不服輸的勁頭,這可能正是您能夠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最終戰勝太平天國的原因吧!曾國藩說:“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為團練大臣,借居撫署,欲誅梗令數卒,全軍鼓噪,入署幾為所戕,因是發憤募勇萬人,浸以成軍,其時亦好勝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為一笑。”
生死都置之度外,還有什么放不下
同治六年五月十七日,曾國藩看到趙烈文在讀佛教典籍,就開口問其中的含義。聽了趙解釋后,曾又囑趙解釋佛經梵文名詞,以便于自己閱讀。十天后的五月二十七日,趙烈文送了一本《圓覺經略疏》給曾國藩,并為曾國藩解釋和翻譯其中的名詞術語,抄寫一冊給他備查。
因為對佛學有共同興趣,所以在五月十七日的談話中又把話題轉到《莊子》上來。曾國藩說:你剛才所說佛教經典的意境,《莊子》一書也有論述。趙烈文說他對《莊子》沒有很深研究,不敢擅自斷言。接著他就順著《莊子》的話題問曾國藩:老師的學問閱歷十分豐富,大事與小事,成功與失敗,大喜與大悲,都經歷過、體驗過,人生可以說達到了很高的境界,現在對自己能否做到十分的把握呢?曾國藩對這個話題似乎很感興趣,于是摸著胡須想了很長時間,才回答說:把握不敢說。但目下想來,就是有股不怕死的精神,因此無論遇到什么事情,都本著死的想法,不知算不算足下所說的把握?趙烈文說:一切至高至大的境界,都不過生死,連生死都置之度外,還有什么放不下呢!不過從佛學的最高境界來看,不怕死仍然是境界未到至高至大啊!因為不怕死仍然是有一念在心中,還沒有到真本原。曾國藩聽后,表示完全贊同。
七月十九日下午,曾國藩到趙烈文處閑談,坦露自己多年來艱難困苦終于有所成就的心路歷程。他說:我剛創辦湘軍那會兒,幾乎所有人都表示懷疑,對我的非議和誹謗也很多。靖港之敗后,更是受到湖南地方官僚的指責和謾罵,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甚至要求駱秉章彈劾我。我的部下出入長沙城,也是“恒被譙訶,甚有撻逐者”。咸豐四年以后,我在江西作戰數載,遭遇挫折,經歷了各種磨難,更是成了眾矢之的。咸豐八年重新出山后,朝廷忽而讓我進兵四川,忽而讓我援助福建,自己絲毫不能做主。到了咸豐九年,因為得到湖北巡撫胡林翼的支持,彼此親如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誠令人念之不忘”。
總督衙門也藏有“私鹽”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曾國藩到趙烈文處,見他正在吃飯,就沒有進去。飯后,趙到曾內室久談。曾國藩將《五禮通考》的最早刊印本拿給趙看,筆畫如手寫一般,十分可愛;曾又把進呈給皇上的《御批通鑒》刊印本拿給趙看,趙無意中看到書堆中夾有民間刊刻的《紅樓夢》,十分驚訝,于是笑著和曾打趣說:“督署亦有私鹽邪!”《紅樓夢》是禁書,鹽由國家專賣,曾國藩私讀禁書,當然與私賣食鹽一樣,都屬違法行為。
每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督署不僅有“私鹽”,而且曾家也有一本難難念的經。同治六年九月十日,曾國藩設宴為趙烈文餞行,菜肴非常豐富,談話尤其暢快。趙這次是去湖北看望在那里做巡撫的曾國荃(曾國荃出山做湖北巡撫后,上章彈劾湖廣總督官文,一石激起千層浪,京中流言四起,曾國荃自己也陷入極大的困境中),所以曾國藩的談話主要是圍繞自己的家事進行。
曾國藩說:“未受寒士之苦,甫欲求館而得鄉解,會試聯捷,入館選。然家素貧,皆祖考操持。有薄田頃余,不足于用。常憶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假歸,聞祖考語先考曰:‘某人為官,我家中宜照舊過日,勿問伊取助也。吾聞訓感動,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而家中亦能慎守勿失,自昆弟妻子皆未有一事相干,真人生難得之福。親族貧窘者甚多,雖始終未一錢寄妻子,顧身膺膴仕,心中不免缺陷。復得九舍弟手筆寬博,將我分內應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貪名而我償素愿,皆意想所不到。家中雖無他好處,一年常無病人,衣食充足,子弟略知讀書,粗足自慰。”趙烈文說:“聆師所述,足見積累之厚。至家庭相諒,子孫逢吉,皆師清德所感。上天報施之道,屈彼申此,自然之數也。”
宴請結束后,趙烈文去別人那里走動,回到總督衙門已是初鼓時分。聽說曾國藩兩次來找過他,趙當即趕了過去。一見到趙,曾國藩的話匣子就打開了。這回主要是說他的九弟曾國荃:“鄉間塘濼所時有,舍弟宅外一池,聞架橋其上,識之者以為似廟宇,所起屋亦極拙陋,而費錢至多,并招鄰里之怨。”趙烈文有些不解地問:“費錢是矣,招怨胡為者?”曾國藩說:“吾鄉中無大木,有必墳樹,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為蔭,多不愿賣,舍弟已必給重價為之,使令者則從而武斷之。樹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間值一緡者,往往至二十緡,復載怨而歸。其從湘潭購杉木,逆流三百余里,又有旱道須牽拽,厥價亦不啻數倍。買田價比尋常有增無減,然亦致恨。比如有田一區已買得,中雜他姓田數畝,必欲歸之于己,其人或素封,或世產,不愿則又強之。故湘中宦成歸者如李石湖、羅素溪輩買田何啻數倍舍弟,而人皆不以為言,舍弟則大遺口實,其巧拙蓋有天壤者。”趙烈文說這正是沅帥為人厚道的地方。官宦之人回到原籍后,購置產業是正常情況,與其做得巧妙,不如拙實好。拙不過損害一時的清廉名聲而已,心意畢竟是好的,沒有刻薄寡恩之嫌,一定能給子孫帶來福祉。即使遇上兵荒馬亂年代,因為是用厚實得來,所以憂患也比較輕。曾國藩說:“此理誠是,然如舍弟亦太拙矣。憶咸豐七年,吾居憂在家,劼剛(曾紀澤)前婦賀氏,耦耕(賀長齡)先生女也,素多疾,其生母來視之,并欲購高麗參。吾家人云:‘鄉僻無上藥,既自省垣來,何反求之下邑邪?’對曰:‘省中高麗參已為九大人買盡。’吾初聞不以為然,遣人探之,則果有其事。凡買高麗參數十斤,臨行裝一竹箱,令人擔負而走,人被創者則令嚼參以渣敷創上,亦不知何處得此海上方。”趙烈文大笑說:“沅帥舉動真英雄不可及,書之青史,古人一擲百萬,奚以過之。”隨后又問曾國藩四弟(曾國潢)是怎樣一個人?曾國藩說:“極長厚人,而好事喜功,不顧清議則同。在鄉有獄訟,縣邑不能決者,往往來訴,輒為分剖,勝者以為所應有,負者則終身切齒。足下視此,以為居鄉宜乎否乎?”趙烈文緊皺眉頭想了會兒,說:老師兄弟一別,已經十年了,何不招四弟來此一游?曾國藩說:“吾久為斯說而不見聽,奈何!方今多故,湘中人人以為可危,兩舍弟方徑情直行,以斂眾怨。故吾家人屢書乞來任所,以為禍在眉睫。”
無話找話,相互調侃
曾國藩和趙烈文的談話不僅海闊天空,無所不包,而且常常無話找話,相互調侃。如同治三年七月八日下午,趙得知曾被清廷封為一等侯,就入內賀喜,并打趣說:“此后當稱中堂,抑稱侯爺?”曾笑著說:“君勿稱猴子可矣!”說完,兩人都大笑不止。又如同治六年九月六日,曾國藩到趙烈文處閑談,當時剛好有人送給曾一只古碗,非常大,于是對趙烈文說:“余脾胃甚壞,故欲得數小碗盛菜,期醒目耳。今此大碗安用之?”趙聽得有趣,也忍不住開起玩笑來:“甚有用處。”曾很認真地問有什么用?趙烈文說:“燒滿碗魚翅以飫烈,亦妙事也!”曾于是大笑說“諾!”趙也大笑說:“烈今年三十有六而童心方盛,奈何?”曾說:“此正過人處。”說話間,曾國藩脫下馬褂放到床榻上,談話結束時忘了帶走,趙拿起一看,不僅面料里料都很普通,而且非常短小,貧寒之士都很少穿這種衣服,趙烈文為此感嘆不已。
像這類相互打趣的事例,趙烈文日記中隨處可見。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生動有趣的細節,才在我們面前呈現了一個完整而又真實的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