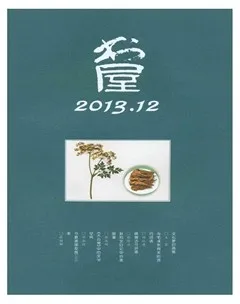大樓、大師與教授的 inspiration精神
民國時期,梅貽琦先生游學歐洲后回到國內,1931年就任清華大學校長,他在12月4日的就職演說中有一段重要的話,這就是我們熟知的:“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校長這“大樓”、“大師”之論使人們從中理解到,作為學者和教育家所持的成熟的、先進的辦學理念多么重要。今天,我們看到梅校長的這個辦學理念已經被歷史驗證。我們知道,在梅校長之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因為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這四位大師,才使國學研究院在不足五年里(1925—1929),培養出七十幾位學生,他們個個成才,而且多有出類拔萃之士。他們離開清華后大多活躍在教育、學術、文化領域,為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為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深深地影響和引導了中國學術發展,其學術蹤跡在一些領域至今猶存。四大導師和他們培養的學生,使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為清華前期發展中的濃墨重彩,是清華的一個時代的標識和里程碑。何兆武教授很準確地總結過清華國學研究院,他說:“清華國學研究院支撐了文化轉型時期我國精神文明與學術的半壁江山。它所培養的學生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我國人文學科當時無愧的中流砥柱。”王國維,我國國學發展中最有影響的史學家,他在國學研究院講授有“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等課程,指導學生研究范圍是經學、小學、上古史和中國文學等。梁啟超既是學者也是政治家,所開課程有“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歷史研究法”等。陳寅恪在國外游學近十年,是我國重要的歷史學家,不僅精通古文字學和英、法、德等文,而且通希臘文、蒙文、藏文、梵文和巴利文等,他專攻中西交通史、佛教流傳史等,開設“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文法”等,指導學生對古代碑志與外族關系作比較研究,還有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的比較研究等。趙元任是通曉多種外語和多種漢語方言,并進行實驗語言學研究的國內外著名的語言學大師,他開設的課程有“現代語言學”、“方言學”、“音韻學”等。國學研究院這四位導師學識淵博,治學嚴謹,不僅貫通古今,而且融匯中西,這使他們所開設的課程能夠借鑒西方現代科學方法和理念,以自己的獨到研究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成為學術高峰,把學生引入到前沿和學術高地。清華國學研究院不僅有這杰出的四大導師,時任講師的李濟、助教趙萬里、浦江清、梁思永等人也都是年輕的精英,后來他們也都成為有重大學術成就的著名教授,各自學術領域中的學術大師。國學院的畢業生中出現了劉盼遂、高亨、周傳儒、謝國楨、劉節、陸侃如、王力、姜亮夫、羅根澤、蔣天樞、徐景賢等這樣一些在史學、哲學、語言學、古文字學等諸領域中的大師和杰出學者,其學術影響至今未絕。
清華國學研究院有這樣的劃時代成就,并不奇怪,更不偶然,從它籌備、誕生之日就已經注定了它絕不是個平庸的學術機構。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先生曾有意延聘胡適來任導師主持國學研究院,但是胡適婉拒了。他說:“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是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云祥校長本想由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回來的吳宓為研究院院長,但是吳宓堅辭不就,只做研究院的執行秘書。吳宓協助曹云祥校長,研究院聘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導師。特別是為聘任到陳寅恪,吳宓更是“竭盡努力進行推薦”,幾番周折。
還有人們熟知的西南聯大,也可作為梅貽琦校長“大樓”、“大師”之論的驗證。在抗日的民族危亡關頭,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三校組成西南聯合大學,1937年至1946年在昆明辦學,史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許多佳話,甚至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中單獨研究的篇章。重要的是留下了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辦學經驗,深深地驗證了辦好大學必備的最基本條件:要有優秀的教授。那時的西南聯大差不多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教授和學術精英。1946年西南聯大復員解散前,由聯大《除夕副刊》主編的《聯大八年》中,有一個統計:聯大共有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歐陸、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聯大的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但也有考察歐美日本的經歷)。五位院長都是留美的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和兩位留學歐陸,二位留英之外,其他皆為留美。我們僅舉若干位來領略一下聯大的教授陣營;相信閱讀稍寬泛一些的人不難知道他們的研究領域或學術專長。他們是鼎鼎大名的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魏建功、楊振聲、陳寅恪、王力、浦江清、劉文典、唐蘭、葉公超、柳無忌、李廣田、威廉·燕卜蓀(英)、潘家洵、吳宓、錢鐘書、劉澤榮、朱光潛、洪謙、馮至、聞家駟、溫德(美)、雷海宗、姚從吾、鄭天挺、傅斯年、毛子水、錢穆、邵循正、向達、張蔭麟、吳晗、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沈有鼎、馮文潛、賀麟、鄭昕、容肇祖、陳康、熊十力(專任講師)、張奚若、錢端升、羅隆基、陳岱孫、戴世光、陳序經、陳達、潘光旦、李景漢、吳澤霖、費孝通(講師)、吳景超、蕭公權、蕭滌非、沈從文、卞之琳、楊業治、查良釗、陳福田、皮名舉、袁復禮、李輯祥、蔡力陰、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周培源、王憲鈞、華羅庚、黃子卿、吳有訓、葉企孫、曾昭掄、王凎昌、束星北、吳大猷、楊武之、張文裕、王竹溪、馬仕俊、趙訪熊、趙九章、錢思亮、馮景蘭、楊石先、李繼侗、僥玉泰、許寶騄、劉仙洲、江澤涵、姜立夫、顧毓秀、陳省身、董作賓、趙忠堯、任之恭、陳芳允、林家翹、張子高等等。這份名單雖然有點長,但是個個閃光,個個響亮,每一位都是在學術史中有位子的人。他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至今我們仍在受其恩澤和教誨。
有統計表明,194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八十一位院士中,西南聯大占二十七位,也就是占了三分之一;1955年大陸中科院的四百三十多位學部委員(院士)中,有西南聯大背景者占兩百多位,幾近一半。西南聯大校舍簡陋,沒有大樓,多為泥墻鐵皮頂房舍,學生宿舍狹窄住多人而昏暗;教授們也多住簡易住宅或鄉間民房。但是,這樣一個特別的戰時大學正因為有這批大師級的精英教授,為國家培養出大批人才,特別是其中不乏杰出人才。二十三位“兩彈一星”功勛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八位從西南聯大走出來的,他們是:郭永懷、趙九章、陳芳允、屠守鍔、楊家墀、朱光亞、王希季、鄧稼先。最先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都是西南聯大的學生。還有一批聯大培養出來的學者成為不同領域的佼佼者或領軍人物,如鄒承魯、王浩、王湘浩、黃昆、劉東升、葉篤正、熊秉明、何炳棣、任之恭、何兆武、殷海光、任繼愈、王佐良、汪曾祺、鄭敏、穆旦、宗璞,還有宋平、彭佩云、王漢斌等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就和西南聯大的輝煌,是梅貽琦校長關于“大樓”、“大師”之論的最好詮釋。
關于“大樓”、“大師”之論,梅貽琦校長完整的話是這樣:“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的智識,固有賴于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梅校長這最后一句話也非常重要,但是常被人們忽略而未加多領會,這inspiration大致是啟示、鼓舞或推動的意思。著名的丹麥物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奧格·玻爾也用過這個詞,說他父親尼爾斯·玻爾(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早已看出inspiration對科學發展的偉大作用。在他主持的玻爾研究所里就有濃濃的inspiration精神,在這里產生了十余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梅校長看來,在大學里,教授不只是教育學生學到知識,獲得專業訓練,不是培養工匠,在此之外,還要對學生有啟示,有鼓舞,有推動其精神上成長的氣氛,大體可理解為對學生還要有比“傳道、授業、解惑”更豐富的精神層面的積極影響和引導,大有以學生為本、施博雅教育的意思。在西南聯大絕不缺少這樣的教授,他們留下了許多故事。聞一多教授可為其中最典型、影響極大的一位,他一生本著“義所當加,毅然為之”的中國文人傳統精神,在解放之前最后的黑暗中,為捍衛民主、正義,大氣凜然,不畏生死而倒在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槍聲中,成為一代鼓舞青年的民主斗士。西南聯大的老學生、著名的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先生說到他的老師吳宓先生時,這樣說:“為學和為人在先生乃是一回事。先生生平不求聞達,在學院的圈子之外,也無籍籍之名;而學生遇到困難時,卻把先生看作真正是自己的導師和引路人。先生畢生執教,桃李滿天下,期間人才輩出,不少都是蜚聲海內外的學者,如錢鐘書、李賦寧諸位先生,我想他們受益于先生的風格者,恐怕并不亞于受益于先生的學問。”這里何先生正是看到了吳宓先生的inspiration精神。西南聯大的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極力倡導通識教育、人格教育,指出“專門教育”與人格陶冶相分離的弊端。張申府先生在抗戰即將勝利的時候更是這樣說:“這幾年來,國人中表現的比較最規矩、最公正,比較最有知識,最能感覺、最關懷國家,忍受的苦難也比較最多,最不失為國家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學教授。”梅貽琦校長說的更生動:“學校猶如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教授與學生正如水中之大魚與小魚的“前導”和“尾隨”,“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不正是教授對學生應有的inspiration嗎?若稍做一點引伸,我們中國文化中的“游學”一詞正好像生動地表意出師生之間的微妙關系,似乎其中也正滲透著inspiration精神。這使人聯想到拉斐爾創作于十六世紀初期的那幅膾炙人口的《雅典學園》,在畫中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師生一面走一面熱烈的討論著,更像辯論著什么問題:老師用右手的一個指頭堅定地指向上,而學生的整個右手卻相反,似也未遲疑地向著地面,師生的生動形象使我們感覺到他們之間也不缺少inspiration精神吧,作為老師,柏拉圖不正在發揚著這種精神嗎?這幅畫和西南聯大的歷史,使我們看到了如古語所言“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的效果。
站在今天回望歷史,現時的中國大學比起老清華也好、比起西南聯大也好差別和變化太大了,但是大學教育的基礎和基本規則不應有根本性變化,教授的根本性作用不應變,校園里的inspiration精神更不可無。令人可惜的是,在我們的大學里,在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系現在淡化了,甚至缺少了那非常可貴的inspiration精神。這提示我們,在反復咀嚼和討論梅校長的“大樓”、“大師”之論后,應該更多地注意教授了,而教授也該自省和反思了,首先看看今日的中國教授身上和校園里還有多少inspiration精神。雖然沒有大樓而因為有大師,則可以辦成培養出杰出人才的優秀大學,已如西南聯大;今日的中國,多的是雖然有漂亮的新大樓,因為沒有大師,更少了inspiration精神,也就少有一流的大學。這應該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了,特別是因為現在我們有太多教授的靈魂太多地迷失了,甚至不在大學里了,該等一等了,要找回來才是。這些教授們大概正像黎巴嫩阿拉伯詩人紀伯倫說的那樣:“我們已經走的太遠,以至于我們忘記了為什么而來。”教授們,我們為什么而來?首先找回那可貴的inspiration精神吧。
今日的中國人民大學有“大師、大樓、大氣”一說,從一個側面看,這不失為是契合時代發展又立意高遠的一種應有的理念和追求。首先要有大師,又有大樓,這樣再去追求和創造出新時代大學的大氣,既有物更有人的大氣,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大氣、時代的大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