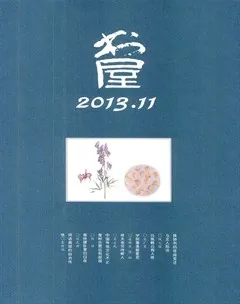錢鐘書的住房變遷與文人際運(yùn)
錢鐘書生于清宣統(tǒng)二年(1910),逝世于1998年,經(jīng)歷了中國社會由近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時期,歷經(jīng)一系列重要變革與運(yùn)動:末代王朝瓦解,民國成立,軍閥混戰(zhàn),抗日,國共內(nèi)戰(zhàn),新中國成立,反右,“文革”……期間,他從無錫到北京、上海、英國、法國、昆明、藍(lán)田,再到上海、北京,他的人生軌跡就是一部生動的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史。
無錫錢家(1910.11.21—1935.8)
宣統(tǒng)二年(1910)11月21日,錢鐘書在無錫岸橋巷秦氏宅出生。秦氏宅為錢家賃租之地。此前錢家在中市橋吳氏宅和東門駁岸湯氏宅都賃居過,秦氏宅是1901年開始租的。宣統(tǒng)三年(1911),再遷至胡橋,租韓氏宅。1915年,遷至大河上侯氏宅。1919年,遷至流芳聲巷租朱氏宅。1923年,移居七尺場新宅。自此,錢家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結(jié)束了長期租房而居的局面。
錢鐘書的童年就是在七尺場新宅度過的。后來上中學(xué)后才漸漸遠(yuǎn)離住所。1923年,錢鐘書小學(xué)畢業(yè),考入蘇州桃塢中學(xué)。1927年,桃塢中學(xué)停辦,轉(zhuǎn)入無錫輔仁中學(xué)。1929年,高中畢業(yè),被清華大學(xué)破格錄取。大學(xué)四年,也只有寒暑假回?zé)o錫老家。1933年清華畢業(yè),到上海光華大學(xué)任講師。初到光華時,錢鐘書與同事顧獻(xiàn)梁共處一室。在上海兩年,因?yàn)榫嚯x無錫近,回?zé)o錫次數(shù)較多。
留學(xué)英、法(1935.9—1938.8)
1935年夏,錢鐘書與楊絳結(jié)婚。此時錢鐘書已通過英庚款第三次留學(xué)考試,獲得公費(fèi)留學(xué)機(jī)會。新婚之后,夫婦二人同赴英國留學(xué)。9月,抵達(dá)倫敦。在牛津大學(xué)校外,他們租得一間較大的房間,做臥室兼起居室。因?yàn)榛锸巢缓茫X鐘書吃不飽,餓得面黃肌瘦。他們想改租一套帶爐灶炊具的住房,自辦伙食,改善生活。在牛津大學(xué)公園對街高級住宅區(qū),楊絳偶見花園路的瑙倫園風(fēng)景勝處,有一座三層洋樓,他們租了其中的二樓。這一層有一間臥室,一間起居室,兩間屋子前面有一個大陽臺,是汽車房的房頂,下臨大片草坪和花園,有專用浴室?guī)N房使用電灶,很小。這套房子與本樓其他房間分隔,由室外樓梯下達(dá)花園,另有小門出入。這里地段好,離學(xué)校和圖書館都近。環(huán)境幽雅,門對修道院。錢鐘書很喜歡這地方。1935年底遷入新居。1936年暑假后,房東因?yàn)榱硪患曳靠桶嶙撸瑸樗麄儞Q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浴室還有大澡盆和電熱水器。
1937年6、7月份,錢鐘書順利通過論文答辯,取得學(xué)位。8月下旬,他們離開牛津,進(jìn)入巴黎大學(xué)學(xué)習(xí)。清華老同學(xué)盛澄華已經(jīng)替他們租賃好了公寓。公寓在巴黎近郊,離火車站很近,乘車五分鐘就可達(dá)市中心。1938年早春,戰(zhàn)情日緊,局勢變得日漸不安,危機(jī)重重,雖然庚款獎學(xué)金還可延長一年,但錢鐘書決定如期回國。3月12日,錢鐘書給英國朋友寫信說:“我們將于九月回家,而我們已無家可歸。我們各自的家雖然沒有遭到轟炸,都已被搶劫一空……”
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冷屋”(1938.9—1939.7)
1938年9月下旬,錢鐘書回國,被母校清華大學(xué)破格以教授身份邀回任教。當(dāng)時清華大學(xué)已并入在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于是他一下船就到昆明報到,楊絳帶著孩子先回上海。
錢鐘書在聯(lián)大的住處在昆明大西門文化巷十一號,房子非常小,“屋小如舟”。抗戰(zhàn)時期,西南聯(lián)大教職員宿舍都極其狹窄簡陋,多是租賃的民房。錢鐘書在詩中描述過他的住所:“屋小檐深晝不明,板床支凳兀難平。蕭然四壁塵埃繡,百遍思君繞室行。”和他同院居住的還有清華外文系1935年畢業(yè)的助教顧憲良,外文系的高年級學(xué)生李賦寧、周玨良,哲學(xué)系的鄭僑等。他的房子雖小,當(dāng)時在昆明能獨(dú)居一室卻已很幸運(yùn),葉公超、吳宓、金岳霖等初到昆明都是兩三人合住一室。錢鐘書獨(dú)自在聯(lián)大,難以排解一個人獨(dú)處他鄉(xiāng)的孤寂、冷清,于是他把自己的屋子取名“冷屋”。1939年1月到5月,他在《今日評論》周刊上發(fā)表了四篇“冷屋隨筆”。在《冷屋隨筆之一》引言中寫道:“賃屋甚寒,故曰冷。”
國立師范學(xué)院“小屋”(1939.11—1941.6)
1939年7月,聯(lián)大的暑假剛一開始,錢鐘書就急不可待地回到上海。岳父楊蔭杭得知女婿將回來度假,特別騰出房間讓他們一家到來德坊租處住。本來錢鐘書準(zhǔn)備好好度這個暑假,享受一下家人團(tuán)聚的樂趣。但遠(yuǎn)在湖南藍(lán)田的國立師范學(xué)院的父親來信,說自己老病,想念兒子,讓他到藍(lán)田去侍奉,并任英語系主任。楊絳認(rèn)為“侍奉”是借口,主要是為聘請不到合格教師的國師招人。錢鐘書雖然非常不愿辭去清華的工作,但礙于老父和家人的態(tài)度,不得已來到國立師范學(xué)院出任英語系主任。
藍(lán)田在湖南西部,舊屬安化縣(今屬漣源市),是湘黔鐵路線上群山環(huán)繞的一個小鎮(zhèn),非常偏僻。這個小鎮(zhèn)很小,幾無地可游。國立師范學(xué)院在這座小鎮(zhèn)西北一里許的李園,原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李燮和在老家修建的府第。全園占地百畝,房屋兩百間,錯落有致。地方偏,房子多,這是當(dāng)時選址建校的重要原因。錢鐘書住在一處小屋中,生活極其單調(diào)刻板。課余時間多關(guān)在小屋里埋頭讀書、臨摹書法或?qū)懽鳌R雇碜x書寫作條件很不好,沒有電燈,剛建院時,全院師生都用燈心草爇桐油盞照明,稍后改用植物油燈。《談藝錄》的一半和《窗》等幾篇散文就是在這里寫出的。因?yàn)閷W(xué)生少,平時系務(wù)和教學(xué)任務(wù)并不重,他在給朋友的信上說:“此地生活尚好,只是冗閑。”
上海辣斐德路錢家與蒲園“且住樓”(1941.7—1949.8.24)
1941年暑期,錢鐘書正式向國立師院辭職,回到上海錢家。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八年抗戰(zhàn)開始。10月,日機(jī)開始轟炸無錫。11月25日,日軍侵入無錫。錢鐘書的叔父錢基厚受到日偽的通緝,于是他將錢家老小近二十口送到無錫西鄉(xiāng)新瀆橋暫避。1938年初,其攜家人輾轉(zhuǎn)來到上海。錢基博那時隨校遷到江西泰和。1938年4月,錢基厚次子錢鐘漢夫婦、五子錢鐘魯、六子錢鐘彭也來到上海,因人數(shù)日多,經(jīng)友人介紹,乃租賃辣斐德路六百零九號(現(xiàn)上海復(fù)興中路五百七十三號)沈氏宅而居,“自此長為僑滬之人矣”。這處房子是一所臨街的三層樓弄堂房子,后面一大片同式樣的樓房,由弄堂進(jìn)出。
錢鐘書此次從藍(lán)田回上海時,辣斐德路錢家人口又有所增加,錢基厚分給錢鐘書父母住的二樓大房間和亭子間均已住滿人,一時半會又租不到房子,錢基厚就把他家原在樓下客堂搭鋪歇宿的兩個女傭,搬到三樓的過道里,把原來臨街窗下待客用的一對沙發(fā)和一張茶幾挪開,鋪上一張大床,掛上一幅幔子,讓錢鐘書一家三口就擠居在幔子背后。白天,客堂照常會客,錢基厚還當(dāng)作講堂教孩子們讀英文。好在這樣的日子不是很長。不久錢鐘書的二弟一家到了武昌,妹妹錢鐘霞也去了藍(lán)田,三弟一家搬到無錫,擁擠的一大家,后來只剩下錢鐘書的母親和他們一家三口。他們就搬進(jìn)亭子間,屋子很小,一張大床、一個柜子和一張小書桌。據(jù)他當(dāng)年的學(xué)生回憶,這處不大的房間堆滿了書籍,與其說是住房,不如說是書房。無論如何,總算有了讀書寫作、談心、同友人交流的空間。這間屋子,一住就是八年。
1949年上海解放。是年初,錢基厚讓錢鐘書三弟媳攜子女三人來上海,住辣斐德路。這時錢基厚夫婦和三子一女六人,再加孫兒和奶媽共八人,錢鐘書一家三口和弟媳及子女六人,一大家子不便再擠居一起了。剛好傅雷夫人的朋友有空房在蒲石路蒲園,他們一家三口就遷居蒲石路蒲園。錢鐘書稱蒲園為“且住樓”。這處新居確實(shí)沒住多長時間。不久,夫婦二人得到清華大學(xué)聘書。8月24日,動身赴北京。
清華大學(xué)新林院(1949.8—1952.10.15)
1949年8月26日,錢鐘書回到闊別十余年的清華園。剛到清華時,他們暫住楊絳堂姐楊保康家,新林院七號,即從前的新南院。不久,學(xué)校甲級住宅分配委員會出臺“分隔與調(diào)整”辦法,對居住人口較少的甲級住宅進(jìn)行分隔,一幢住兩家。錢鐘書一家被分配住新林院七號乙,臨時遷居工字廳西頭的客房,等校方派工匠來打隔斷。西客廳久無人住,破爛不堪,地板下老鼠橫行。好在熬過半個冬天,房子總算隔好,他們又搬回新林院。周圍的鄰居有潘光旦、梁思成、林徽因、霍秉權(quán)、林超等。他們熟悉的師友分居于西院、北院、勝因院等不同的宿舍區(qū)。因?yàn)闆]打算長住,這段時期他們家里家具只買了必不可少的床、衣櫥,桌子是借楊保康家的舊桌,箱子當(dāng)?shù)首幼依锓浅:喡?/p>
1950年8月,錢鐘書調(diào)往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工作,平時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
北京大學(xué)中關(guān)園二十六號(1952.10.16—1959.5.14)
1952年全國院系調(diào)整,錢鐘書雖然還在城內(nèi),但已被調(diào)入文學(xué)研究所外文組。文研所編制、工資屬新北大,工作由中宣部直接領(lǐng)導(dǎo)(1956年正式劃歸中國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錢鐘書不再在清華的教工宿舍居住,10月16日,舉家遷入新北大新建宿舍中關(guān)園二十六號,從此離開清華。
中關(guān)園是北大搬到西郊以后為教職員工新建的宿舍,位于北大東門對面,對著校內(nèi)理科樓群。新房面積不大,是個平房。錢鐘書利用屏風(fēng),從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間書房,并把小書房稱為“容安室”、“容安館”、“容安齋”。錢鐘書在1954年寫過《容安室休沐雜詠》組詩,第一首曰:“曲屏掩映亂書堆,家具無多位置才。容膝易安隨處可,不須三徑羨歸來。”寫的就是這個新家。
1954年翻譯“毛選”工作告一段落,錢鐘書回到文學(xué)研究所工作。
東四頭條一號文學(xué)研究所宿舍(1959.5.15—1962.8.13)
1956年秋,文學(xué)研究所撤出北大,搬到中科院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所在的中關(guān)村社會樓。1958年冬,再遷至建國門原海軍大院。職工宿舍也一遷再遷。到1959年,文學(xué)研究所才開始有正式宿舍,就是東四頭條一號。1959年5月,錢鐘書一家從中關(guān)村小平房遷到東四頭條文研所宿舍。
東四頭條宿舍是由一座辦公樓隔成四家的結(jié)構(gòu),面積比中關(guān)園平房要小,是個大雜院。錢鐘書的新家是由一間寬大的辦公室隔成的五小間,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住在另外的三間房里。當(dāng)時有人去他們家后,發(fā)現(xiàn)主人顯然是力戒任何排場與氣派,客廳里只有再簡單不過的幾把坐椅。
從1958年初到1963年,錢鐘書是英譯“毛選”定稿組成員,雖遇“三年困難時期”,但他生活無憂。
干面胡同十五號學(xué)部宿舍(1962.8.14—1969.10.10)
1962年8月14日,錢鐘書一家在東四頭條居住三年多后,搬到干面胡同十五號學(xué)部宿舍(在學(xué)部新建大樓內(nèi)),離東四頭條并不太遠(yuǎn)。干面胡同十五號,是中國科學(xué)院社會科學(xué)學(xué)部高級研究人員的宿舍,是1961—1962年新建的磚混結(jié)構(gòu)樓房,住房條件比較好。1962年入住,當(dāng)時有二十九戶。住戶中包括了像錢鐘書、金岳霖這樣的一級研究員,還有部分副研究員和若干高級行政干部等。他們的新家近八十平方,在當(dāng)時算不小了。一共有四個房間,朝南三間,中間是客廳,沿墻放書櫥,一間廚房、一間衛(wèi)生間、一個陽臺。東邊一個套房是錢鐘書的臥房兼書房,西邊臨陽臺的一間是楊絳的臥房兼書房。幾年之后,女兒結(jié)婚,女婿住進(jìn)了他們家。朝北的西盡頭房間就成了女兒和女婿的新房。他們添買了家具,住得很寬舒。
1963年英譯“毛選”定稿工作一結(jié)束,1964年,錢鐘書又成為翻譯毛澤東詩詞五人小組成員。“文革”開始,翻譯毛詩的工作一停止,錢鐘書才真正嘗到運(yùn)動之苦。1966年8月16日,他被革命群眾“揪出來”,變成了“牛鬼蛇神”、“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寬舒的住房條件也很快受到威脅。
當(dāng)時學(xué)部的另一處宿舍是西觀音寺四十五號,多為資歷較淺的研究人員和行政人員居住。單身的年輕人住集體宿舍,人均六點(diǎn)六平米。“文革”兩三年后,已是革命小將的那些單身青年陸續(xù)成家,整個社會忙于運(yùn)動又沒有新建住房,因此住房顯得十分緊張。解決的一個辦法,就是占用其他有房者的房子,大家共同居住。這樣,干面胡同那些“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的住房,就順理成章的被占用,還被美其名曰“摻沙子”。楊絳說這是軍宣隊(duì)在“文革”中采取的一項(xiàng)革命措施,讓“革命群眾”入住“資產(chǎn)階級權(quán)威”家。干面胡同的三居室,大都摻進(jìn)了“沙子”。1969年5月19日,錢鐘書家里住進(jìn)“一個在工、軍宣隊(duì)那里很吃香的革命派兩夫婦”,占去房屋兩間,只剩下客廳和原先錢鐘書的臥室兼書房。好在住在一起不是很長時間,錢鐘書就下放干校了。
“合居”現(xiàn)象在“文革”前就開始,但“文革”之中達(dá)到了高峰,成了一種普遍的居住形式。這種現(xiàn)象一直延續(xù)了三十年,深深影響了中國城市社會的人際關(guān)系。合居的住戶之間吵架、罵街甚至大打出手,成為常見現(xiàn)象。
干校的集體房(1969.11.11—1972.3.12)
1969年嚴(yán)冬,學(xué)部人員分批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11月11日,錢鐘書作為“先遣隊(duì)”隊(duì)員之一,下放河南羅山干校。不久,干校從羅山而息縣,從息縣而明港,輾轉(zhuǎn)遷徙。多數(shù)時候,下放人員都是集體住在一間屋子里,條件艱苦,有時饑不果腹。錢鐘書在下放期間負(fù)責(zé)收發(fā)過信件、報刊,燒過開水等。
有回憶說,在羅山,八十個單身漢聚居在一間屋里,分睡在幾個炕上。但據(jù)錢碧湘回憶,下干校之初,“錢先生和吳世昌先生等四人同住一間土屋。地面比路面低,進(jìn)門要下兩級臺階,非常潮濕。四塊鋪板緊靠四墻擺放,中間一小方空地,白天便權(quán)充工場。”過了一個多月,他們搬到息縣東岳。這個地方地僻人窮,沒有房子住,他們就自己造。錢鐘書這時變得又黑又瘦,一般人都不認(rèn)識了。1971年早春,學(xué)部干校搬到明港某團(tuán)的營房,四五十人擠住在一間兵營的大瓦房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玻璃房,洋灰地,上面懸著一只非常昏暗的燈泡。廁所不再是葦墻淺坑,如廁也不需要排隊(duì)了。干校期間,錢鐘書一有空閑就找書看。
1972年3月12日,錢鐘書隨第二批“老弱病殘”回北京。此時他們必須要面對兩家人同住一個屋檐下的生活了。錢、林兩家擠在一起,什么隱私都沒有,抬頭不碰低頭碰,難免出現(xiàn)矛盾。1973年12月2日,終于爆發(fā)打斗。有關(guān)兩家打架的原因各說各是,在上個世紀(jì)末的文壇熱鬧過一段時間。這其實(shí)是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的一場鬧劇與悲劇,大家都應(yīng)是受害者。
從北師大宿舍到小紅樓(1973.12.9—1974.5.21)
1973年12月9日,錢鐘書夫婦被迫逃離學(xué)部宿舍,開始了他們的“流亡生活”。他們的第一站是女兒錢瑗所在單位北師大學(xué)生集體宿舍。房間在三樓,朝北,陰冷臟亂,沿東西兩墻放著三只上下鋪的雙層單人床,中間對拼四張書桌。他們一到北師大宿舍,錢瑗的同事、朋友就聞訊趕來,同情他們的遭遇,紛紛從家里拿來生活必需品。生活上雖然簡陋,但讓他們感覺到溫暖。不久,錢瑗的一個同事知道他們住宿條件差,便將朋友讓給他的兩間小紅樓的房子,讓他們先過去住,自己仍住原房。12月23日,他們遷入小紅樓。小紅樓是教職員宿舍,條件比學(xué)生宿舍好些。兩間房,一朝南,一朝東,屋里有床和桌椅等學(xué)校的家具。他們和另兩家合住這一組房子,同用一個廚房,一間衛(wèi)生間。這次錢鐘書大病了一場。這是錢鐘書解放后度過的最狼狽、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時期。
學(xué)部七號樓辦公室(1974.5.22—1977.2)
那時候,各單位房子都很緊張。度過寒冬,天氣回暖之后,錢鐘書夫婦想著不能老占人家的房子不還,就去學(xué)部向文學(xué)所“軍宣隊(duì)”求得一間堆雜物的辦公室,在學(xué)部七號樓一層西盡頭。1974年5月22日,他們告別北師大朋友,搬進(jìn)這間辦公室。在搬進(jìn)之前,文學(xué)所與外文所的年輕人已經(jīng)打掃了屋子,擦洗了門窗,配了鑰匙,掛上窗簾,怕暖氣片供暖不足,還裝上了爐子,從煤廠拉來一車又一車的蜂窩煤,碼在廊下,為防中煤氣,還裝上風(fēng)斗。錢鐘書夫婦對這種精心的安排感激莫名。
學(xué)部七號樓有兩層,上下層住有十余戶文學(xué)所同事,每家一間房,住起來非常局促。西盡頭的走廊是廚房兼堆煤餅,走廊就是每家的廚房。錢鐘書所住的這間辦公室一直用作儲藏室,封閉的幾年間,冬天生了暖氣,積聚不散,把房子脹裂,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不過好在墻外還抹著灰泥,并不漏風(fēng)。在這間已是危房的斗室中,他家安了兩張書桌。兩壁是鐵書架(鍋碗瓢盆就放在上面),頂西墻橫放兩張行軍床,中間一只木箱當(dāng)床頭柜。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錢鐘書和其他學(xué)者的“五人小組”繼續(xù)進(jìn)行翻譯毛主席詩詞工作。由于錢鐘書年初曾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戶”。翻譯小組成員不得不每天來陋室工作。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余震不斷,波及北京。七號樓西山墻被震裂,居民紛紛搬到空曠處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錢鐘書等老弱同志轉(zhuǎn)移到大食堂,因?yàn)槭程么笪蓓斒怯霉靶毋U皮連接而成的,不易坍塌。所里的年輕人把他們家的兩張行軍床和生活用品搬到大食堂,將他們安置在最安全的地方。但他們?nèi)]多久,又溜回七號樓。
這一年,十年“文革”宣告結(jié)束。錢鐘書不久也結(jié)束了陋室生活。在這間陋室,他一共住了兩年九個月,完成了《管錐編》初稿,參與了《毛主席詩詞》英譯工作。
三里河南沙溝“部長樓”(1977.2—1998.12)
1977年1月,學(xué)部辦公處的辦事人員忽然給了楊絳一串鑰匙,叫她坐學(xué)部的車,到三里河國務(wù)院新蓋的宿舍去看房子,并說如有人問,就說因?yàn)樗麄冏∞k公室。楊絳和女兒看了房子,立即在年輕同事的幫助下,把干面胡同與陋室里的家當(dāng),在2月4日立春那天搬進(jìn)新居。楊絳怕錢鐘書再次吃灰塵,“把他視為一件最貴重的行李,下午搬遷停當(dāng)后,用小汽車把他運(yùn)回新家”。這次搬家很突然,是在胡喬木的直接關(guān)心下才解決的,楊絳此后幾次表示過“始愿不及此”的感激。
范圍不大的三里河高級宿舍區(qū)直屬國務(wù)院,由一幢幢小洋房組成,聚居著一些高層次的特殊人士。錢鐘書居住的南沙溝小區(qū)是一處鬧中取靜的院落,院里有很多高大的喬木和碧綠的草坪。新居共四間房,一間是錢鐘書夫婦的臥室,一間是給女兒錢瑗居住的,一大間是錢鐘書和楊絳的起居室也稱書房,有時用來充客廳,還有一間吃飯用。錢鐘書夫婦對這套房子非常滿意。楊絳在《我們仨》中寫到:“人間也沒有永遠(yuǎn)。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錢鐘書在這里一住二十年,這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居所。
楊絳先生買新房子(2000)
在錢鐘書去世兩年后,楊絳在北京買了一處新房子。在楊先生自己撰寫的《楊絳生平與創(chuàng)作大事記》中,她清楚地寫道:2000年12月14日,“買房交款”。第二年的9月7日,她在清華大學(xué)設(shè)立“好讀書”獎學(xué)金,正式簽協(xié)議書。這項(xiàng)獎學(xué)金是用他們夫婦2001年上半年所獲七十二萬元稿酬現(xiàn)金以及以后出版的所有作品報酬設(shè)立的。就在設(shè)立“好讀書”獎學(xué)金之后三天,9月10日,楊絳領(lǐng)到新房房產(chǎn)證。楊先生在捐贈稿酬和版權(quán)后,如果要在京城買房子可能就困難了。
以楊先生的現(xiàn)狀和品行,她買這處新房肯定不是為她自己。在女兒錢瑗與錢鐘書相繼離開后,房子、錢財對她來說,意義已經(jīng)不大。在《我們仨》結(jié)尾,楊先生寫到:“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歲末,鐘書去世,我們?nèi)司痛耸⒘恕>瓦@么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jiān)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現(xiàn)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dāng)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房子·文人際運(yùn)·時代變遷
錢鐘書成家以后,隨著工作與環(huán)境的變化,長期處于搬家的狀態(tài)。他曾在別人提問有關(guān)買書、藏書的問題時回答說:“我不買書,因?yàn)槲遗掳峒摇!痹谝殉霭娴腻X鐘書手稿集中,留下了很多有關(guān)住房變遷的痕跡,比如“容安館札記”、“且住樓日乘”、“偏遠(yuǎn)樓日乘”、“偏遠(yuǎn)廬日乘”、“燕巢日記”等,這些五花八門的齋號,是對其住房變化的真實(shí)寫照。
錢鐘書對住房的要求其實(shí)并不高,有書看,有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住什么并不重要。干校期間,他一有空閑就找書看。楊絳在《干校六記》中記錄了這樣一段對話:“默存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默存認(rèn)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真的,什么物質(zhì)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只有在年輕的時候,他曾表露過對理想居處的向往。那是1934年春,他在上海光華大學(xué)工作,北上北京看望在清華讀書的楊絳。他們一起來到動物園,園內(nèi)最幽靜的一隅有幾間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樹,一灣流水。“鐘書很看中這幾間小屋,愿得以為家”。但就是這個“愿得以為家”的地方,也只是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才得以實(shí)現(xiàn)。天地之大,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何其難也。
然而,相對于其他許多人,錢鐘書又算幸運(yùn)的。解放后到“文革”前,知識分子們的住宅分配和占有嚴(yán)格按照級別而定,居住的多寡實(shí)際也成了工資收入的一部分,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錢鐘書因?yàn)橐恢弊鲋汀懊x”、“毛詩”有關(guān)的翻譯工作,加上一級研究員的身份,直到“文革”前,他實(shí)際上沒有遭受多大的不公,即使在狂風(fēng)暴雨般的“反右”浪潮中,也沒有被打成右派,知識分子身份始終是得到尊重的。因此住房條件也是一個逐步改善的過程,尤其是最后在干面胡同十五號的學(xué)部宿舍,住得非常舒適。同一時期,那些資歷淺、學(xué)術(shù)聲名小的人,住房條件相對就差很多,住房需求很難得到滿足。
“文革”開始后,知識分子地位一落千丈,淪為“臭老九”,像錢鐘書這些知名學(xué)者都成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除了受到批判外,住房條件也隨之發(fā)生變化。房子要么被革命小將或工人占去換著住,要么一起合居,知識分子一般只能忍氣吞聲,有時也有口角相交或大打出手的。錢鐘書夫婦就是一例。“文革”期間,錢鐘書經(jīng)歷了生命中最遭罪的一個時期。從寬舒的幾室?guī)讖d,到住干校集體房,到“流亡”大學(xué)宿舍,再到蝸居十幾平米的辦公室,嘗盡搬遷之苦。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雖然和政治形勢與社會地位的變化有關(guān),實(shí)際上與那時包括民宅在內(nèi)的城市建設(shè)的停滯也有很大關(guān)系。長期的政治運(yùn)動,使城市建設(shè)停滯,造成住房緊張,促使那些人以強(qiáng)住、合居等方式獲得住房,這是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的特殊現(xiàn)象。
“文革”一結(jié)束,在胡喬木的干預(yù)下,錢鐘書輕而易舉的搬進(jìn)“部長樓”。當(dāng)時確實(shí)使人產(chǎn)生“一棵參天大樹拔地而起”之感,引起很多人的眼紅。這種眼紅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經(jīng)歷了不堪回首的十年之后,到了八十年代,全國各大城市都進(jìn)入了“房荒時期”,住房需求達(dá)到了極其緊張的狀態(tài),誰都希望能公平、公正的分得一處房子。在這一輪新的住房分配大潮中,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價值開始重新得以體現(xiàn)。在很多單位,分房要打分,那些老知識分子的學(xué)歷、職稱、工齡、年齡、級別等都在打分中占到優(yōu)勢,得到承認(rèn)。九十年代后,一些單位尤其是高校在引進(jìn)人才時,仍把住房作為重要的條件之一,而住房大小也成了衡量其學(xué)術(shù)水平高低的重要標(biāo)尺。其實(shí)為引進(jìn)人才分配一定大小的住房,這不僅是對知識分子的肯定與尊重,也為他們掃除了后顧之憂,只有這樣才能安心搞學(xué)術(shù)研究。把住房完全推向市場,難免會讓知識分子們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上急功近利,導(dǎo)致學(xué)術(shù)腐敗。在錢鐘書去世前后,中國的住房改革已經(jīng)到了全國逐步推開與深化階段,住房已經(jīng)市場化。2000年,楊絳先生在北京買了自己的私人住宅。終其一生,終于拿到屬于自己的一把房屋鑰匙,即便房子并不是為自己而買。
可以說,錢鐘書經(jīng)歷的住房變遷過程,不僅觀照了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知識分子的命運(yùn),也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復(fù)雜、變化最快的一場住宅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