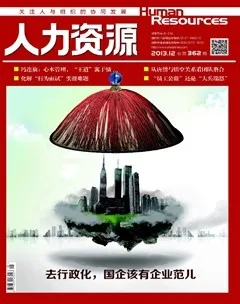亦商亦官:國企的兩張臉
我國社會層面的行政化現象由來已久,而國有企業中的行政化趨勢甚至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用企業創造的利潤和履行的社會責任即可衡量企業和企業家的價值,而給企業和企業領導戴上行政級別的“大帽子”,則純屬多此一舉。因此,若想破除行政化之弊端,就不能不端詳國企和國企領導“亦商亦官”的兩張臉。
“旋轉門”下角色難轉換
我國國企的行政級別是承接計劃經濟而來。計劃經濟時代把一切都納入到計劃中,并根據行政職務的大小來配置公共資源,分配剩余價值,彼時國企坐擁名正言順的行政級別,是因為它裝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盒子里。無論是作為企業還是個人,都很難跳出來。
但是,市場經濟打破了原有的分配體制,在計劃之外,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被確立起來,大量非公企業的崛起不斷瓜分此前被國企所壟斷的領域,這就為國企的去行政化提供了可能。早在1999年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已明確指出:“深化國有企業人事制度改革……對企業及企業領導人不再確定行政級別。” 2000年,原國家經貿委發布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管理基本規范(試行)》明確規定,企業不再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級別,也不再比照黨政機關干部的行政級別確定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待遇,實行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管理辦法。
可惜,上述兩個規定沒有得到貫徹落實,究其根源,在于中國社會各個層面的行政化愈趨普遍,整個社會向做官的行注目禮,國企領導若沒有一定的行政級別,企業和政府的“旋轉門”就沒法打通。而國企領導的任期一般都比較短,很多國企領導只是把任期當作“跳板”,積累幾年的企業資歷后再“跳”回到政府部門,也有一些國企領導原本是因為競爭政府職務失敗,不得已到企業“臥薪嘗膽”。
如此看來,要取消國企領導的行政級別確實有些“實際困難”,它牽涉到企業和政府那扇“旋轉門”的問題。但這種困難只是一種假象,國外也有企業和政府的“旋轉門”,一些國家的政府部長經常是從企業而且是從私人企業提拔而來,比如,高盛公司的董事長保爾森就直接被奧巴馬點將做財政部長。但是國外的國企領導并沒有行政級別,保爾森做財政部長是部長,回到高盛就不是“部長”了,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在企業和政府之間“旋轉”。
長期關注中國改革與社會轉型研究的媒體評論員鄧聿文認為,國企的去行政化,取消國企領導的行政級別,關鍵在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決心。如果政府認為某位國企領導適合從事政府管理工作,完全可以把他安
排在行政崗位(當然要征詢他的意見),而不必拘泥于他有沒有行政級別,是不是干部。做官就為人民服務,造福百姓;當企業家就經營好企業,造福一方。
雙重利益之下難抉擇
國企高管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屬于行政序列的公職人員,還是普通的企業管理者?這個問題恐怕很多人,包括國企高管自己都很難給出準確的答案。如果他們屬于前者,其待遇就應當按相應行政級別來確定;如果他們是后者,那么只需按照市場規則來確定。而現實的情況卻往往是國企高管在雙重利益之下“腳踏兩只船”,不僅在級別上和部級、局級、處級、科級等行政稱謂掛鉤,而且其薪酬收入也與國際接軌,甚至出現了“天價薪酬”的個別現象。
近日,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牽頭進行的針對央企和國企高管收入的調研顯示,208家上市國企發布的2012年年報中,在192家國企董事長或總經理中年薪超過200萬元的有十多位。國企高管在享受行政級別的地位、待遇、權力的同時,也享受著市場名義下的高薪酬,“行政級別”和“高薪收入”的雙重利益,讓眾多腳踏官場和商場兩只大船的國企高管欲罷不能——而這對于其他社會成員來說,卻極不公平。
對于國企高管而言,薪酬的高低或許并不重要,因為企業高管更多關心的是他們的行政級別和待遇,仕途上的晉升才是他們的“小命根兒”。雖然國企高管表面上的收入水平不及同行,卻能同時擁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待遇,而與同級別的公務員相比,他們的年薪又堪稱“天價”,可謂名利雙收。
然而,國企高管們“一腳踏兩船”的現象卻很難得到改變。2007年,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網通與中國聯通交叉“換帥”;2008年,中電投、國電集團等電力巨頭間也進行了人事調動;2011年,石油公司高層也進行了“互換”,中海油總公司原黨組書記、總經理傅成玉調任中石化集團掌門人,中石油集團原副總經理王宜林調任中海油接替傅成玉。顯然,競爭企業間的職務變化絕非市場邏輯所能夠解釋,完全脫離了市場高管職務變化的范疇。對于這些“現實讀本”,青年經濟學家、中央電視臺財經評論員許一力一語中的:國企高管從薪酬到職務都受到行政指令的巨大影響,根本無法通過“職業經理人”的市場化標準予以業績考量。“職位,上級任命;工資,自己決定”,正是國企高管雙重利益的現實寫照。許一力認為,去行政化是為國企引入新鮮血液的關鍵,只有讓更多的職業經理人進入國企和央企并使其起到決定性作用,終結國企對行政主導的過度依賴,才能把國企打造成為“大而強”的現代企業。
“去行政化”恰逢好時機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細胞,企業的質量決定整個經濟的質量,企業的競爭決定整個經濟的活力。因此,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如何使企業成為獨立而平等的主體一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十二屆三中
全會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任務,提出“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規范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的權責,完善企業領導者的聘任制度”。正是因為有了這樣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判斷,并依此切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發展的措施,企業的種類和數量才不斷增加,并持續推動著財富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
在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賴德勝看來,目前國企“去行政化”的問題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而且這還會導致以下多方面消極影響:
一是不利于公平競爭。企業沒有大小之分,只有強弱之別。不論是世界五百強還是中國五百強,企業之間的地位都是平等的;由競爭而入“強”,過程也必須是公平的。但由行政權力“安排座次”,賦予不同企業高低不等的行政級別,就等于將不同企業置于不同的起跑線上,那些級別高的企業自然處于更有利的位置,這顯然有悖公平原則。而如果競爭不公平,市場經濟的整體效率也就無從談起。
二是不利于創新。我國經濟增長進入了“換擋期”,未來要維持一個較高速度的增長,就不能再單純依賴大規模投入,而必須依靠創新。國有企業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級別,會阻礙其進行創新。原因很簡單,企業行政級別特別是較高的行政級別,意味著擁有更多的資源,甚至能獲得某種行政壟斷的特權,這減少了企業創新的動力。
同時,給管理者冠以行政級別,意味著他是由上級任命的,他的提升與發展主要取決于上級的偏好與滿意度。因此,他會想盡辦法獲得上級領導和組織的好評,企業自身的發展則往往被淡化,從而減少管理者促進企業發展的創新動力,相反,探究為官之道的動力倒是很足。這也是我國國企高管貪污腐敗時有發生的重要原因。
三是不利于企業家階層的形成。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重要推動者,根據熊彼特的理論,企業家也是創新的重要推動者。但企業家與官員畢竟屬于不同的階層,雖然“商、官”可以轉換,而且在轉型階段,這種轉換有利于官,也可能有利于商,但在一種身份內,則要在官言官,在商言商。國企管理者有行政級別,則意味著他既商又官,官商兩種身份合二為一,則難免會發生角色沖突。
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的、法治的市場經濟。在其中,企業不管規模大與小,都是平等的,是沒有高下之分的。因此在當下,國有企業去行政化就顯得尤為緊迫。實際上,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就已明確提出過“去行政化”的具體要求,但十多年過去了,國有企業行政化仍很普遍。令人欣喜的是,正在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國企“去行政化”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全國上下對進一步深化改革也達成了高度的共識,社會各界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出臺的改革方案更是充滿期待。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讓國有企業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級別退出歷史舞臺,阻力相對來說會比較小,從而真正將書面決定轉化成現實行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深化國企改革作為重點之一,正是抓住了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我們不妨先從理順國企內部的各種復雜關系入手:國企是獨立法人,是市場經濟的一個細胞,卻按照行政機構套用行政級別,國企董事會成員和高管層按照行政官員套用級別待遇。這種關系最大的矛盾在于:國企老總在薪酬待遇上按照市場化的企業標準要求與國際接軌,拿著天價年薪,卻仍按照行政級別戴“官帽”。
知名財經評論員余豐慧認為:深化國企改革的第一步,就應該從廢除國企高管的行政級別待遇和國企行政級別開始,使國企真正成為市場經濟主體而不附帶任何行政色彩,真正依靠市場競爭而站住腳,與其他市場主體平起平坐,這將有利于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取消國企高管行政級別,徹底切斷其行政官員級別待遇的后路,一方面能使得國企高管一心撲在企業上,背水一戰、心無旁騖地把企業搞好;另一方面,也可讓民眾對其擁有的高薪待遇普遍接受,同時也為國企高管徹底實行面向海內外的市場化招聘奠定基礎。
當然,從根本上深化國企改革還需要繼續完善企業內部股權結構,按照市場化改革原則,讓國有股份逐步從國企撤出,才能使國企真正成為完全的“市場細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