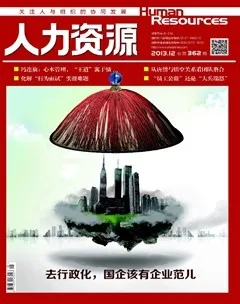利益之鏈,當斬則斬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表述擲地有聲。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權”和“利”之間徘徊的國企,如今該摘下這頂“官商不明”的烏紗帽了。
“天價招待費”的背后
在2012年上市公司年報中,一份關于招待費和會務費的報告清單格外顯眼:11家企業業務招待費過億元,其中10家為央企,業務招待費最高的為中國鐵建,高達8.37億元,同為國企的中國交建和中國水電分別以7.80億元和3.43億元緊隨其后。相比逐年激增的招待費,部分國企和央企的經營狀況卻開始在悄然之間顯出頹勢。該份年報顯示,上市的國企、央企包攬了2012年上市公司巨虧榜前十位,合計虧損近500億元。一方面是逐年遞增的招待費數額,另一方面卻是財報數據巨虧和巨額高管年薪問題的不斷曝光,讓人們不得不產生質疑——國企開出的“天價招待費”,究竟“招待”了誰?
一位曾與基層鐵道建設系統打過交道的人士透露,鐵道建設單位與基層政府維系關系的“武器”就是請客吃飯,甚至是“鐵路修到哪里,就得請到哪里”。國企“天價招待費”本質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公款吃喝”,這不僅僅關乎面子排場,其背后還存在著半公開的腐敗和巨大的利益鏈條。然而,作為一項既可能涉及官員貪腐、又可能涉及企業是否合法經營的重要事項,業務招待費其實是一個公共事項,而非私人事項,對于獨攬公共資源的國企來說更是如此。“天價招待費”究竟有多少最終變相裝進了私人腰包?當吃吃喝喝滲透到權力的運行過程時,公共權力是否已經淪為金錢的奴隸?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強調政企、政資分開、市場化道路與社會責任”的論述,以更加堅決的態度,昭示著國企與政府及其他利益群體之間的鏈條已經到了應立即斬斷的時候了。
利益鏈從何滋生
集體利益的固化。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一些歐美老牌名企慘遭破產或收購,我國的民營企業也是舉步維艱,唯獨通信、石油等領域的央企依然“衣食無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稱,國企仰仗著得天獨厚的行政優勢占據市場,逐漸演變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其發展依托兩個優勢——壟斷和資源。
不僅如此,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對行政、制度、金融等資源形成了強烈的依賴,對巨額的國有金融資本運營更如同“暗箱操作”,誰也摸不清公共部門整體上的國有金融資本規模、收益和風險狀況。民建湖南省委參政議政委員會委員楊孟著認為,國企利益鏈條不斷被相關政府部門以設定特許經營、行業準入等行政壟斷的形式日益維系和強化,已經變得堅不可摧,牢不可破。
高管的既得利益。2010年的一項統計表明,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現任官員作為公司高管的總數占A股全部高管總人數比重的5%。201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涉足鐵路產業利益鏈的33家上司公司高管中,有37名曾在鐵道部或其他政府部門任職。許多高級管理層都采用行政與職稱“雙跨”的薪資待遇模式:行政方面漲工資時一次不落,職稱方面加薪時分毫不少,并且在養老、住房、醫療等方面享受國家相應級別干部的待遇。
在利益鏈的庇佑下,少數帶有行政職級的干部一方面經營著自己的私營公司,同時又在國企掛職。今年
8月有媒體爆出,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13名核心管理人員在十年前偽造退休或辭退證明并注冊私營公司,然后假借國企之名騙取合作公司的信任,跳過審批程序完成轉讓。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這十年期間,其中有8人還在國企中得到職位晉升,獲得財富和仕途“雙豐收”。這類漏洞百出的“操作”,如果沒有原持股國企的默許和上級監管機構的選擇性“失明”,恐怕未必行得通。近些年來,越來越多國有資產違法吞并案件的曝光,不禁讓公眾對行政、監管、科研等機構與國企之間的利益關系浮想聯翩。
無法回避的副作用
國企滋生惰性。在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員工手捧著“鐵飯碗”,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愿主動參與市場競爭,不愿打破現有的穩定局面。長此以往,無論是基層員工,還是領導決策層,都在求穩和拒變的過程中滋生出了惰性。然而,對國家補貼的過度依賴、盲目拓展業務范圍、管理人員占比高、生產成本高于業內平均水平等都會迅速將國企逼入虧損慘境,這充分說明國企在經營中存在兩大劣勢:一是內部運作體系不夠市場化;二是對外部變化適應性較差。同時,與民企相比,國企在裁員方面的空間很小,缺乏成本調控能力和績效考核機制。
民企無路可走。2010年,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鼓勵、支持和正確引導民間投資。然而,殘酷的現實卻給非國企,尤其是民企當頭一棒:山西煤炭民企被煤炭國企整合并擠出市場;河北鋼鐵民企被重組擠出鋼鐵領域……楊孟著表示,國企與民企之間超過2/3的收入差距完全是靠國企的壟斷地位及其相應的壟斷利潤帶來的,這兩者發展的不平衡,對我國經濟效率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十分不利。
身為民營企業管理者的福建鑫垚貿易集團總裁余榮鵬對民間金融創新活動遭受的歧視性待遇深有感觸:“融資難,市場準入難,都是擺在民營企業面前的生存難題。同樣是企業,銀行會認為國企貸款風險小。我們去銀行貸款,就算用土地和資產抵押也不行,非讓我們再找個擔保公司做擔保。”對于余榮鵬這樣的民企管理者來說,他們最渴望的是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擁有與國企同等的項目、資產、信用條件,因為企業歸根結底都是在為社會和人民創造財富。
斬斷利益鏈重在走市場
近年來,頻繁發生的礦難為政企之間的利益鏈條增加了一道帶血的疤痕。礦難的發生范圍,從黑煤窯、小煤窯、民營煤窯向著國營煤礦擴展。煤炭產業背后巨大的利益鏈條,讓克扣礦工工資、在安全生產環節千方百計減少投入等方式成了某些煤炭企業獲取暴利的捷徑。與利益鏈相伴的,還有一條權力鏈——資源決定著權力的分配。這種鏈鏈相扣的情況不僅出現在煤炭產業,也存在于國民經濟的其他關鍵領域中。今年8月底中石油四名高管的先后落馬牽扯出國資委相關官員的嚴重違紀嫌疑,還有中儲糧窩案、中國移動腐敗窩案等案件的曝光,都揭示出國企“大一統”的管理體制和金字塔形的治理結構造成的高管權力過度集中。而個別相關政府管理部門與掌握壟斷資源的國企依靠行政資源進行的“官商勾結”,正是權力異化的體現。
數年前,原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中山大學演講中“國企沒搞好,責任在政府,不在企業”的一番話,讓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室主任楊濤感想頗多。在國家和政府推動國企改革時,既要防止“國進民退”中出現利益集團的阻力,又要防止“國退民進”中產生權貴階層。在楊濤眼中,斬斷利益之鏈,進行國企去行政化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楊濤認為,首先,國企管理和去行政化的關鍵,在于創造寬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使各類企業健康成長,最大限度地激發生產力。除少數公益性國企之外,盡可能減少國企無償或低成本掌握資源、享受特殊政策的情況,杜絕利益集團的暗箱操作,逐漸為所有企業創造一個公平有效的競爭環境。
其次,應在政府與國企關系之外,構造更加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管理機制,如引入立法機關的監督和約束,對國企管理者的選擇和運營情況進行直接監控,避免政府的直接干預和影響,將國企的運營情況向利益相關的公眾進行公開,讓國有資產的不法操作遁于無形。
最后,公眾之所以對國企“天價招待費”等問題產生質疑,很大程度在于他們很少能直接感受到國企紅利的回報。對此,還應該加快中央和地方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完善,使得國企利潤的合理部分能最終用到與公眾切身相關的就業、養老等領域,讓公眾真正享受到國企利用自然壟斷使用公共資源所創造出來的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