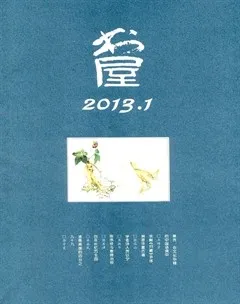酒令的演變
歷史進步,時代前進,社會發展,一切都處在丕變之中。以小者言之,古代麻衣褞袍,如今皮爾·卡丹、比基尼;古代牛車、木牛流馬,如今奧迪、寶馬……不過,筆者愚見,人生中最重要的食物,仿佛變化的幅度不大,程度也不深,變不離宗而未曾有質的飛躍。例如,“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欲”,如今,我們仍然安享他老人家的恩澤,面食如饅頭,專家說不晚于晉朝,有《晉書·何曾傳》為證;宋朝高承《事物記原》說,是諸葛亮征孟獲時發明。而今,大米饅頭仍是平民化的主食。至于菜和酒,則是愈早愈值錢。滿漢全席的價格一聽就讓人頭皮發麻,如果哪天開發出明皇貴妃的飲宴菜單、秦皇漢武登極的慶典食譜,那價錢,怕是一個小縣全年財政收入也對付不了的。酒呢,記得媒體報道過,某地發現道光年間的窖藏酒,在北京拍賣是每公斤六萬!洋酒更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拿破侖,聽人說,小杯上千元!還聽人說,法國名酒最大的買主,是咱們中國。
說到酒,那就把話拉回到題目上來。古今酒令的功能,是翻了燒餅。酒令之興,原是限制飲酒的。西周初年,鑒于商朝統治者溺酒亡國的教訓,由周公以王命發布《酒誥》禁酒。“群飲,汝無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哇塞我的媽,飲酒者居然處以極刑!然而,美酒的誘惑在宏觀上是禁不了的,于是只好在微觀上設令限制。《詩經·小雅·賓之初筵》中的“立之監”、“佐之史”,就是三千年前執行酒令、監督飲酒的專職干部。那時的酒令,想來不外乎“少喝點”、“只許舔一下”、“當心酒后失德”之類,完全是后來以酒令來勸酒、罰酒的一種反動。
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社會風習也隨之變化。反映在飲宴上,是酒令成為助興的主要方式。清人陸以湉《冷廬雜識》卷四《酒令》說:“蔡寬夫《詩話》謂:‘唐人飲酒必為令,有舉經句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云云。余嘗與友人宴飲效此為誦,僅得二句,曰‘山出器車’,曰‘一二臣衛’。”如果宋朝蔡寬夫的記載屬實,則唐人飲宴時行令已屬常態。只是,這“舉經句相屬而文重”的要求近乎苛酷:“炎”是“火”的重疊,出自《尚書·胤征》:“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圭”是“土”的重疊,土圭是玉器,用以測日影,《周禮·大司徒》:“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正日景(影)以求地中。”這種酒令,連陸以湉這位道光十六年的進士都覺得玩不轉。
雖然勸酒、罰酒的酒令至少始于唐朝,但文采燦然卻是明、清。文人學士們把飽讀詩書、泛覽雜籍的學風移植到飲宴上,使其郁郁乎文哉,讓吃喝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形成斑斕的吃文化、酒文化。同時,它還體現出一種考核機制,答不上么,那就罰一大杯,浮一大白。
明人周玄暉《涇林續記》里記三位縣令級干部相逢,宴筵上施酒令,應答不上罰巨觥。時旭日東升,縣令甲見景出詩:“東方日出三分白,日落西山一點紅。北斗七星顛倒掛,牽牛織女喜相逢。”縣令乙望著池中荷花,吟道:“一灣流水三分白,出水荷花一點紅。映水蓮房顛倒掛,鴛鴦戲水喜相逢。”眼前景色都講了,縣令丙被卡,尷尬間,聽門外鑼鼓聲,命門子打聽,回報是鄉人娶婦。當下靈感來了,縣令丙誦曰:“村里婦人三分白,口上胭脂一點紅。兩耳多環顛倒掛,洞房花燭喜相逢。”于是和平飲宴,無攻伐之舉。詩人袁枚頗先鋒頗新潮,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居然大膽招收女弟子。他在《隨園詩話》里記有女弟子飲宴時的酒令:一句宋詩,一句曲牌,要文義關合。出令:“閑看兒童捉柳花,合手拿。”對曰:“有約不來過夜半,奴心怒。”看似平實,其實要求嚴格:“合手”組成“拿”,“奴心”組成“怒”。
極富文化氛圍的達官貴人的筵席上,酒令更豐富、更精彩,也更嚴格。《紅樓夢》第六十二回里,史湘云出令:一句古文、一句詩、一句骨牌、一句曲牌名、一句時憲(歷書)上的話,最后以筵席上的一件物品結束。乖乖隆地隆!六句話,一句一道關,真夠損的。而且,還要熟悉打牌賭博業務。寶玉被難住了,張口結舌答不上來。林妹妹為心中的白馬王子解圍,應道:“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天高過雁哀,卻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腸,這是鴻雁來賓。”說完,從席上拈起一個榛子,謂:“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K5IaKeFJHW/i62nIRcCqbzYhIDRQZ6+jjgJlasQH+Gc=戶搗衣聲。”這套酒令的前五句,依次為:王勃文、柳宗元詩、骨牌“折足雁”、曲牌《九四腸》、時憲書引《月令》之“鴻雁來賓”,全圍繞“雁”來汰選句子;“榛”與“砧”同音,引出李白《子夜吳歌》的句子,時令點出“秋”,與“雁”諧和。天王老子地王爺!這樣的酒令,非滿腹詩書、思維敏捷是答不上來的。
鄙俗之輩的酒令則是另一番面目。深度洞察社會、體味人生的曹雪芹也有所描寫。《紅樓夢》第二十八回寫薛蟠的酒令:“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唱的則是“哼哼調”:“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疑似涉黃、少兒不宜的一句在此不錄。曹雪芹的現實主義創作,使我們得知當時酒令是風雅與鄙俗甚至下流并存。這是人類文化素質、人格秉性多重化,社會生活、情趣愛好多元化的體現。
道光、咸豐年間的梁章鉅,在《歸田瑣記》里記下了某些“雅而謔”的酒令。其一是張更生與李千里對酌,李出令:“古有劉更生,今有張更生,手中一本《金剛經》,不知是胎生、是化生、是卵生?”張回應:“古有趙千里,今有李千里,手中一本《刑法志》,不知是二千里、是二千五百里、是三千里?”筆者翻檢了工具書,方知西漢劉向,原名劉更生;明末趙之琰,原名趙千里。腦子里能貯存這些信息并隨時調遣出來,真所謂“謔”了。稍后的梁紹壬,在《兩般秋雨庵隨筆》(此書前些年有新版,封面標明“毛澤東最珍愛的書”)中記的酒令,是要用《詩經》中的句子合成花卉名:“宜爾子孫”、“男子之祥”合成宜男花(即萱草,傅休《弈賦》:“花應宜男,本應禎祥”);“駕彼四牡”、“顏如渥丹”合成牡丹花;“不以其長”、“春日遲遲”合成長春花等。嗚呼,古希臘的柏拉圖曾在學院張貼告示:“不懂幾何學者免進”;不熟讀《詩經》和《群芳譜》的賓客,入這等宴席只能是被灌得酩酊大醉!至于鄙俗酒令,這二位梁兄深入生活恐不如曹雪芹,未能記下一句。
這種宴席上的文化,民國初年猶有余韻。民國四年上海章福記書局石印本《寫信必讀》里,專有一章《賓筵酒令》,分酒令為八類。如赴試令其中之一,是要求“一句鳥,二句物,三、四句切題押韻”。對曰:“飛鳴本是孤雁,聲大一似銅鐘,愿得此行名姓顯,共看攀桂步蟾宮。”又如慶賀令其一要求“一句內兩個詞(曲)牌名,二句為古詩”。對為:“銷金帳里訴衷情,夜半無人私語時。”當然也有一些低下的,如要求前為骨牌名、后為《千家詩》中句,答稱“臨老入花叢,將謂偷閑學少年”。這反映了十里洋場中文士冶游于秦樓楚館的某種實況吧?
但畢竟時代、社會不一樣了,宴飲者的學識秉性、社會理想和人生態度也不一樣了,酒文化的內涵和表征也就不一樣了。席間字令少了,多為劃拳,以數字助手勢來勸酒,如“一枝花”、“兩面光”、“三生石”、“四季美”、“五魁首”之類。飲酒速度加快了,飲宴時間縮短了。這是不是也反映了農耕社會恬然慢節奏與現代社會浮躁快節奏的區別呢?短短酒令,實為社會風習的一個縮影;賓客的言行舉止,則從一個側面顯示了社會上特定階層的素質和秉性。
新中國成立后,酒令銷聲匿跡;家庭喜筵、單位會餐,也只是祝辭。近些年來,吃喝特盛,酒風尤熾。事必“研究”(煙酒)、人需“久經考驗”(酒精),且“革命就是請客吃飯”,而有的單位提拔要看“三平”(文憑、水平、酒瓶)。在這種外部條件下,酒令居然“春風吹又生”了。時下,飲酒之道精深無比,勸酒之術、賭酒之法不斷翻新。酒令躬逢其時,發揮出巨大潛能。開席甫始,直奔主題;酒則大口,言則狂呼。不能淺酌低吟,酸文醋詩滾蛋。“交情淺,舔一舔;交情深,一口吞”。接下是“雙杯為敬”,繼之“哥倆好,三杯少”,連著“生意興隆,四季發財”。不勝酒力想逃席是辦不到的,“天大地大不如喝酒事大,爹親娘親不如酒友親”。
酒為財媒人,賓宴多為利益關系。三千年前是“立之監”、“佐之史”在旁限酒,現在則是“巧笑倩兮”的“螓首蛾眉”在旁勸酒。薛蟠的“哼哼調”如今也“茍日新”了,赤裸得可以。“一二三四五,不喝打屁股”。真能讓妙齡女子打屁股?只好舍命陪君子,喝!也有席上出古詩詞為令的,對句卻是逸興遄飛。如有以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之“鳳凰臺上鳳凰游”為令,若大學畢業的陪酒女郎對“鳳去臺空江自流”,那么,肯定滿座為之不歡。這女郎,定被視為“紅樓夢”中不識繡春囊為何物的傻大姐一類。若女郎應聲“一公一母頭挨頭”,則立馬滿席喝彩,氣氛更為熱烈,賓客更為歡心,老板更為滿意。世風如此,無可奈何。
聽說近年來,有大學生“挽狂瀾于既倒”,致力扭轉酒風,在酒令中增加文化成色。如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對“此處省略三個字”(趙本山小品詞);又如“天蒼蒼,野茫茫”,對“我十分想念趙忠祥”(宋丹丹小品詞);再如“白日放歌須縱酒”,對“妹妹你大膽往前走”(歌詞);還如“床前明月光”,對“我爸是李剛”(網絡熱門語)等。一句古詩詞,一句社會流行詞語,這種雅趣式的調侃,也許吻合消費文化的題旨吧?
國慶長假,上街閑逛,見一路賓館家家爆滿。吆喝聲破窗而出,嘈雜中隱約聽見“一杯少哇”,“兩相好哇”,“三結義哇”……心想這是行酒令了。回家后,寫下這篇《酒令的演變》,聊記心中之感慨云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