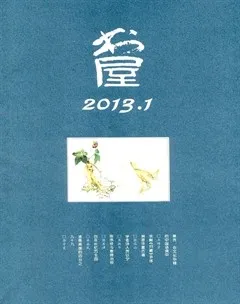鄧石如對歐、蘇文賦的膜拜
鄧石如(1743—1805),原名鄧琰,字石如,后因避嘉慶皇帝颙琰名諱而以字行,更字頑伯,其號有完白山人、完白山民、古浣子等多個。鄧石如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在篆刻領域更是獨樹一幟,“印從書出”,他以擅長的小篆入印,使刀如筆,形成剛健婀娜的獨特風格,開創了鄧派篆刻,在當時印壇上與皖、浙兩派鼎足而三。
翻覽鄧石如印譜,人們會為他匠心獨運構造出來的方寸天地、朱白世界而癡迷。其中兩方印面頗為碩大的印章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一方為“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另一方印文為“新篁補舊林”。對這兩方印的解讀,可為理解歐陽修、蘇軾的文賦名篇在后世的傳播與影響,提供獨特的視角。
一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這方印的印文,讀者比較熟悉,句出蘇軾《后赤壁賦》。該印刻有一段篇幅較長的邊款,云:“一頑石耳。癸卯菊月客京口,寓樓無事,秋多淑懷,乃命童子置火具,安斯石于洪爐。頃之,石出,幻如赤壁之圖,恍若見蘇髯先生泛于蒼茫煙水間。噫!化工之巧也如斯夫。蘭泉居士,吾友也,節《赤壁賦》八字,篆于石贈之。鄧琰又記。圖之石壁如此云。”
此款語言寫得精致之極,我曾把明清以來印章邊款上的文字,戲稱為“電文式”的小品文,或許能夠比較形象地描述邊款文體的形制特征。
讀此邊款后,我恍然大悟,原來這方曠世名印的靈感,竟來源于頑石火灼后幻出的紋理。按照常理,一方印章的產生,往往是事先有了想刻的印文,然后再據印文內容刻制邊款。但鄧石如此印卻非如此,可謂擺落一切預設目標,達成天機爛漫的境界。我們依循他在邊款中所述的內容,稍稍還原歷史場景。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的某一天,四十一歲的鄧石如正客居京口,“寓樓無事,秋多淑懷”,不禁起刻石饋贈友人之意。或許是手邊的這方石頭太過稀松平常,以致只能目為“頑石”,難于就刀,也羞以贈人。但世間“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蘇軾《超然臺記》)。鄧石如突發奇想,將這方頑石放到烘爐上灼燒,有如鴻蒙初開時,女媧欲補天裂,也是以火燒煉五色石。頃刻之間,石中的礦物成分發生了高溫反應,可以想象,在烈焰中,有的地方顯出裂紋,有的地方則變為赤色。印石上呈現的圖景,讓鄧石如想起了赤壁,于是恍惚若見須髯飄飄的東坡先生正泛舟赤壁之下,置身蒼茫煙水之間。靈感醞釀及此,一切都已水到渠成,遂節取《后赤壁賦》中“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八字刻到印面上。因此,此印的制作,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從最初的茫然一片,不知刻什么為好或者說隨便刻什么都好,到現實中的頑石經火燒之后幻化出來的紋理圖案,再到想象的赤壁圖以及東坡赤壁之游,最后轉為援引歷史上的文學經典入印,由實而虛,又由虛而實,一片神行之氣往來今古,是藝術創作過程中思維跳躍的絕佳案例。
但如果考慮得更多些,我們不妨設想,鄧石如此時正居住在長江邊的一個樓上,臨近江邊的地理環境,是否也正是“江流有聲,斷岸千尺”?放眼現實中的一切,是否也給了他某種觸動,引領他將思維的觸角,伸到歷史的經典場景——黃州赤壁與經典文本——東坡《赤壁賦》中去?這樣的疑問,并非庸人自擾,它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鄧石如印章與東坡名篇之間的物類感應關系。
如果細心,我們還會在鄧石如這方印的邊款上注意到一個圖形密碼以及一句解碼的提示語。從拓片看,該印的邊款文字顯是經過斟酌刻意編排出來的,從右往左,每行文字占據的長度逐漸增加,形成一個狀如“◤”的圖形,而這在視覺上給人的恰恰是危崖絕壁的直觀印象。若比對古人筆下的繪畫,無論是宋人李嵩還是明代仇英、文徵明的《赤壁圖》,便可知這樣解碼,并非全無根據。而且更為有力的證據是,鄧石如在最后另行加刻的幾個字“圖之石壁如此”,則直接提示了我們解讀的方向。因此,這方印,邊款形式、灼燒后幻化出的圖景以及印面文字,從外觀到內涵,都彼此關聯,有著鮮明的互文性,共同構成一個意義完整的統一體,昭示著東坡文學經典的巨大影響力。
二
如果說“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印與東坡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是顯性的話,那么,“新篁補舊林”印則是對歐陽修《秋聲賦》的隱性依傍。
此印也是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秋天,地點也在京口客寓中,兩印屬同一時期作品。此印印文,句出元代詩人高啟《過戴居士宅》中的一聯“高樹藏卑屋,新篁補舊林”,是應他人所求而刻。按理說,該印與歐陽修《秋聲賦》之間,無論如何也不存在聯系到一起的必然性。但高明的藝術家,其思致之跌宕跳躍,必能迥出流輩,而在無數可供選擇的古代名人與古代經典文本中,鄧石如的選擇也就特別見出意義了。
該印邊款云:“癸卯秋末,客京口。梅甫先生屬作石印數事。時風聲、雨聲、潮聲、濤聲、欸乃聲與奏刀聲,相奔逐于江樓。斯數聲者,歐陽子《秋聲賦》中無之,爰補于此石云。古浣子鄧琰記。”
歐陽修在《秋聲賦》中以秋聲為線索,寫出山川寂寥、草木零落的蕭索景象,文章一開篇即對秋聲進行一番生動的描摹:“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于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
歐陽修秋夜讀書,聽到由遠而近、由靜而動的秋夜奇聲,一片悲涼的氣氛登時彌漫開來。在那個絕少噪音污染的古代社會,人的耳朵與心靈顯得格外敏感、敏銳,再細小的聲音都仿佛放大了無數倍。當鄧石如刻制“新篁補舊林”印時,窗外傳來各種聲音,風雨打窗聲,潮水拍岸聲,以及江中行舟的欸乃聲,這些聲音與他刻印章時石頭砉然崩裂的奏刀聲混雜一起,包圍著樓中的他。時當秋末,秋氣正深,于是鄧石如不由想起歐陽修的《秋聲賦》,并很快得出一個書生氣十足,甚至有點較勁好勝意味的結論:“斯數聲者,歐陽子《秋聲賦》中無之”,所以要補歐《賦》秋聲之不足。而這些轉瞬即逝的聲音,如何才能留住,如嘉祐四年(1059)那個夜晚歐陽修“悚然而聽之”的秋聲一樣,千載而下,猶在讀者耳際?以鄧石如篆刻家的身份來說,最佳的途徑就是化為文字,刻到石上。“爰補于此石”后,一時的經驗與感悟便凝固為永久的存在了。平情而論,鄧石如所說的幾種聲音,除欸乃聲與奏刀聲之外,其他的,《秋聲賦》中“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一句即能全部涵蓋,只不過歐是虛寫,是作為秋聲的喻體存在,而鄧是實寫,是直道眼前景。但是,我們絕不會因此認為鄧石如此舉為多事,他欲以親身體會來對歐陽子《秋聲賦》作增補,恰足以反映《秋聲賦》作為一篇經典之作,在他心目中的分量。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歷經時間的淬煉,最后成為“召喚文本”。《秋聲賦》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無比向心力的召喚文本,吸引著鄧石如,成為他身心感受的坐標系,哪怕是以挑剔的眼光、不滿足的心態去對待,證明的結果也只能是這個召喚文本的內蘊是多么無窮,而無從削弱其影響的磅礴力量。含而不露的膜拜心理,較之對待東坡《赤壁賦》顯豁的遙想傾慕,更能引起我們的同情之了解。西方文藝批評中有所謂“影響的焦慮”之說(哈羅德·布魯姆),鄧石如印款反映出的對待經典的心態,可視為一個有趣的例證。
三
進言之,了解鄧石如生世遭遇的人,都深知鄧早歲之孤貧坎坷,以至一度“販鬻餅餌以給饘粥”(李兆洛《鄧君墓志銘》),一生狷介高潔,藤杖芒鞋,僅以布衣終其身。中年后雖有梁巘、梅镠、金榜、畢沅等聞達之士賞識、照拂,尤其是客居金陵梅家的八年,更得主人“為具衣食楮墨,使專肄習”,孜孜于“金石善本”的研求(《清史稿·鄧石如傳》)。但畢竟是落得個寄人籬下、托身富門的地步,他的心靈人格,又何嘗能夠以此為樂事?《清史稿》記載了他晚年的一樁事跡,可見其不款曲、無媚骨的性格:“時京師論篆、分者,多宗內閣學士翁方綱。方綱以石如不至其門,力詆之,石如乃去,客兩湖總督畢沅。沅故好客,吳中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石如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
鄧石如以不知逢迎惹怒翁方綱,招致詆毀而出京。畢沅(字秋帆)與翁氏不同,他生性儒雅和易,在當時即有“愛才尤篤”的美譽,“人有一技之長,必馳幣聘請,唯恐其不來”(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卷四《書畢宮保遺事》)。他能以寬容的心態接受我行我素、不改狷狂本色的鄧石如,但鄧石如最后還是選擇毅然辭歸。怪不得畢氏以“山人,吾幕府一服清涼散也”的評語贈行,可謂形象之極的知心之言。狷介骨鯁的背后,其實是對世道人心有著深刻體察而有所堅守,有所不為。古往今來,有這般性格的人,大抵皆難免落落寡合,感受到他人無法感知的孤獨與悲涼。我們知道,歐陽修、蘇軾二人正是這等人物。我們曾讀過這樣的文字:當歐陽修喃喃獨語,面對虛空的秋夜,大發關于秋聲的感慨,深沉的苦悶悲哀彌漫字里行間,故作的解脫與振作,終究顯得蒼白,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童子天真爛漫的回答,以及最后“童子莫對,垂頭而睡”的憨態可掬;蘇軾謫居黃州,以醉消愁,待三更時分歸來,迎接他的是“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的尷尬,只得在門外倚杖傾聽滾滾而逝的江聲,暫時被酒意消釋的煩惱再次生起,捫心自省“何時忘卻營營”,結句中“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自我寬慰,同樣不免單弱無力之嫌,曠達掩蓋不住傷感(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這些飽讀詩書肩負道義,“為文化所化”的大人物只贏得一腔愁緒與滿肚皮的不合時宜,惟未曾開蒙、無知無識的童子,方得無憂無慮。
我們注意到,鄧石如的印款中也出現了一個童子,他曾幫助主人置火具,灼燒頑石。可以想象,當鄧石如寂坐江樓奏刀刻印,突然意識到“風聲、雨聲、潮聲、濤聲、欸乃聲與奏刀聲”為“歐陽子《秋聲賦》中無之”而思接千載、萬緒紛然時,那個童子可能早已忍不住哈欠連連,垂頭而睡,甚至鼻息雷鳴了吧!
鄧石如刻下的這兩方印,若放置到這樣一個意義上詮釋、解讀,或許才能抉發其更深刻的內涵。而歐、蘇二人的文賦經典,在后世茫茫人海中贏得的一個遙遠而精彩的回響,也才能穿透歲月隔閡,不致湮滅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