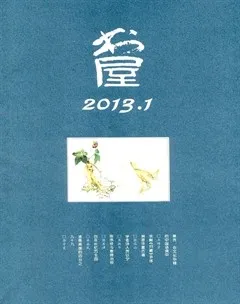上世紀三十年代文人知識分子隨想
(一)
1937年3月1日,出版于武漢的《奔濤》(半月刊)雜志第一期,發表了兩個名人的通信。一個是被郭沫若諷刺為“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代言人”的“圣人”胡適之,另一個則是五四時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后又以痛罵魯迅為職志的蘇雪林。在這篇《關于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通信中,兩人就已經持續了十余年的左翼文化風潮發表各自看法。
蘇雪林捍衛“黨國利益”,痛心疾首于“赤焰大張”,慫恿胡適出來主持“正義”,扭轉時局的“左轉”傾向:
五卅以后,赤焰大張,上海號為中國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較聞名的作家無不沾染赤色思想。他們文筆既佳,名望復大,又慣與出版事業合作。上海除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幾個老招牌的書店以外,其余幾乎都成了他們御用出版機關。他們灌輸赤化從文學入手,推廣至于藝術(如木刻、漫畫)戲劇電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文化;甚至教科書的編制,中學生的讀物,也要插進一腳……先生等在五四時代辛苦造成的新文化,被他們巧取豪奪,全盤接收了去,自由享用,不但不感謝先生,還要痛罵先生呢。先生恬淡為懷,高尚其志,本不屑同這些人爭奪什么“思想領袖”、“青年導師”的頭銜,不過目睹千萬青年純潔的心靈,日受叛國主義(君衡先生語)的熏染,能不痛心?現在政府雖還不合我們理想的標準,但肯作平心之論的人,都承認她是二十五年來最好的一個政治機關。她有不到處,我們只有督責她,勉勵她,萬不可輕易就說反對的話。我讀先生著作,知道先生對現政府的態度,正是如此。
曾經滄海的胡適之,可不是“逼上梁山”的“黑旋風”。他自有亂云飛渡的仍從容:
關于左派控制文化一點,我的看法稍與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傾,并不足憂慮。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只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并不足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產生一些好文字。我們開路,而他們做工,這正可鼓舞我們中年人奮發向前。他們罵我,我毫不生氣……我總覺得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氣候。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對左翼“成不了什么氣候”的不屑一顧,對時局的處驚不變和樂觀判斷,對“黨國”的惺惺相惜,是因為胡適相信“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
此時的胡適,已非五四時期光芒四射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了。自從發起那場也曾慷慨激昂的憲政運動,經歷了人權與約法、民主與獨裁的論辯硝煙,曾經的“侮辱本黨總理,詆毀本黨主義,背叛國民政府,陰謀煽惑民眾”的“反革命之胡適”,已經和那個“盧梭第二”的風采漸行漸遠;已經由大義凜然的抗爭,漸漸忍耐和認同“以黨治國”的“訓政”,成了黨國“救焚”、“補天”的諍友;不但對左翼的痛罵“毫不生氣”,就是對黨國的獨裁和腐敗只怕也是“老僧不見不聞”了。這是胡適的無奈和聰明,或許還有對體制的一點殘存期待。
其實,蘇雪林如果還自詡為一個獨立的文人知識分子,她就應該問問青年人,為什么不再擁戴胡適而追逐左翼風潮?問問她心目中那個“最好的政治機關”,是否有容忍胡適提倡“憲政”的雅量?
蘇雪林一片“擁護現政府的苦心”,真乃日月可鑒。她不久又在3月16日的《奔濤》雜志第二期,發表了那篇蓄意已久、投告無門的《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為“黨國”的危局憂心忡忡:“共產主義傳播中國已十余年,根柢頗為深固。‘九·一八’后,強敵披猖,政府態度不明,青年失望,思想乃益激變,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乃更得勢,今日之域中,亦幾成為赤色文化之天下矣。”
可惜,她心甘情愿當“幫忙”、“幫閑”之壯舉,不但沒有得到“黨國”的授勛頒獎,就是引以為知己和靠山的胡適都不以為然,而且正色相告:那些“罵魯”的“舊文字的惡腔調”,“應該深戒”。
或許蘇雪林知道自己的舉動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她在給胡適的信中大訴其苦:“我不怕干犯魯黨之怒以及整個文壇的攻擊,很想做個堂·吉訶德先生,首加魯迅偶像以一矛。但幾個我素投稿的刊物的編輯人,一聽我要反對魯迅,人人搖手失色,好像魯迅的靈魂會從地底下鉆出來吃了他們似的。一連接洽三四處都遭婉謝。魯迅在世時,盤踞上海文壇,氣焰熏天,炙手可熱,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復如此,更使我憤憤難平了。”
或許蘇雪林真的應該反躬自問:鞭尸魯迅、痛斥左禍的《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為何屢吃閉門羹?為何“罵魯”會導致整個文壇的攻擊?為何不是她蘇雪林,也不是胡適,而是魯迅被擁戴為“思想領袖”和“青年導師”?為何“魯迅雖死,魯迅的偶像沒有死,魯迅給予青年的不良影響,正在增高繼長”?
從歷史的后設視野來看,胡、蘇所探討的“赤焰”風潮,其實已經面臨轉折。嚴峻的國內政治斗爭和文化矛盾,很快就要被殘酷的民族戰爭所轉移,歷史即將由“十年內戰”(又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進入慘烈而悲壯的抗日戰爭時期。
后世的一些歷史學家,通過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和當年胡、蘇所看到的表象近乎一致的結論:“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政權,從而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的穩定。”〔1〕民族經濟尤其是工業經濟飛速發展,GDP增長居于世界前沿;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進入了罕見的“黃金”快車道。然而,不久日寇瘋狂入侵,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此夭折。所以,歷史不能假設,歷史的進程復雜而曲折。當人們的眼光局限于國內時,外患卻在步步逼近。
(二)
1927年8月16日,在上海出版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發表了時有恒的一篇雜感《這時節》。時在文中感慨:“久不見魯迅先生等的對盲目的思想行為攻擊下的文字了”,“我們懇切地祈望魯迅先生出馬……因為救救孩子要緊呀”。
“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2〕,離開革命大本營廣東,剛剛來到上海寓居的魯迅,在是年10月1日的《北新》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上,發表了《答有恒先生》,公開回答自己為何“不發議論”、為何“沉默”:
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以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于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于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并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于凌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凌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后腦上么?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游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一年前,目睹青年學生被北洋軍閥政府屠殺,他感到“實在無話可說”:“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3〕可是剛剛一年的光景,連為北洋政府、為“孤桐先生”搖旗吶喊的“正人君子”們,都“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本來以為“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蕩蕩。”〔4〕但是,“黨國”上臺用以祭旗的血污,讓他目瞪口呆、感到未有過的恐怖,只好用老法子救助自己:一是麻痹,二是忘卻。這種從未有過的恐怖經驗壓抑了一年,“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他也還是只能“而已”而已。
血的游戲已經粉墨登場,好戲還要不斷上演,豈能草草收場?
四年后,他又沉重地感到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黨國”讓他又一次“忍看朋輩成新鬼”。又過了兩年,他才能夠“怒向刀叢覓小詩”:
可是在中國,那時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輕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么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5〕
九年后,在臨死的前兩天,他在生命中最后的未竟稿里,還念念不忘在其治下茍活了四分之一世紀的中華民國:“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絕不會這樣愛它的。”〔6〕曾經“城頭變幻大王旗”的魯迅,深知“剪辮的自由”也來之不易,可是他為之“焦唇敝舌”的中華民國,難道只容許有“剪辮的自由”?他更深知,即使這“剪辮的自由”,在“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也要看主子們臉色的喜怒陰晴。這一點,他知道胡適們比他有更深刻的切身教訓,不然他不會奉送上“焦大”的頭銜: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于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于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凈,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臟,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志也遭殃。〔7〕
對這個依靠軍事暴力維系的政權中的大多數來說,權力和財富才是最賞心悅目的追求。這個政權的最高領導人自然也不例外:“在十年的南京政府統治時期,蔣介石所領導的軍隊成為政府的統治部門,蔣本人成為政權中凌駕于一切的存在。正如曾經一度擔任過蔣的顧問的何廉所回憶:‘委員長走到哪里,真正的政府權力就在那里。就權力而言,他是一切方面的頭兒。’”〔8〕“或者,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在1934年觀察到的,‘蔣介石的影子遍布各個角落。(如果沒有來南京)我將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達到如此明顯的程度。他的利益觸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動;而在別的地方,如果不是癱瘓,至少是聽任政策放任自流。”〔9〕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黨國”的“同調”胡適,僅僅“對于黨國有了一點微詞”,“何嘗有絲毫不利于黨國的惡意”,不但招致黨國總動員式的口誅筆伐,而且國民政府還正式下令教育部嚴懲“反革命之胡適”。讓人噤若寒蟬的是,國民黨上海特別市第八區黨部一紙控狀,就能將提倡憲政的第二號人物羅隆基抓捕入獄。更讓人恐怖的是,被逼離開上海至天津的羅隆基,竟然被“黨國”特工追殺至南開,差點斃命津門。如果沒有五四時代暴得的大名,沒有汪精衛、宋子文等“黨國”高層的暗地支持,如果沒有“黨國”內部派系斗爭的漏洞,胡適的境遇只怕比羅隆基還糟糕。
這樣一個連“焦大”都容不下的政權,你還能指望它什么呢?
著名民國史專家易勞逸,通過扎實而嚴謹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個政權是個獨裁政權,建立在軍事實力之上,并靠軍事實力來維持。這個政權的領導人唯恐失掉他們的權力,不愿與他人分享權力和隨之而來的額外所得;對于政敵和批評者則采取壓制的態度。在一個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愈益增強的政治形態中,公民必然變得更有政治覺悟,這種大權獨攬的做法,一般地說是自我毀滅。”〔10〕
(三)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方生方死,白駒過隙。
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怪癢癢的。蘇州河的濁水幻成了金綠色,輕輕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黃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經漲上了,現在沿著蘇州河兩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尺。風吹來外灘公園里的音樂,卻只有那炒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也最叫人興奮。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電車駛過時,這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從橋上向東望,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暝色中,閃著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望,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齒光和青磷似的綠焰:Light,Heat,Power!
這是茅盾小說《子夜》開篇對上海的一段有名描寫。小說初版本內封里還襯寫著“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高聳入云的摩天大樓,轟鳴駛過的電車,光影交錯的電影院,風情旖旎的舞廳,人頭攢動的跑馬場,熙熙攘攘的百貨公司,一切的都市風景線,仿佛都在發光,發熱,給力!五光十色的大上海,華洋雜處、中外兼容,它的情調與時尚,至今還是許多國人心目中最標致的“a Romance of China”。的確,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這個遠東第一大都市,東方的巴黎,是中國的最“摩登”。當然也是“黨國”的國家影像名片。
“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不僅是穆時英如是說。五光十色的上海之下,還有黑暗、貧窮和骯臟;雍容華貴的上海之外,更有破敗、凄苦和淪亡。
1927年10月的《生活》周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上,發表了著名新聞記者鄒韜奮的《世界各國財富的比較》,副標題為:1920—30年代“美國最富,英國其次,中國財富列在第三”。該文通過引證各種經濟數據,得出一個判斷:北洋軍閥治下的中國經濟,竟然居暴強的日本、德國和法國之上。既然如此繁榮富強,何患之有?可是鄒韜奮卻說:“所患者國未統一,軍閥橫行,所以國勢日弱”,“可惜軍閥把持,兵費徒耗,弄得民窮財盡,只有慨嘆!”。
對這個政權的貪污腐敗,沒有黨派色彩的中間人士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1929年,南通大學校長張孝若(近代著名實業家張謇的兒子)給胡適寫信,大發感慨:
時局攪到這個程度,革命革出這個樣子,誰都夢想不到的,而事實一方面,確是愈趨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現在政府對于老百姓,不僅僅是防口,簡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現在最不堪的,是人格破產,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弄錢,上行下效,變本加厲,與廉潔二字確成背道而馳,恐怕要弄到只有府門前一對石獅子干凈了。最痛心的,從前是官國,兵國,匪國,到了現在,又加上黨國,不知中華幾時才有民國呢?〔11〕
再讀一讀那令人痛徹心扉的《與妻書》,早期黨人舍家別業、死赴國難的鐵骨柔腸、赤膽豪情,而今安在?中山先生《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有言:“革命黨人,歷艱難險阻,以堅毅不擾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碧血橫飛,浩氣四塞”。后來“黨國”執政者大多搖身一變,不為獨夫,即為民賊,“斯誠后死者之羞也”!冷子興演說的榮、寧二府,就是黨國的前塵往事:“如今生齒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與政治上的專制獨裁、軍事上的擁兵自重、經濟上的貪污腐敗相配套的,必然是“黨國”文化上的腐朽反動。胡適當年曾以莫大的勇氣,寫過一篇至今鋒芒閃爍的名文《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從文學革命、思想言論自由和文化問題態度三個方面,直言“國民黨是反動的”,“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便含有擁護傳統文化的成分。因為國民黨本身有這保守性質,故起來了一些保守的理論。這種理論便是后來當國時種種反動行為和反動思想的根據了”。他預言:“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12〕
國家者,全體國民之國家;天下者,普天之下匹夫匹婦之天下。如果肉食者只顧結黨營私、魚肉百姓、恃強凌弱、嗜血專橫,最自然不過的后果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四)
夜闌臥聽風雨聲,一枝一葉總關情。
左翼文化風潮之所以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茫茫中華大地脫穎而出,如蘇雪林所言“赤焰大張”、“赤化宣傳如火之乘風”,就是因為它走在了時代精神的最前沿,有敢于為民鼓與呼的擔當意識,替壓抑和苦難的人民大眾發出了心靈深處的怒吼。
左翼文人知識分子大多出身于社會中下層,對民生的疾苦、草根的艱辛本來就感同身受,有切膚之痛。當真理、正義、公平、自由和民主的旗幟高高飄揚,他們的體驗、知識、理想和膽識,當然更容易被激活和催發。他們以大無畏的獻身真理的精神,走在了時代文化的潮頭。“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正是這一代左翼文人知識分子的光彩寫真。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方面是新文學運動。或許是承續先賢遺緒,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又一次光榮地站在了時代文化的潮頭。上世紀三十年代文壇的各種紛爭,既是問題的深刻扣問,又是主義的深情探求;既是文學自我調節與生長的一個影像,又是社會動蕩與發展的一面鏡子。勃蘭兌斯有言,文學史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們在困頓中的執著探索,本身就是中華民族的心靈在那個特定時空的燦爛綻放。海德格爾有言“人是綻出的存在”,而真理,正是召喚這種綻出的天籟!這個綻放的過程,充滿了挫折和坎坷,也不乏幼稚和謬誤,但是必須記住的是,那種為真理舍生取義的勇氣,那種以身殉道的膽識,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豪邁,足以令后人扼腕長嘆!
托克維爾談及《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寫作動機時,曾言:“我希望寫這本書時不帶有偏見,但是我不敢說我寫作時未懷激情。一個法國人在談起他的祖國,想到他的時代時,竟然無動于衷,這簡直是不能容許的。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每個部分時,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制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因此,每當我在先輩身上看到某些我們幾乎已經喪失然而又極為必要的剛強品德——真正的獨立精神、對偉大事物的愛好、對我們自身和事業的信仰——時,我便把它們突出出來;同樣,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風尚中碰到吞噬過舊社會,如今仍在折磨我們的某些弊病的痕跡時,我也特別將它們揭露出來,以便人們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13〕
如何不溢美、不謚惡,去勉力探求上世紀三十年代及其文人知識分子背后的歷史事實真相和歷史精神真相,讓那些塵封已久的歷史遺跡和精神律動,和我們實現跨越時空的心靈對話,是一個沉重的問題。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們,是在“黨國”的重重鐵幕之下,踏上追求真理的漫漫長路,開始他們響應天職召喚的生命之航。我們如何靜下心來,去仔細諦聽他們從歷史深處傳來的遙遙不滅的回聲?
注釋:
〔1〕〔9〕〔10〕《劍橋中華民國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54、186頁。
〔2〕魯迅:《三閑集·序言》,《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頁
〔3〕魯迅:《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頁。
〔4〕魯迅:《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頁。
〔5〕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7—488頁
〔6〕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557頁。
〔7〕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頁。
〔8〕(美)易勞逸:《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王建朗、王賢知、賈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頁。
〔11〕《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23—524頁。
〔12〕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文集》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588頁。
〔13〕(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