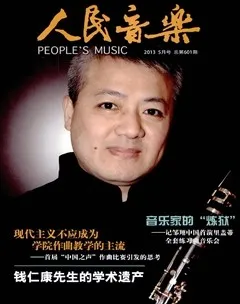“保護”還是“破壞”?
推遲一年的“第15屆CCTV全國青年電視歌手大獎賽”終于開賽了。和往屆賽事不同的是,本屆比賽不僅沒有了“合唱”的比賽,而且還沒有了“原生態唱法”的比賽。“唱法分組回歸民族、美聲、流行,不再單獨設立原生態組”的新賽規,在文藝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據報道,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政協會議上(2013年3月6日),一直力推“原生態唱法”進入青歌賽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田青提交了反對青歌賽取消“原生態組”的提案,他認為取消“原生態組”剝奪了民間歌手(尤其是少數民族歌手)的參賽權利。不僅如此,34位文藝界政協委員還在這份提案上簽了名。①近日,有記者采訪了本屆青歌賽組委會,所得到的回應是:青歌賽并不排斥“原生態唱法”,只不過是“不再單獨設立原生態組”;“原生態唱法”歌手仍可參加“民族唱法”組的比賽。②關于“不再單獨設立原生態組”這一新規的出臺,本屆青歌賽總導演秦新民做了相應的解釋:“回歸三大唱法并不是不重視原生態,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原生態歌曲是展現地方文化的一種歌唱形態,不可再生,也很難有新作品涌現,曲目上重復很多,選手在選曲上也在不斷重復;再有,因為參賽范圍大,很多地方很多參賽隊伍沒有原生態歌手,外雇選手增加很多負擔,比賽意義也不大;第三,從推出伊始至今,一直存在分歧,專業觀點上有其不可比的理由,作為地方文化的精華,各自都有獨特的藝術風華,技術上很難比較。”③這個解釋無疑是就比賽在組織和評比的難度而言的,看不出對“原生態民歌”及“原生態歌手”的態度。但筆者認為,“不再單獨設立原生態組”作為央視出于比賽組織和評判難度上的一種考慮,客觀上卻成為保護“原生態民歌”的一個重要舉措。
大家都知道,將原生態民歌搬上舞臺,始于20世紀90年代。那時主要是以一種音樂會形式展現原生態民歌,歌手(如陜北民歌手王向榮)的聲音是原生態的,但都重新編配了伴奏,甚至運用了管弦樂隊。真正以“原生態”形式呈現的演出應是2003年CCTV舉辦的“西部民歌電視大賽”。此后,原生態民歌逐漸在演出市場上炙手可熱。2006年,在第12屆“CCTV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上,“原生態唱法”正式作為一個組別納入比賽之中,并成為該屆青歌賽的亮點。在后來的第13屆、14屆青歌賽中,原生態民歌和原生態歌手也一直備受關注。也正因為如此,“原生態唱法”成為2006年以來中國音樂理論界的一個關鍵詞。到目前為止,如果在“中國知網”(www.cnki.net)上用“原生態民歌”作為主題詞進行搜索,所得到的結果竟有855個之多。這些文章不少都是較純粹的學術論文,甚至還有碩士學位論文。不夸張地說,原生態民歌已成為一個持續的學術熱點,其話語中心就是“保護”。不難看出,這個問題正是由青歌賽設立原生態組比賽引發的。
將原生態民歌搬上舞臺,對于原生態民歌及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那種“原生態”,究竟是“保護”還是“破壞”呢?這顯然是一個必須回答、但又難以回答的問題。這是因為,“保護原生態民歌”作為一個理論話語,涉及一些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
按最早那些支持將原生態民歌上舞臺的文化學者和音樂理論家的說法,原生態民歌亮相文藝舞臺,可滿足廣大觀眾對它的好奇和審美需求,進而使國人對原生態民歌乃至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具有一種基于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感,最終使這種認同感轉換為一種保護原生態民歌的責任感。但事實表明,這似乎只能是學者和理論家們的一個美好愿望。不難發現,將“侗族大歌”、“蒙古族長調”、“土家族民歌”等多民族、多形式的原生態民歌搬上舞臺、推向市場,的確使其藝術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進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播,并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喚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它的認同、熱愛和珍視,最終使國人對傳統音樂的認同感得以增強。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認同感并沒有真正轉換成一種責任感;對原生態民歌的保護意識也在人們的極度好奇中消解。還必須看到的是,自從青歌賽中設立“原生態唱法”比賽,原生態民歌作為一種“原始生命的文化形態”就被貼上了商標,進而作為一種“文化工業”產品推上“商業化運作”的平臺,并在廣播、電視、電影、演出、出版、旅游等多個產業中“發酵”。這就不可避免地招致一些文化產品制造者和商業化運作推手對其進行過度發掘和開采。與此同時,無論是作為“原始生命的文化形態”還是作為“文化工業”產品,原生態民歌也被媒體和學術界深度炒作。正是這種頻繁的“商業化運作”和“炒作”,原生態民歌及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原生態”被極大破壞。比如,伴隨著原生態民歌被搬上舞臺、推向市場,相當一批原生態歌手流入城市,甚至滯留在像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不再回到他們原來的那個生存環境里去。更有一些歌手走上了職業歌手的道路,進而在極大程度上改變或放棄了他們原來作為一個原生態歌手的審美觀。進入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團的阿寶就是一個例子。當然,這些歌手走向城市進而成為職業歌手,對于他們自己來說,無疑是為了改善自身生存狀態、謀求自身發展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是正當的,任何人都沒有批評和責備他們的權力。對此我們應給予支持。但正由于原生態歌手進入城市、原生態民歌進入市場,原生態民歌及其“原生態”遭到破壞成為事實。還應看到的是,一些原生態民歌的表演已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做秀”。所表演的所謂原生態民歌都不同程度得到了專業音樂工作者的“修剪”,甚至是專業作曲家的改編;一些“原生態歌手”也都受到了專業歌手的影響,甚至得到了專業的聲樂培訓。關于這一點,早在2008年,曾作為青歌賽評委的歌唱家李谷一就提出了質疑。④試想,這種“做秀”不僅脫離了其原生態,而且還對原生態民歌進行了直接的破壞。還需指出的是,在一些保留有原生態民歌的區域,政府鑒于通過推動這一藝術形式走上舞臺提升區域文化形象、進而能為經濟建設服務,便給予原生態民歌和歌手以政策和經濟上的扶持。但也不難發現,這種扶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對“原生態”的破壞。總之,將原生態民歌搬上舞臺、推向市場無疑是對原生態民歌的一種人為的破壞。而青歌賽“不再單獨設立原生態組”卻在客觀上成為對原生態民歌的一種保護。
那么,原生態民歌可不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護呢?這也許是許多圍繞原生態民歌的理論話語的中心。筆者認為,在當今這樣一個信息化時代,原生態民歌作為一種“原始生命的文化形態”難以得到有效保護。這主要是因為,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原生態”已經被破壞,且這種破壞將會愈演愈烈。大家都知道,原生態民歌并不是那種可以脫離其“原生態”的“文本”。原生態民歌就像是一種只有在某種特定水域中才能存活的魚類,一旦脫離這個特定的水域就會死亡。原生態民歌無疑是一種“活”的藝術,離開其“原生態”也就不復存在了,或者說就不再是原生態民歌了。總之,原生態民歌的保護,取決于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原生態”的保護,也就是其“文化環境”(或“文化語境”)的保護。那么,怎樣保護其“原生態”?這無疑要以犧牲那些原生態民歌原產地的經濟發展速度、甚至放棄改善那個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為代價。試想,這種“犧牲”有意義嗎?值得嗎?這種“犧牲”顯然是缺乏人文精神或人文關懷的。鑒于此,人們開始探討用其他保護原生態民歌的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營造一種人為的“原生態”,并將原生態民歌“移入”這種“原生態”之中。談及這種方式,人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作曲家田豐(1935—2001)苦心經營的“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1993年,田豐出于保護云南25個少數民族原生態歌舞的美好愿望,用募集的10萬錢在一個遠離城市喧囂、遠離現代化的山林里辦起了這個“傳習館”,聘請云南各族民間藝人在那里為招募來的各族青少年傳授歌舞技藝。記者是這樣描述“傳習館”的:“在以傳習館為基地進行傳習、研究、展演和展示的同時,‘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還將在全省范圍內民族文化仍然存活、保存原生狀態較典型的地方,分滇東北、滇西北、滇西南、滇東南及滇中南五大區域,設立民族保護村,平均每個區域設十個村落,共設五十個。在村內采取一系列有效的保護措施,使之既能有效的保存并發揚各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又能推動地方各民族文化、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各保護村都將選定二至四名民間藝人和智者負責村內和保護區域內的傳習工作。”⑤起初孩子們在這種人造“原生態”中快樂地接受民族歌舞的“傳習”,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但后來孩子們不樂意了,他們難以忍受那種封閉的、清苦的生活,也難以抵擋現代社會的誘惑,盡管他們與外界是“隔絕”的,連電視和報紙也都看不上。而田豐也因為“傳習所”的生計窘困不堪,并與孩子們因經濟問題產生了糾紛。2000年春,“追隨田豐7年之久、曾視其為家長的孩子們以激烈的沖突方式,與田豐徹底決裂”。⑥2001年,這位作曲家也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曾斷斷續續用5年時間記錄了田豐及其“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并拍攝了長達116分鐘的電視紀錄片《傳習館》。該片制片人彭紅軍曾用“憂傷的文化故事”描述田豐的“傳習館”。他曾嘆息道:“田豐死了,傳習館化為烏有,孩子們浪跡天涯,一種悲憫感油然而生,這里沒有簡單的是非對錯。他們都是絕美的原住民文化和商業文明激烈碰撞的犧牲品。”⑦這個令人扼腕的故事似乎告訴我們: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信息化時代,那種遠離現代化的“原生態”難以存在,進而依賴這種“原生態”的原生態藝術也難以存在。更重要的是,創造和享用這種原生態藝術的人也不再樂意生活在這種“原生態”之中,而更愿意追求一種現代生活方式和現代審美情趣。“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所取得的成效在后來楊麗萍的《云南映像》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但不難發現,這部《云南映像》所展現的云南“原生態歌舞”并不是真正的原生態藝術,而像青歌賽等一些列電視節目或舞臺演出中所展現的原生態藝術一樣,不再是“原生態”中的“活體”,而是一個脫離了“原生態”的“文本”。以上這些都說明,原生態民歌是難以在一種人造的“原生態”中得以存活的。
筆者認為,原生態民歌保護,可能是一種基于充分挖掘、整理的“博物館式保護”。這是因為,原生態民歌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文化語境”是不可能不變的,因為這種“原生文化語境”是以物質和經濟為基礎的。既然物質和經濟基礎正在發生改變或必將發生改變,那么原生態也必然要改變。應該看到,幾乎所有仍保留著原生態民歌的地區,都是經濟不發達或不夠發達的地區,甚至是物質條件極差的老少邊窮地區。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任何人都沒有權力要求那些地區不發展經濟,而去保護那種不再有利于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原生文化語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筆者認為,原生態民歌及其“原生態”的保護極有可能是一種“博物館式保護”,這就意味著,原生態民歌將會是一種“木乃伊”,而不能是“活化石”。
①李珊珊、郭人旗《全國政協委員熱議:青歌賽該不該取消原生態唱法》,《中國文化報》,2013年3月12日。
②馬艷娜《青歌賽:對“原生態”不拋棄,不放棄》,2013年3月19日。www.people.com
③www.cntv.com《青歌賽之王者歸來——專訪第十五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總導演秦新民》,2013年3月23日。
④東方《青年歌手大賽再起波瀾,李谷一質疑原生態唱法》,《現代快報》2008年3月28日。李谷一說:“最初我們界定的原生態唱法,是未經學校學習的、原始的唱法就叫原生態,但現在很多來比賽的原生態是經過包裝的,那么這個名字還成立嗎?還有,說起原始,到底原始到什么程度,這也是很難界定的。”
⑤杜慶云《田豐和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人民音樂》1997年第4期,第24—27頁。
⑥⑦《著名作曲家田豐——8年蹲守保護原住民文化》,《華夏時報》2003年12月11日。
李梅 浙江職業藝術學院講師
(責任編輯 榮英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