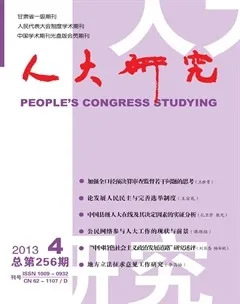現時期應加強立法博弈問題的研究
當你打開法條書,閱讀法律條文的時候,你可能會為這種冷靜的、平和的、嚴謹且沒有感情色彩的語言風格所困擾。你可能會因此而感到法律的枯燥與乏味。但當你把自己的視野放在這些法條的背后,就不難發現,在法律這一神秘之幕下,利益集團之間正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的博弈,伴隨其中的還有激烈的思辨、數不清的判決和法律人的日夜操勞。也許這正是法條美之所在,但法律并不總是正義的化身,透過法條你看到的可能是權勢分利集團的貪婪,可能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壓,甚至是赤裸裸的剝削、奴役、歧視與暴力。但是,你也許會看到另一番“美好”的景象,我們享有憲法賦予的各種權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法條允諾給我們的平等、自由和對私產的保護并沒有得到兌現,其華麗的辭藻無法掩飾這個世界上所存在的丑陋與罪惡。面對這些現象,你不免有所失望,可能還會憤憤不平。但你是否思考過,這究竟是法律的荒謬還是現實的扭曲?
在回答以上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回到對立法本質的探索中去。立法的本質是為了創建某種特定的社會秩序還是從社會中發現法律?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已經具備。馬克思說過:“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1],“無論是政治的立法還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在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2]。德國法學家郝克(Philip Heck,1858~1943)在其1914年出版的《法律解釋和利益法學》一書中寫道:“法律是所有法的共同社會中物質的、國民的、宗教的和倫理的各種利益相互對立、謀求承認而斗爭的成果。在這樣一種認識中存在著利益法學的核心。”[3]因此,法律不僅是一個邏輯結構,而且是各種利益的平衡。由此可見,法律是利益的反映,當我們漠視法律背后的利益關系,不顧及社會現實情況,一味地追求法律文本中的公平與正義,法律不能夠被有效地實施也便在我們的意料之中了。
但是,僅僅信服于上述觀點,也許會使我們陷入片面的認識誤區。試想,若法律完全是由利益所決定的,那么法律是否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強調利益主導著立法結果的同時,是否也應當關注法律對利益的影響?事實上,法律能夠表達利益之要求,調整利益之沖突,重整利益之格局,這種能動作用便是法律被創造出來的實質目的。法律反映著一定時期內特定的利益關系,因此法律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滯后性,當法律不能與社會利益的發展相協調的時候,法律便需要被改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根據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制定的法律才能得到發展與完善,進而促進利益格局的穩定和社會關系的和諧,而這種良性互動最終又有效地促進了法律的實施。在此,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利益都能為法律所反映。一般來說,只有那些涉及國家制度、國家安全、生命、財產和自由的利益才會受到法律的保護,而有很多利益不需要也不可能轉化為法律上的利益,比如道德利益、非法利益等等。因此,我們在這里所談到的“利益”僅指代的是“法律利益”。
無數的立法與司法實踐已經告訴我們,未經人類設計而產生的秩序,遠遠勝過人們有意構想的計劃。一個合格的立法者是善于從社會中發現規則與秩序的人,并且能夠通過這些規則與秩序去平衡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但是立法機關畢竟只是由能力有限的個人所組成的,并且還承擔著人們所賦予的其他職責。因此,他們不可能洞悉世間萬象,把社會規律把握得分毫不差。除此之外,不同立法參與者個人的成長經歷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各不相同,因此而造成的法律觀念和政治立場上的差別也可能導致立法結果與現實利益的背離。
如何使立法更切合實際而不致淪為純粹的暴政工具或者僅僅是毫無約束力的華美樂章?方法只有一個——從社會中尋找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但要依賴立法者的智慧,還要集思廣益,參照不同意見,并仔細斟酌其中的利弊。有誰會真正關心立法呢?那就是法律所涉及的不同利益主體,他們的利益只有通過法律以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的方式確定下來才具有穩定性,事實上,在立法過程中,人們所提的各種“意見”的背后承載的是各種不同的利益。因此,讓那些與立法具有利害關系的個人或群體在法律制定前進行博弈使我們再放心不過了。此時,立法者完全可以站在局外人的角色,憑借自身經驗理性地觀察分析,然后將博弈的結果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這樣的法律便能夠體現客觀的社會利益格局。但是,如果思考到此為止,我們很可能便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誤區,或者以一種僵化的思維看待社會問題。法律是在動態平衡中發展的,新的利益主體的出現或者利益主體實力的改變必然將導致法律與現實的再度脫節,達到一定程度時立法者就要根據新的利益形勢來否定前一博弈所確定的結果。另外,利益博弈并非能夠保證所有的利益主體之間的公平,勝負要受到很多現實條件的制約,比如對信息量的掌握、利益主體的整體素質,以及在立法過程中各方利益主體所提建議的分量等等。不可忽視的是,扮演著“統治者”角色的立法者往往也是利益博弈的一部分,在利益衡量中很難將自身利益置身于其外。因此,我們想要僅從利益博弈中得到公平正義的法律并非易事。
但是,尋求利益平衡之困難并不能阻止我們探索的腳步。對社會正義的熱愛促使我們在挫折中不斷尋求解決問題之道。在提出見解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目前的利益博弈現狀有所了解。在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出現了多元化的利益主體,這些主體之間的競爭不斷白熱化。但是,在立法過程中,作為“經濟人”的行政部門起著主導作用,它們運用自身所具有的委托立法權或者其他“特權”自我賦權、規避責任,或者向立法機關施加壓力,爭取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在這場較量中,眾多利益集團也踴躍躋身利益博弈之中,采取各種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進行游說,影響立法者的最終抉擇。除此之外,社會團體與民間力量同樣關注立法過程,希望能夠為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于是各種力量共同在立法場上角力,將中國社會多元化的趨勢演繹得淋漓盡致。
由于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法律對結社自由的限制,在利益博弈過程中,利益各方力量懸殊較大,弱勢群體缺乏利益表達的組織,無法將自身利益有效地反映到立法中去。同時,由于政府具有“經濟人”的性質,很多行政機關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爭搶立法主導權,甚至采用排斥利益競爭的方式參與分羹,致使人民利益遭受嚴重損害。此外,利益博弈少有制度基礎和法律保障,缺乏合法有序的博弈環境,致使利益博弈的主體和過程較為復雜和混亂。這些現象極大地限制了立法博弈過程中的公平,成為民主立法進程中的障礙。
當然,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之下,我們面臨著兩種不同的景象。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漸趨成熟,立法民主性不斷增強,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利益集團開始出現并逐漸地影響立法,弱勢群體法律利益的表達也逐步通暢。可以說,我國正在朝著利益博弈的時代邁進。然而,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也不能盲目的樂觀,現實中的很多問題還需要我們不斷地研究,而本文所提到的立法博弈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并非短時間內能夠解決。但我想,隨著社會主義法治的逐漸完善,隨著人們立法參與意識的逐步增強,我們有信心期待成熟的立法博弈機制的建立。
學術研究對制度的建設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推動作用,對立法博弈問題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發現當前所面臨的問題,進而采取措施完善現有的立法博弈機制。因此,筆者認為,在社會轉型期,尤其在現階段應當加強我國立法中的利益博弈問題的研究,這對我國立法的民主化和理性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頁。
[3]何勤華著:《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25頁。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