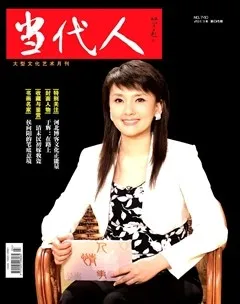巡禮一位中國電視人的生命形式
在中國視協(xi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見到了老文友張子揚兄。說來很巧,我倆同庚肖猴(他略長我33天),有著近似的人生經(jīng)歷,當(dāng)過兵,上過大學(xué),懷揣著文學(xué)青年的夢想,從文學(xué)而藝術(shù)、而戲劇、而電視……然而,子揚的人生卻因藝術(shù)而迸發(fā)出雷霆與閃電……
一、人格論——子揚其人
我是因電視結(jié)識的子揚。他是中央電視臺幾位著名的大胡子導(dǎo)演之一。他的相貌,可謂威風(fēng)凜凜;他創(chuàng)作的詩文,運思精妙;他任總導(dǎo)演的文藝晚會,雅俗共賞;他撰寫的影視評論,精辟睿智;他監(jiān)制、引進播出的海外節(jié)目,開啟新風(fēng);他主抓的電視大劇令人難忘。
子揚送我的《筆底留芳——香爐齋序跋輯錄》,此書可謂開卷有益。
細讀細品子揚的新著,面對子揚這樣一位十分專業(yè)的“雜食者”、一個電視行業(yè)的“茶人”、一個有著“詩人桂冠”的電視文藝“班頭”、一個多元文化融于一身的“國家專業(yè)電視劇頻道總監(jiān)”、一個知行合一的“哲人”、一個肩負使命感且仍在孜孜以求的“文化精英”、一個睿智的文藝批評家、一個熱心于民族復(fù)興偉業(yè)的黨的電視文藝工作者……我該用怎樣的價值尺度來丈量這樣一位中國當(dāng)代電視行業(yè)中不可多得的復(fù)合型、全能型人才呢?
2002年,著名文化學(xué)者仲呈祥在給我的書《序》中說:
“我曾向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學(xué)學(xué)科奠基人之一的張道一教授討教,他亦認為:培養(yǎng)藝術(shù)學(xué)的博士,或造就高層次的文藝評論人才,都是最好選拔那些對藝術(shù)好幾種門類都有所涉獵和研究,而于某一門類有著較深入研究的對象;對好幾種門類都有所涉獵和研究,才可能對打通各種藝術(shù)門類的內(nèi)在勾連的藝術(shù)學(xué)的普遍規(guī)律有所感悟和把握,而對某一門類的較深入研究,才可能對某一藝術(shù)門類獨特的藝術(shù)規(guī)律有所感悟和把握,于是,才有可能善于在個性中發(fā)現(xiàn)共性、在共性中深化對個性的認識。”
重溫仲先生的至評,以此來丈量“子揚現(xiàn)象”的方圓,你便會有一種頓悟。他的藝術(shù)感覺,審美的視知覺,對各個不同門類藝術(shù)形式的獨特規(guī)律的把握、藝術(shù)個案的精到分析,對民族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宏觀掌控,對國家文化版圖的憂思,對中國當(dāng)代影視劇“后戲劇”命題的提出,都源自于他從小受到的良好文化氛圍的熏陶以及在中央戲劇學(xué)院導(dǎo)演系四年的正規(guī)化專業(yè)訓(xùn)練,在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研究生學(xué)歷的進一步深造。良好的藝術(shù)天賦、扎實的學(xué)術(shù)功底、正規(guī)的專業(yè)訓(xùn)練、國家電視媒體的歷練,還有他產(chǎn)自于黑土地文化沃土上熱愛生活、熱愛藝術(shù)、熱愛交友的性格,勤奮好學(xué)、敏于思考、憎愛分明、俠肝義膽、樂于助人、誨人不倦、勇于拼搏、開拓創(chuàng)新的人生態(tài)度,似乎已透露出“子揚密碼”的一些主要數(shù)據(jù)。
二、作品論——子揚其文
詩言志、歌詠言,文以載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生活是藝術(shù)的源泉,人民是藝術(shù)家的母親。這些中國當(dāng)代文藝家耳熟能詳?shù)乃囆g(shù)箴言、創(chuàng)作圭臬,在品讀張子揚已結(jié)集出版的全部文字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中外文學(xué)史證明,無論韻文還是散文,都追求“詩的境界”與“詩性的表達”。子揚由詩而文,而戲劇,而電影、電視文藝、電視劇、電視研究,而多種藝術(shù)形式的點評,可以說都源發(fā)自他的“詩心”、“詩性”與“詩情”。子揚正是“詩意地游弋于影視與藝術(shù)的天地之間”,呈現(xiàn)出他“詩意的”生命形式與藝術(shù)實踐方式。
(一)《筆底留芳——香爐齋序跋輯錄》
“序”與“跋”應(yīng)該是中國文化韻味頗濃的一種散文文體。古已有之。其主旨無非是價值評判,背景介紹、情分緣由,是主客體的一種文化、情感、思想互動。同時在客觀上對讀者又起到一種導(dǎo)讀的推介作用。是重點中的要點,要點中的關(guān)鍵詞。體現(xiàn)了序、跋作者的眼光、胸懷、境界、素養(yǎng)、睿智與才情。《筆底留芳》全集中共收錄了子揚為各種出版物寫就的序跋46篇,加上他成書后的《后記·筆底留芳》,凡47篇。若從書寫量考,近20萬字。但從其涉及的閱讀量考,則堪稱奇觀。
1.對“戲劇”的崇拜、信仰、酷愛,終生相隨。
子揚是一個學(xué)人,更是一個聰明人。因?qū)W戲劇,而分配到中央電視臺。把職業(yè)與興趣愛好有機結(jié)合,把工作中的階段成果編輯成書,把成果與經(jīng)驗用所學(xué)理論上升到科學(xué),留下自己的心路歷程。由此,我們才看到了他所從事的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領(lǐng)域、不同工種的出版物的序與跋。《幾度拋梭織得成——<譯制片劇本精選>序》、《<正大綜藝·世界之旅>序》、《我與<動物世界>序》、《勤于行·勇于思——<跨文化傳播探討與研究>跋》、《<感悟熒屏>跋》等,都是因工作、職業(yè)、階段性成果的原因而成就的文章。
但他能別具心耳、獨具慧眼,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言之鑿鑿。舉例證之:
“戲劇導(dǎo)演是我所學(xué)專業(yè),在我畢業(yè)分配至中央電視臺之后,幾乎再沒有一次完整的實踐,回首頗感遺憾。但在我所執(zhí)導(dǎo)的大型晚會、專題節(jié)目乃至于多個欄目的創(chuàng)辦時間中,卻始終受益于曾經(jīng)受過的專業(yè)能力訓(xùn)練與戲劇美學(xué)的觀照。特別是作為管理者曾任過中央電視臺影視部主任和現(xiàn)任職國際部主任的經(jīng)歷——面對熒屏播放的國內(nèi)電視劇和國外影視劇的疊現(xiàn)進行比較、分析、品鑒之后,遂有感悟:在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依靠電視技術(shù)的普及,作為戲劇藝術(shù)衍生的新形態(tài)的電視劇,是繼電影故事片之后更顯戲劇特征的一個新的戲劇種類進入了當(dāng)今觀眾的精神世界,影響了民族的文化生活。特別是世界各國電影、電視劇的引進,使得電視接收機成為戲劇的舞臺,它所被置放的廳堂成了劇場,而熒屏前的觀眾便成了足不出戶,亦不用買門票的‘超級’觀眾了。域外諸多不同民族的藝術(shù)形象通過熒屏進入了中國觀眾的精神畫廊——‘后戲劇’的概念由此而生,我有興趣繼續(xù)為這個概念作更深度的思考。
“世界各國的電視節(jié)目作為藝術(shù)作品跨越時空的相互交流,使我們在熒屏中建筑了一個多彩的電子‘文化廣場’,同時,這個‘廣場’又是一個‘商場’——電視節(jié)目以它特有的商品品位,以各種可能,為其推銷者爭取著最大的利潤……便有感嘆:這個‘廣場’‘市場’也是個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場’……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如何捍衛(wèi)本土文化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如何弘揚本民族健康的精神氣質(zhì)?——于是,便有了‘文化版圖’的概念思考。”
子揚的這篇“跋”文,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中國電視人的感悟,充滿了精辟的論斷。無論是對于電視節(jié)目的創(chuàng)制者,域外節(jié)目的引進者、播出管理者,還是有志于中國電視節(jié)目的創(chuàng)新者、繼承者,都有著重要的啟示與警醒作用。
2.詩意人生的審美體驗。
說子揚是詩人,具有“酒神”的精神,一點也不夸張;但他的序跋集中,還燃燒著“日神”的火焰。他燃燒著自己,溫暖著他人,也同時被文友們溫暖著,燃燒著。他曾身居斗室,在“香爐齋”——坐落在和平門香爐營香兒胡同七號的小雜院里,一間不足十四平米的平房里,年輕的子揚做過1990年元旦晚會的案頭工作;與策劃、撰稿們一起討論過春節(jié)晚會的結(jié)構(gòu);寫就了專題片《關(guān)于西藏》的文本。回想起這些難忘的歲月,子揚十分動情地寫道:“讀書、寫作是我在這間小屋里最為快樂和興奮的事,許多報告文學(xué)和論文都在這里完成,而如今結(jié)集出版的這部《序跋輯錄》中收錄的大部分文章也是在這里完成的。在我看來,為自己熟悉的師長、友人的著作寫序或跋,不僅是一件非常快樂和有榮譽感的事,更是一個學(xué)習(xí)人生與向人生學(xué)習(xí)的寶貴過程。”“就是在這樣的寫作條件下,我卻常常被友人的托付所溫暖,常常被友人的智慧所啟迪,常常在友人筆下的文章中感受到他們的才華、他們的精神乃至他們的人格。所以,在為朋友們寫序、寫跋的時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種精神上、心情上難以表述的暢然。這些序跋既記錄了朋友們的創(chuàng)作碩果,也記錄了我的心得體會,送人玫瑰,手余芳香,自然,我的筆底也留下了有關(guān)于他們精神智慧的欣馨記憶。”
子揚在《書以載道——<郎鴻葉書法集>序》中寫道:“我在藝術(shù)門類的喜好上屬雜食,口味廣泛,多則難專。”實乃自謙。品讀這篇序文,你就會驚羨他雜而廣,博而專了。 “于今賞讀鴻葉兄自撰的《品茗賦》文,從飲茶之緣起,詠茶之詩篇,到品茶之情趣,悟茶之真諦,剪裁精當(dāng),繁簡得宜,具古韻而不艱澀,甚是一篇情辭并茂的好文章。僅此一篇佳作令鴻葉兄躋身于當(dāng)代茶人之行列亦不為過矣。”子揚從茶藝茶道,進而論說書法書道,縱論古今,旁征博引,信手拈來,最后以一位90歲高齡的前輩藝術(shù)家張仃在中國美術(shù)館舉辦畫展的不長的序言中的肺腑之言表達了藝術(shù)家的“詩意人生”——“一個人,生在有毛筆、墨和宣紙的國度里,真是一種幸福……”由此可見,子揚的生活盡管忙碌,卻時時可以獲得審美體驗。
但是,當(dāng)你細細品讀《張子揚詩選》,你又會看到一個詩人的赤誠,為愛的癡情與苦戀,對生命之痛的沉思。有人稱之為“情種”、“情圣”(李碩儒語),有詩人贊美他的“詩心”、“詩根”(葉延濱語),我卻每每從他的“詩品”而識其“人品”,敬其“人格”。
3.比較文化視野中多元文化的思考。
俄羅斯民諺有“一切從比較中識別”;中國老百姓也知道“貨比三家”,更有民諺“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我國改革開放之后比較文學(xué)作為一個學(xué)科在中國再次興起 。子揚應(yīng)該屬于得比較文化風(fēng)氣之先的那批青年學(xué)子。我感覺比較文化無論是作為一種方法,還是學(xué)科,它所給當(dāng)代中國文化界帶來的首先是一種文化視野,一種思維角度,一種對比方法。從張子揚的電視節(jié)目引進與輸出思路,到“文化版圖”概念的提出;從《<中國畫黑白體系論>跋》,到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化及佛教文化的思考;從對中西方戲劇史的巡禮,到提出“后戲劇”概念的命題;從他經(jīng)歷的對外文化交流實踐,出任國際三大電視節(jié)評委,到系統(tǒng)闡述捍衛(wèi)民族文化安全,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使命感,都會使人從心底發(fā)出由衷的贊佩。
4.仁心交友、文心雕龍,詩心著文。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文會友,當(dāng)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子揚兄有一位年輕文友竇欣平。子揚曾激賞他“從記錄型作者到學(xué)者型作者”,這個評價可謂來之不易,是子揚多年來跟蹤、研讀、分析、點評的結(jié)果。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子揚已是一位筆耕不輟的文化名人了,他擁有永遠年輕的“詩心”、濃濃的詩情,更有一種溫暖朋友、晚輩、前輩、鄰里的仁心、愛心。他曾為同事的新作寫下《大藝亦精誠——<醫(yī)者仁心>序》,也曾為鄰里魏阿姨——一位老軍人的詩集《歲月留馨》流著淚寫序;更讓人感動的是,子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為了盡孝心陪年邁母親習(xí)畫,用盡心力“哄老太太玩”,先是“添亂”,繼之“添彩”的母子深情與唱和之樂躍然紙上;而最讓我敬佩的是與劉揚體先生因電視學(xué)術(shù)而結(jié)下的“忘年交”,在劉揚體先生于2000年出版50萬字的《苦澀的輝煌——劉揚體電視劇評論選》一書時,子揚不辭勞苦為其寫下序文《至仁者勇》,表達了子揚對“有真知灼見的、真誠的、說真話的”電視劇研究專家的由衷禮贊。
仁心交友,文心雕龍,詩心著文,正是子揚留給讀者刻骨銘心的人文風(fēng)采。
(二)《戲里劇外——電視劇美學(xué)漫筆》
我和子揚都是軍人出身。他的這本新著《戲里劇外》,在我眼里,從里到外透著“軍旅情結(jié)”。書序為中央電視臺現(xiàn)任臺長胡占凡所撰,題為《電視劇的文化堅守》;跋是長江學(xué)者、中國傳媒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胡智鋒所為,題目是《文化自覺的理性思考》。子揚此書內(nèi)容可謂是:一條紅線,兩套戰(zhàn)法。
1.一條紅線
少小從軍,一定終身。軍人情結(jié),讓子揚“脫了軍裝還是兵”!只是轉(zhuǎn)換到了“沒有硝煙的文化戰(zhàn)場”上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以守土負責(zé)為擔(dān)當(dāng),以戰(zhàn)死沙場為神圣。“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旅轉(zhuǎn)崗到電視行業(yè)之后,子揚崗位調(diào)整頻次應(yīng)是最多的。當(dāng)過文藝晚會導(dǎo)演、影視部主任、國際部主任、電視劇管理司副司長、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副主任、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直至受命于關(guān)鍵時期出任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頻道總監(jiān)。但不管他轉(zhuǎn)換過多少崗位,愛崗敬業(yè),捍衛(wèi)祖國文化版圖,“好戲出央視”、“打造國家電視劇制作旗艦”、“海外爭鋒”,所有這一切都源自于他忠于職守與強烈的“崗位意識”。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黨叫干啥就干啥,人民需要啥,就生產(chǎn)啥,播出啥!胡智鋒先生歸結(jié)為“一條紅線”貫穿始終。我曾有詩贊子揚兄:鐵肩擔(dān)著傳媒的使命,赤子懷揣著文化的大道。如此珍重!
2.兩套戰(zhàn)法
從子揚出任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副主任開始,就沐浴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春風(fēng),面對文化事業(yè)、文化產(chǎn)業(yè)如何互相促進、融合發(fā)展,一支電視劇生產(chǎn)的“國家隊”如何能夠擔(dān)負起黨和人民的重托,發(fā)揮“旗艦”的作用,子揚一邊公干,一邊思索,寫下了一批有真知灼見、有理論建樹的文章,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專業(yè)思考,還有個案批評,盡顯“儒帥”風(fēng)采。對指導(dǎo)央企文化事業(yè)發(fā)展、文化體制改革具有示范作用與指導(dǎo)意義。子揚剛履新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頻道總監(jiān),即打出了“中央電視臺第八路軍”的旗號,透出一股軍人的豪情,一顆軍人的赤膽忠心。他不是來當(dāng)官享受的,而是來決戰(zhàn)沙場的。按照臺領(lǐng)導(dǎo)的要求,積極探索“國家電視臺專業(yè)電視劇頻道”在藝術(shù)規(guī)律、市場規(guī)律、導(dǎo)向要求的形勢下如何尋求健康快速發(fā)展的思路,我們便看到了《更新理念,再鑄輝煌——有關(guān)好戲出央視的思考》,這篇看似工作研究的“領(lǐng)導(dǎo)文章”,實際上是“專業(yè)領(lǐng)導(dǎo)學(xué)者化”的一個典型范例,無論是業(yè)務(wù)型臺長,還是高校師生,讀過這篇文章都深感其“實踐理性”的價值。
一文一武,張弛有度;亦文亦官,兼融有道;辯證思維,切合實際。因而我們看到的“第八路軍”打造的“第八頻道”風(fēng)生水起,好戲連臺。
三、風(fēng)格論——文如其人
閱讀張子揚新著中的文章,你會從字里行間品出一種味道,在準(zhǔn)確、曉暢、通達、明了之外,一種情趣美、節(jié)奏美、詼諧幽默的風(fēng)格,強烈地感染著你。
前輩作家周明先生在《喜讀張子揚 <筆底留芳>》序文中寫道: “雖然是序跋輯錄,但這本書是由一個個讓人新鮮震驚的故事、一段段優(yōu)秀動情的文字組成的,也就是說,張子揚的序跋,本身就不是應(yīng)人之約的溢美粉飾之言,而是發(fā)自肺腑真情的醉人文學(xué),是漂亮的美文。”
導(dǎo)演出身的人,都會講故事。子揚的序跋集中幾乎篇篇都有故事。讓人在閱讀之中,養(yǎng)眼養(yǎng)心,怡情悅志,傾向與主旨在娓娓的敘述中自然而然的顯露,而不僅僅是乏味的說教和邏輯的推衍。
子揚也喜歡議論。但那1414546a31369e5c936972b2ce300d88f471bd9a7779f6b6851ff413c47f8bf6是詩人的智慧閃現(xiàn),如一條珠串,看似散漫,卻形散神聚。用詩人的意識流,在影視蒙太奇技巧的編織下構(gòu)成子揚影視評論的文體風(fēng)格。子揚在注重文章結(jié)構(gòu)、思想深度的同時,更注重敘述、闡釋的表達之美。
中國傳統(tǒng)文論中“文如其人”,“文以氣為主”,西方文藝美學(xué)中“風(fēng)格即人”的要義,都是引領(lǐng)我們?nèi)グ盐兆訐P“其人其文”的金鑰匙。
細讀子揚的文章,你還會發(fā)現(xiàn),黑土地文化沃土上生長出的語言表達風(fēng)格,詼諧幽默,充滿生活情趣。
“原本商定:由我聯(lián)系侯一民先生與陳昊蘇先生各寫一序。而我與鴻葉兄各成一跋以為‘后記’。無奈侯先生大病做了手術(shù),……陳昊蘇先生突因公務(wù)繁忙,常常國際行走,溝通不暢。……緊迫之際,鴻葉、桂棕兄嫂賢伉儷反復(fù)誠邀:序由我作。如此,雖受之有愧,然卻之不恭,只好義不容辭地‘后衛(wèi)改前鋒’了。”行文間,作者的真情實感,做事做人的風(fēng)格、天性,亦莊亦諧,“后衛(wèi)改前鋒”這“小包袱”一抖,讓人忍俊不禁。
“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神話)是人類精神世界童年時期的搖籃,而宗教藝術(shù)則是置存在這搖籃中的玩具與歌謠。”這段話,實在精彩,既通俗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經(jīng)典論述,又比喻恰切,生動形象地告訴當(dāng)代人們“宗教藝術(shù)”的本質(zhì)屬性與功能地位。如果不是詩人的智慧與想象,換成個別的學(xué)貫中西的專業(yè)學(xué)者,或許會長篇大論,邏輯推衍,把簡單問題復(fù)雜化、術(shù)語化、神秘化。而子揚做人為文,卻絕沒有一絲“唬人”的動機,他處處在為“觀眾”、“讀者”著想。
子揚用詩人對形象、意象天才的捕捉能力,以神似的喻體,去傳達被喻者的神韻和自己的感受。這應(yīng)該是子揚作為一個成功的影視工作者多年養(yǎng)成的一種職業(yè)習(xí)慣,用影像語言去轉(zhuǎn)化文學(xué)作品的整體感受。從當(dāng)代電視文藝評論的受眾需求而言,這也是我們正統(tǒng)文藝評論家應(yīng)該兼顧的探索方向。
我們期待張子揚的事業(yè)健康發(fā)展、高歌猛進;也期盼繼續(xù)看到記錄其心路歷程的美文如雨后春筍,蓬勃簇生。
(責(zé)編:孫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