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死亡”的契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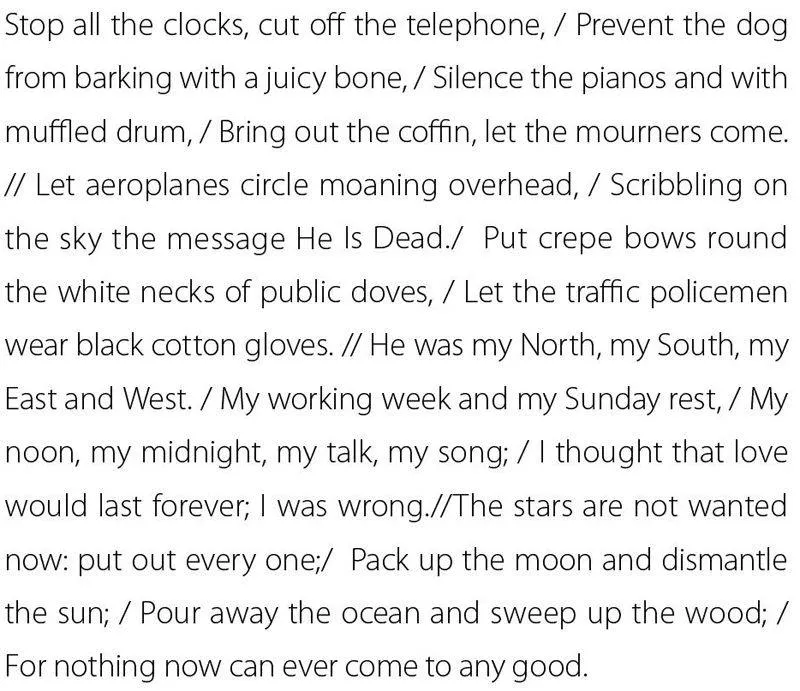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文明之城。這里有凡·高描摹的金燦燦的“向日葵”,亦有倫勃朗捕捉的“夜巡”中的光影。優(yōu)秀的文學(xué)滲透到這樣的城市,比城市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和歷史更能抗擊歲月的步伐。被公認為英國“國民作家”的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1948-)便憑借一部“小長篇”《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舉摘得了1998年英國曼布克文學(xué)獎的桂冠。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容許人們選擇安樂死的城市,這一點恐怕并不為人們所熟知。備受病痛折磨的人可以在這個城市對自己生命存續(xù)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權(quán)利。麥克尤恩和他的遠足同伴達成了一個有趣的協(xié)議:如果二人之中,有人開始罹患類似“老年癡呆”的病癥,那么為了避免對方陷入屈辱不堪的境地,另一方就要把他帶到阿姆斯特丹,以接受合法的安樂死。結(jié)果,一旦哪個人忘記帶上了必備的遠足設(shè)備或是記錯了某個日期,對方就會戲謔地調(diào)侃:“嗨,你該去阿姆斯特丹了!”然而,這個小玩笑卻促成了麥克尤恩的一個念頭:如果把兩個達成協(xié)議的人物放在小說里,讓他們反目成仇,之后不約而同地引誘對方來到阿姆斯特丹,又同時謀害了對方的性命,這豈不是一個不錯的故事?于是,《阿姆斯特丹》便漸漸擁有了自己的生命。
《阿姆斯特丹》中的兩位男主角,一位是“偉大的作曲家”克利夫·林雷,另一位則是一家“全國性大報”《大法官報》的主編弗農(nóng)·哈利戴。兩位男配角分別是富可敵國的出版商喬治·萊恩,另一位是極有可能問鼎首相寶座的現(xiàn)任外交大臣朱利安·加莫尼。從藝術(shù)界到新聞界,從文化界到政治界,這四個人真可謂國之棟梁。而這四個男人卻是由一個女人莫莉聯(lián)系到一起的。喬治是莫莉的丈夫,另外三位是她的老情人。莫莉的葬禮拉開了《阿姆斯特丹》的序幕,雖然她在開篇即已死去,但她生前的音容笑貌,依然鮮活地存在于情人們的記憶之中。在莫莉的葬禮上,通過克利夫的視角,讀者可以看到屬于這個社會中堅力量的眾生相:“他四顧看著周遭這幫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齡,上下相差不過一兩歲。他們是何等興旺發(fā)達,何等有權(quán)有勢,在這個他們幾乎蔑視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們是何等地繁榮昌盛。”
克利夫與弗農(nóng)雖擁有共同的情人,卻是多年的好友。莫莉的死亡,讓他們感到恐懼。兩人相互約定,如果其中—人面臨死亡,對方有責(zé)任幫助他有尊嚴地死去。于是,他們簽下一紙契約,可以在這種情況下為對方實行安樂死!這也為兩人后來實現(xiàn)“共赴死亡”的契約埋下了伏筆。
從第二章開始,麥克尤恩分別以克利夫與弗農(nóng)各自的行為軌跡作為平行線索,截取生活與工作的片段,從容不迫地勾勒出兩人的日常生活與內(nèi)心世界。由于麥克尤恩對古典音樂,尤其是巴赫的嗜好,所以他在章節(jié)布局上采用了對調(diào)格式,如同一支短小凝練的“二重奏”,兩條線索并行不悖。
為了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克利夫決定到山間遠足。正當他在懸崖上通過騰空飛起的鳥兒尋覓到創(chuàng)作靈感的時候,在懸崖下方卻正在發(fā)生一起強奸案。害怕丟掉創(chuàng)作靈感的克利夫卻一直沉湎在自己的音樂里,無動于衷。
麥克尤恩的文字具有尼德蘭室內(nèi)畫的靜謐。他不動聲色地直接把讀者帶入主人公的內(nèi)心世界,讓讀者和克利夫一起感受他創(chuàng)作《千禧年交響曲》的心理過程:他如何自得、如何焦慮、如何遭遇瓶頸、如何打算到山間遠足以實現(xiàn)突破、如何在靈感乍現(xiàn)的重要關(guān)頭受到致命的干擾等。比如,當克利夫不愿出手相救那名正在遭受傷害的女子時,他在心里這樣為自己開脫:“……就假裝他沒有到過那兒不就行了。他是沒有到過那兒。他一直在他音樂當中。他的命運,他們的命運,相差云泥,根本就沒有交集。那不是他該管的事。這才是他的事,而且并不容易對付……”穿插其間的妙趣橫生的小插曲,也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一塊口香糖徹底地破壞了克利夫的心情:“他心情抑郁,已經(jīng)覺得步幅有些不對稱,就仿佛一條腿比另一條長出了一塊。他一找到座位就脫下鞋來查看,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有一團烏黑的口香糖已經(jīng)被踩平了,深深嵌入他鞋底上那些鋸齒形的紋路當中。他厭惡地撅起了上唇,直到列車都緩緩啟動了,他仍舊在用小刀奮力地挑著、割著、刮著……多恐怖啊,竟然跟某個陌生人嘴巴里嚼過的東西有如此切近的接觸。”
《大法官報》的主編弗農(nóng)其實才華平庸,“他是個沒什么棱角的人,既沒什么缺點,也沒什么美德,在大家眼里是個可有可無的主兒”。由于趕上報社所有權(quán)利益的重新調(diào)整,他僥幸當上了主編。葬禮之后,喬治給弗農(nóng)打來電話,說他手里有一張莫莉生前拍攝的外交大臣加莫尼的照片,希望能夠在《大法官報》上刊載。這是一張加莫尼穿著裙子、擺出貓步的易裝照。可在弗農(nóng)眼中,這成了挽救報紙發(fā)行量和打擊加莫尼的致命武器。
弗農(nóng)不顧眾人的反對,決意刊載這張照片,以讓加莫尼出丑,改變他在選民中的形象。他十分希望得到克利夫的支持。然而,克利夫卻堅決反對弗農(nóng)刊載照片,并痛斥弗農(nóng)是“在莫莉的墳頭上拉屎”。
原本是莫逆之交的兩人心生齟齬。他們開始互相批判。讀者可以通過他們各自的視角,看到對方的“真面目”。在弗農(nóng)看來,克利夫妄自尊大,自以為是,為了所謂的創(chuàng)作靈感,竟然對正在發(fā)生的強奸案視而不見:而在克利夫的眼里,弗農(nóng)作為主編,不僅毫無創(chuàng)新性,居然還打著正義的旗號千方百計地搞臭加莫尼,目的不過是為了挽救報紙可憐的發(fā)行量。
隨著兩人危機感的加劇,一種語言節(jié)奏上的加速度也漸行漸快,直到崩潰的臨界點,弗農(nóng)被迫辭職。輿論普遍認為,弗農(nóng)具有“訛詐者的陰暗心理,以及跳蚤的道德境界”。因為,在公眾看來,“在這樣的時代,屬于個人私下里的無害的小嗜好,哪怕他們是公眾人物,也仍舊只是他們自己的事。而只要是跟公眾的利益無關(guān)的議題,訛詐者和偽善的告密小人的過時伎倆也就失去了興風(fēng)作浪的舞臺”。同時,他接到了來自克利夫的惡毒的詛咒信“你活該被炒魷魚”。弗農(nóng)氣急敗壞,決心報復(fù)克利夫。
由于弗農(nóng)的告發(fā),克利夫不得不在《千禧年交響曲》創(chuàng)作的關(guān)鍵階段,配合警局的警官調(diào)查案件,心力交瘁。在內(nèi)心深處,克利夫?qū)⒆约翰潘伎萁摺㈧`感缺失的事實全部歸罪到弗農(nóng)身上,他覺得自己身上的天才稟賦已被弗農(nóng)破壞殆盡。克利夫的創(chuàng)作最終宣告失敗。《千禧年交響曲》被認為是抄襲之作,“顯然,結(jié)尾的一個旋律是對貝多芬《歡樂頌》的無恥抄襲,不過加減一兩個音符而已”。于是,他決計通過安樂死來報復(fù)弗農(nóng)。就這樣,兩位最好的朋友,相約在阿姆斯特丹,在假意和好之后,各自為對方斟滿了一杯毒酒,同時將對方置于死地。兩人的相互謀殺,就如同他們當初約定的安樂死一樣,充滿了諷刺,而更加諷刺的是,最終從阿姆斯特丹運回他們尸體的人,竟是道貌岸然的外交大臣加莫尼和出賣妻子照片、坐收漁翁之利的喬治。
這部作品就像一部探查人類內(nèi)心世界的探頭,它挖掘了人性的脆弱和虛偽,反映了當下人們?nèi)狈π叛龅木駹顟B(tài)。美好的東西,需要經(jīng)過漫長歲月的經(jīng)營和維護;而仇恨與邪惡,卻可以在頃刻之間就毀滅人們心中最為珍貴的情感。麥克尤恩以英國20世紀30年代著名詩人威斯坦休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歧途》(The Crossroads)一詩的首句作為該小說的序言,可謂切中肯綮。“在這里相逢并擁抱的朋友已經(jīng)離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錯誤”。
在奧登的另一首《葬禮藍調(diào)》(Funeral Blues)中,他這樣寫道:
“拔停所有的時鐘,切斷電話,/給狗一塊帶汁的骨頭,讓它莫吠,/鋼琴聲歇,隨著低沉的鼓聲/抬出靈柩,讓哀悼者到來。/讓飛機在頭頂上悲旋,/在天空中涂寫著訊息:斯人已逝。/把黑紗系于信鴿的白頸,/讓交警戴上黑棉手套。/他曾經(jīng)是我的東,我的南,我的西,我的北,/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話語,我的歌聲;/我以為愛可以永恒:我錯了。/不再要星星,摘下每一顆,/包起月亮,卸下太陽,/傾瀉大海,掃集森林;/因為一切都不會再有意義”。(筆者譯)
麥克尤恩雖對女主人公莫莉著墨不多,可她卻是一條隱形線索,將四個男人聯(lián)系在一起。表面上看,這四個男人似乎都很愛莫莉,可實則不然。喬治不愛她,否則就不會拿著她拍攝的照片,四處買賣,坐收漁利;弗農(nóng)不愛她,否則就不會做出刊載照片這種可笑可鄙之事;自私的克利夫,為了挽留靈感而置受害的女子于不顧,如果受害的女子換成莫莉,想來情況也不會有所改變:而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惜利用老婆、孩子大打親情牌的“易裝癖”加莫尼就更談不上愛莫莉了。“我以為愛可以永恒:我錯了”。興許,她曾經(jīng)也是“我的東,我的南,我的西,我的北,/我的工作日,我的休息日,/我的正午,我的子夜,/我的話語,我的歌聲”,可當愛情泯滅,友誼不再的時候,才知道“一切都不會再有意義”。那時,“共赴死亡”說不定也是一種很好的解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