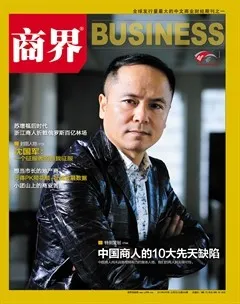小團山上的商業苦旅

這是一場略帶浪漫主義色彩的商業實驗。在距離安徽合肥市區40公里的肥西縣銘傳鄉,一位臺灣教授聯合島內十幾位同行,用六年的時間,將一座荒蕪的垃圾山變成了小有名氣的香草農莊。
香草農莊的商業邏輯一度讓當地人很難看懂。比如,名為農莊,但農產品包括加工制成品銷售只占其盈利結構的20%;與之同時,兼具南歐與徽派建筑風格的民俗建筑里,則常年開展諸如生態教育課程以及親子活動等……
事實上,這種帶有典型臺灣農莊經驗的商業模式,破解的正是大陸“農家樂”投入產出比低的行業現實。在臺灣,農莊往往規模很小,但30畝地卻能做出上億元人民幣的營收。它是怎么做的?
在我們接下來的敘述中,你將看到這樣的商業模式建構。同樣還會感受到當這種農莊模式橫跨海峽遭遇新商業環境,所產生的“糾結感”;與這份糾結相伴的,還有故事主人公的教授思維與商人思維之間的落差,臺商身份與當地村民間的文化融入難題……
2004年
2004年前,郭中一的身份是留美物理學博士,畢業后被聘為臺灣東吳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就在此時,原本生活富裕的岳父遭遇破產,妻子莊蕙英不得不為父親背上了上千萬元臺幣的負債。
一開始,郭中一并不知情,直到他得知妻子為了還債每天打四份工,有時竟連一份中碗的面都買不起時,他心疼極了。妻子也心疼丈夫,為了不給他增加負擔,提出了離婚。
郭中一拒絕了。
最終,夫妻倆將美國的房子賣掉,一部分錢用于還債,另一部分錢則在臺灣購置了一處房產。郭中一是對的。兩年后,臺灣那處房產增值,他們不但還完所有外債,還為后來的小團山積累了第一筆本金。
2004年,郭中一還做了—件事。
為反對陳水扁政府的“對美巨額軍購案”,郭中一和幾位教授組織了抗議游行。抗議期間,他不斷接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曾經在一次臨時抗議中被警察打倒在地。盡管如此,他還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70多次。
同樣是2004年,郭中一被推選為臺北市合肥同鄉會的會長。“合肥?我自己都沒見過故鄉的樣子,怎么才能讓出生在臺灣的第二代合肥人了解自己的家鄉呢?我得先去看看。”郭中一決定親自走一趟。
郭中一的故鄉隸屬肥西縣銘傳鄉——以清代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的姓名所命名。劉銘傳在臺灣享有很高聲譽,而郭中一祖上曾是劉家的私塾先生。據郭中一父親回憶,郭中一后來所建的香草農莊就靠近自家祖屋。
郭父一生保留著肥西口音,發不出“五”這個音。“水燒好了,你先洗還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還是我先死?”從小郭中一填籍貫,都要寫安徽合肥。所以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合肥肥西人。
陸陸續續探訪故鄉幾次之后,郭中一有些失望——幾年過去了,為什么這里還是老樣子?垃圾沒人清理,道路越來越差,農民的生活依舊窮困。
他找到鄉長,把自己的疑惑告訴對方:“人家上海的一個小地方一兩年就把它開辟那么好,為什么我的家鄉還是老樣子?”“郭教授,那你回來!我幫你把土地呀這些必要條件想辦法弄好。”鄉長的鼓動讓郭中一心動了。
按照當地政府的想法,如果郭中一帶來項目落戶肥西,那郭便是鄉里唯一的外商。而在郭看來,臺灣島內寸土是金,想要找塊土地實現自己的生態農莊夢想無異于癡人說夢!為什么不轉戰故鄉呢?當郭中一把消息帶回自己的圈子,迅速取得共識,幾位教授們紛紛響應。“中央大學”的李河清教授說:“我們能不能為自己設計—個無污染的社區?”
最終,七位博士、教授合資,由郭中一夫婦牽頭,確定在肥西縣銘傳鄉啟明村建設生態農莊。
信義的糾結
按照郭中一最初的設想,小團山將建成為一個“生態農莊”。農產品包括加工制成品的銷售,只占小團山盈利結構的五分之一,不求量,但一定要保證綠色健康。
在臺灣,新農業項目直接銷售的附加值,遠不及在農林牧漁營造出來的自然、生活基礎上開展的服務業,所以小團山的未來盈利項目應該是餐飲、會議接待、面向中小學生的生態教育課程和親子活動等。
這的確是個讓人興奮的美麗藍圖。只是當藍圖植入現實,一切都變味了。
2006年,莊蕙英帶著丈夫郭中一以及其他幾位教授的心愿,籌措來的250萬元人民幣,和兩個孩子來到合肥。這一來,就是三年。
初來乍到,土地問題就讓莊蕙英焦頭爛額。早在2005年,鄉政府打包票給他們四塊地,而且彼此相距不遠,郭中一很滿意,打算同時發展。當莊蕙英來到這里,這才發現原先說好的四塊地已經被轉手給了當地鄉長的親友,只剩下一座從未有人耕作過的荒山——小團山。教授們對地方政府的背信之舉非常不高興,但莊蕙英說服了其他股東,還是把地租了下來。理由是,“荒地的好處是零污染,而且不會與農民爭地。”
小團山上200多畝農地簽的是50年租約。這片區域相給本地人的山頭都以荒地計算,荒蕪的小團山卻被劃入了旱地、林地乃至良田,每畝租金400元——全鄉最高。另外一方面,村里人還是抱怨臺灣人占了地,因為他們拿到手的只有45塊錢。
土地的問題并未就此最終解決。一開始,鄉政府承諾把土地以一畝3萬元的價格賣給他們,等指標下來就可以買。可指標下來,地價已經從3萬元漲到11萬元,變成了工業用地的價格。莊蕙英咬咬牙,準備籌錢買下,便簽了約等著辦手續。
哪知政府把地以一畝600萬元拿到中心鎮炒地皮,并拖著不辦手續。2012年,地價已經漲到了一畝22萬元!郭中一去找官員理論,對方遂口徑放寬為先繳錢,待手續辦完后再將差價部分返還。但這“返還”只是口頭承諾,沒有任何人愿意出具書面擔保。
——“最基礎的誠信在哪里?”郭中一憤怒地拒絕了這一提議,雙方僵持至今。
除了土地,人情關系也常常讓他們非常苦惱。“都說在大陸做生意,大部分是做人情生意,我們都不是商人出身,不懂得去跟政府打交道。”在臺灣,想要辦手續,只要去相關的部門拿號排隊,很快就可以拿到手續。如果有公務員服務不周,投訴也方便。
為了適應大陸的“商業規則”,莊蕙英不得不硬著頭皮參加各種應酬。一次,政府相關機構在小團山舉辦了一個簽約儀式,來了很多政府要員。莊蕙英在這種場合不懂拒絕,旁邊有人不停地說,“你們這一次都是某某領導拍板的,你一定得去跟他喝一杯。”
莊蕙英硬著頭皮喝了幾杯。突然,她感覺下體一陣不適,一低頭,發現褲子都紅透了。“當時不是生理期,我真是害怕了。”莊蕙英說。
身體不濟,加上人情復雜,對于小團山,莊蕙英多少次想要放棄,但想到丈夫,她又于心不忍。
村姑與“農夫”的矛盾
初建農莊,一些村民攜家帶口要上小團山看個究竟。他們對莊惠英說:“這里以前是我們家的,你還不讓我進來看看?”而此時郭家自己的親戚對此非但不管不顧,還說“咱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另一方面,小團山上的土壤屬酸性,為了化酸為堿,莊蕙英不得不找人從山腳下取土向上填埋。為了養地,她早期先種上了綠肥植物,并試種少量香草。而村里人對香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更難以理解什么“生態農業”,不僅常常把菜種進農莊圈好的地里,還在后山的魚塘邊等著莊蕙英撈魚時搶一些回去,有時一大群鴨子被趕到地里,把剛剛種上的香草苗吃個精光。
更讓莊惠英哭笑不得的是,有人甚至到政府部門檢舉過農莊在山上建導彈發射臺,實際那只是香草農莊供水用的水塔而已……
——2009年,郭中一終于辭掉臺灣高校的工作,趕到大陸。而此時的小團山,在莊蕙英的辛苦經營下已初具規模。
終于在故鄉扎根,郭中一一來便急于“施展拳腳”。他想把自己肚子里的墨水運用到農莊里,卻遭到了莊蕙英的反對。想當初反軍購運動中,妻子風雨無阻,為游行的人們送水送傘送食物,積極地保障后勤工作來支援他,讓他感動至今。為什么這時,她卻跟自己唱起了反調?
莊蕙英有自己的理由。
這幾年的獨自辛苦經營,使她不希望丈夫冒險去嘗試結果未知的事。“如果不成功,資金又會周轉不過來。”雖然有時郭中一提出來的問題,的確對農莊的發展有很大的改善,但莊蕙英仍然比較保守——資金上的捉肘見襟已經讓莊蕙英學會了精打細算。
有一次,郭中一提出要開發北京和上海的市集,莊蕙英表示:“現在我們的產品還沒有成熟,你現在這樣會提前把我們公司的形象搞壞。”,但郭中一堅持要去,說:“現在不走,還等什么時候?等我們開發好就晚了。”于是每次市集,郭中一就帶一批大學生坐夜車到那邊的市集擺攤位賣產品。但是由于商品都是粗加工LcETIUf/wn50MzzABW3AkhhMObmRROUP/GFedZx+Rx8=,包裝也不精美,常常原模原樣地抱回來。“又花掉一大筆的交通費和住宿費,他們賺的錢都不夠這些花銷的。”
莊蕙英對于丈夫的執著很懊惱,夫妻倆也因此常常冷戰。但有時莊蕙英也心疼丈夫的辛苦,看到他的積極性被現實打擊,她便不會再多說什么,只要是在資金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莊蕙英都會盡量幫丈夫實現他的想法。
其實最讓她擔心的并不是丈夫的做法不妥而浪費了錢,而是曾經熱情積極的他,意志變得頹廢。
原來,郭中一剛來小團山,就有很多民企和商人來找他合作。郭中一也希望生態農業的概念普及,順便為自己帶來一些盈利。所以他常常徹夜給他們講課,幫他們找資料,寫項目書。有時候,談到高興時他就會興奮地說,“小團山要有一個兄弟出來了。”但很多人都是表面上看似考察農莊,實則把項目報告拿走后就沒有了下文。莊蕙英勸丈夫:“人家只不過是當做一個可以申請資金的項目,圈一些政府的錢而已,你不要想太多了。”
郭中一確實很失望。
在他的概念里,在臺灣,就算想做都沒有土地,而現在有了這么好的項目,又有現成的模式,盈利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為什么非要淪為圈錢的工具呢?他想不通,也接受不了。
現在,聽到有人找妻子說關于合作的事情,郭中一會很冷淡地對她說:“不要浪費你的時間”。莊蕙英明白卻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郭中一當初的創業激情已在各種不信不義之人和事的打擊下,慢慢消退……
模糊的未來
“我現在扛一袋50斤大米還跑得很快哩!”莊蕙英笑著告訴記者。
——2012年12月28日清晨5點鐘,被暴雪侵襲的合肥還是一片漆黑,莊蕙英已經坐在地板上開始打包要發往北京集市的手工魚丸。6點鐘,她開上小面包車,把打包好的貨物送往快遞公司,然后緊接著就去買菜送往農莊。這是她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她年輕時的照片,真的很難想象,一個曾經留美的漂亮女教授現在已經儼然一副農婦的模樣。“我每天從上山到回家來回要三個小時,但從來都不覺得累,因為我來這里就不想回家了!哈哈……”說完,莊蕙英笑得像個孩子。
小團山已經像她一手撫養長大的嬰兒,她傾注的不僅僅是精力,更多的是感情。
2013年是郭氏夫婦到小團山創業整整第六年。外人看來,“臺商獨資”是一個耀眼的光環,人人都以為他們腰纏萬貫,出手闊綽,就連很多不熟悉的親戚都想來小團山謀個工作,沾沾光。誰曾想,他們自己送貨做飯,制作包裝農產品,就連打掃衛生,看山護院有時都親力親為。
就在妻子為農莊忙上忙下的時候,郭中一則奔走于臺灣和合肥兩地,拿著小團山的項目說明書和一個名叫“小團山的故事”的視頻四處籌款。一個曾經風光無限,教書育人的大學教授如今回到臺北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是一遍遍地向朋友、同事介紹小團山,希望能拽到更多的資金支持小團山的發展。
朋友多是支持的,但偶爾的不順利還是會讓郭中一心里不是滋味。百感交集過后,他仍然堅持,為了當初股東們的信任,也為了現在依舊忙碌在小團山的妻子和員工們。
冬天的小團山萬物凋零,不能像夏秋季節那樣通過組織夏令營或旅游觀光來盈利,莊蕙英只能靠著豐收的香草做一些農副產品,如香草香腸、精油、餅干、魚丸等,進行粗加工后,拿到網上去賣。而這一點收入,遠不夠給山上的員工發工資。于是有人勸莊蕙英不如放一半的員工回家吧,就不用到處籌錢發工資了。
但莊蕙英不忍,“沒有紅利給大家我已經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能還讓大家沒有工資拿?”好在丈夫每次打電話來,都是寬心的話:“你放心,資金我來解決,你不用太擔心。”
每周六的下午,小團山上都是孩子們的身影,因為這個下午是他們免費學習英語和計算機的時間。有時候家長們還會抓雞,拿雞蛋送給莊蕙英,“我就說你們自己都省吃儉用的,我不能收。我拒收了之后,可是他們還是偷偷地把自己養的雞丟到我們農莊的養雞棚里去,挺有意思的。”莊蕙英說到自己的公益事業時,滿臉笑容。
郭中一也在小團山上開設了學堂,自己授課,學生除了自己的兩個兒子,還有一些認同他們教育理念的家長也把自己的孩子送過來。每當過去的學生問起郭中一的選擇,郭中一回答: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吐出人生最后一口氣前,決不妥協。如果還能夠改善世界,就不能耽于個人一己的安樂。
——采訪結束,站在小團山上,周邊的田園景色一覽無余。薄薄的雪覆蓋在泥土上,香草農莊特別的建筑設計,和不遠處的農村景象顯得并不搭調。或許,這份反差和這種糾結依舊會伴隨郭氏夫婦的未來時光,只是雪凝雪融,小團山新一季的香草好像又要發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