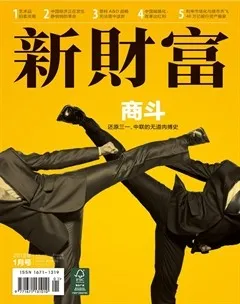中國城鎮化:改革出紅利
未來十年的經濟主題中,城鎮化被認為是最大的關鍵詞。但中國城鎮化面臨著欠賬、趕超和制度三大問題。改革可以使城鎮化回歸到一個自然提升過程,只有改革才能突破城鎮化的現實約束。
在十八大之后的未來十年經濟主題中,城鎮化被認為是最大的關鍵詞。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當人均GDP近5000美元、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時,經濟社會變化的一大主流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將生活在城市。中國就處于這樣的發展階段。在一些觀察家看來,執政者推動城鎮化,就抓住了未來一二十年中國經濟社會變化的主流。果真如此嗎?
人口、財力制約城鎮化
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就開始下降,比此前的預測早3-5年。由此帶來的問題是,在城市低端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情況下,是否有足夠多的人口可供轉移?
我們的測算表明,中國向城市可轉移的農業勞動力,大概只有4000-6000萬。國家統計局多估了將近1億的農民。原因是國家統計局計算的時候,沒有區分全職農業勞動力,我們估計中國兼職的農民數量大概8000萬(詳見2012年10月號李迅雷專欄文章)。這意味著,中國未來城鎮化的空間可能不大。
另一方面,中國城鎮化必須要從“低端工人奉獻”到“向低端工人反哺”的階段,這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務覆蓋更多的城鎮化人口。但中國財政收入進入長期減速階段,土地轉讓金收入受制于房地產調控,政府財力日益顯得捉襟見肘。簡單推算,全國有1.6億外出農民工,如果全部市民化,按每人15萬的費用計算,則需要支出24萬億元。如此大支出負擔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面對城鎮化“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城鎮化的關鍵在市民化
然而,城鎮化不繼續推進,中國無疑將陷入一個中等收入陷阱。一個8.3億的龐大群體(農村居民和城市農民工),人均消費水平僅相當于另外一個5.1億城市群體的1/3,如果結構固化,中國顯然沒有希望。
從經濟結構看,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內需不足、服務業滯后、區域和城鄉差距大,這些問題都和城鎮化有關。問題的對策是低端工人需要從“生產因子”轉變成“消費因子”,土地的“斂財功能”需要讓位給“生產功能”和“生活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中產階級和城市“小資”逐漸形成并成為社會穩定力量,農村居民受益于近年來的減稅和社保措施,對社會滿意度提高。唯有“夾心層”處于相對不穩定狀態,這包括1.6億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和城市貧民,以及未來還要轉移到城市的農村居民。如何讓其在城市安居樂業,不至成為“流民”,是城鎮化的重大課題。
按照人口普查數據, 2010年內地分別有6.7億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在6.7億城市居民中,有5.1億城市戶籍人口,還有約1.6億在城市連續居住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在6.7億農村居民中,青少兒童(34歲以下)3.1億,中年人(35-59歲)2.5億,老年人(60歲以上)1億。面對人口約束,城鎮化的關鍵是,已進城和新轉移農民工及家屬的市民化。
市民化意味著,未來十年內,中國需要讓現有的1.6億農民工和即將進城的1.4億農民工及家屬過上正常的城市生活。這對于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城鎮化是個系統工程
市民化不會自動實現。地域轉變不足以實現市民化,過去十年里,數以億計農村居民轉移到城市,他們推動了中國經濟增長和城市發展,但客觀上惡化了經濟結構,因為他們有力生產而無力消費。身份轉變也面臨障礙,假設10年3億、每年3000萬居民從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地方政府很難配合,因為公共服務(城市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等)配套將遭遇瓶頸。
市民化的現實路徑是:在中小城市開放戶籍準入,大城市逐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淡化戶籍壁壘,解決社會保障問題;促進就業和扶持創業,解決收入問題;提高征地補償標準,讓農民享受更多的城鎮化和工業化紅利,給予農民更多的進城資本。
從財力角度,市民化反而增加了財力約束,因為征地補償標準提高意味部分征地收入從地方政府轉移到農民。地方本來就財力緊張,如何能應付不斷增加的公共服務配套壓力?
第一,增加地方政府財源,擴大征收資源稅和房產稅等。擴大資源稅需要全面理順資源品價格體系,因此,公用事業價格改革是前提;第二,逐步推行財政預算陽光化,限制各級政府支出鋪張浪費;第三,推動財稅體制改革,使得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更加匹配;第四,推動市政建設投融資體制改革,實現建設主體和融資方式多元化;第五,將更多的國有股權劃撥到社會保障領域,彌補社會保障缺口。
從物質角度,城鎮化涵蓋更廣泛內容。當前日益緊張的資源能源環境,如何能滿足未來8億城市居民的消費需求?多個超大城市群和城市帶之間及其內部如何實現功能分工與協調?
從問題出發,我們將中國城鎮化內容歸結為三個方面:一類欠賬問題,這和中國特殊國情或制度扭曲有關,包括,城市化人口未能過上“城市”生活,土地城鎮化遠快于人口城鎮化,城市發展中的低效高耗問題,城市基礎設施分布不合理,大城市發展受限而小城市發展滯后,房地產市場不規范增加城市化成本;第二類是趕超問題,中國城市和其他國家城市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何使城市發展更符合人居生活,包括節能環保、智慧城市等發展潮流;第三類是制度問題,因為城鎮化是個系統工程,制度改進必不可少,包括戶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財稅體制、市政建設投融資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等。
改革啟動城鎮化紅利
從工業化國家發展歷程看,如果各種商品和要素能以市場化方式交易和流動,城鎮化率上升是個自然結果。中國經濟發展至今,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水平,正在由溫飽向小康邁進,直接進行需求刺激的空間已經不大,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在于消費升級和技術進步拉動產業升級。
兩方面都指向要素市場化。要素市場化是實現“供給創造需求”的關鍵,生產潛力發揮,各要素獲得與貢獻相匹配的收入,需求自然能增加;要素市場通過市場選擇使資源集中到效率高的企業和產業,推動技術進步。
城鎮化是實現要素市場化的推手。勞動方面,城鎮化將給予全國居民更均等的社會保障,促進勞動力流動,保障勞動者權益和鼓勵創業;土地方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意味著增加土地流轉自由度,賦予土地使用權人更多權益;資金方面,促進民間投資意味著給予國民平等金融待遇,利率市場化使得資金價格更能反映其稀缺程度,流向更有效率生產領域;稅制改革和公用事業價格改革也將促進資源能源的集約使用。財稅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助于減少政府對市場體系的干預。
改革可以使城鎮化回歸到一個自然提升過程,只有改革才能突破城鎮化的現實約束。值得注意的是,局部領域的改革正在推進。2012年11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12月初,媒體報道發改委已向國務院上報煤電價格并軌方案。只有當類似更多改革被推出時,一個8億城市居民、靠消費和服務業推動的巨型經濟體才值得期待。
作者李迅雷為海通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陳勇為首席宏觀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