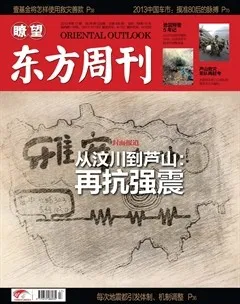美好社會的密碼
2012年底,我在北京參加一個思想沙龍。與會者多是這些年來在公共領域較為活躍的歌手、導演、商人、網絡精英、學者及出版人。那天的活動持續了很長時間,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個“中國夢”環節,主持人讓最后上臺的幾位嘉賓談自己關于中國未來十年的夢想。
這樣富有時代特征的氛圍與場景,對我來說實在太過熟悉。和往常一樣,大家集中表達的多是希望自己能夠生活在一個既安全又有尊嚴的國家,那里有成熟的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多元文化、民主政治,以及持久保障的人權、法治、自由,等等。
還記得1984年,張明敏唱《我的中國心》時的情景。從中國心到中國夢,跨越三十年。不同的是,中國心是以中國塑造中國人,而中國夢是以夢想塑造中國。前者連接過去,后者面向未來。

美國夢,中國夢
這個環節也讓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看到的一份有關美國夢的民調結果。
據《今日美國》報道,24%的人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美國夢,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夠實現美國夢,15%的人表示毫無希望,21%的人表示對此并不關心。
什么是美國夢?這個詞最初是1931年由美國歷史學家詹姆士·亞當斯在他的著作《美國史詩》中提出來的。“每個美國人都應該有機會實現他的美國夢。”“美國夢不是物質豐裕的夢想”,他繼續寫道,更是一種“社會秩序,在這種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能夠以其天賦與能力來獲得他的成就,而且他們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認可,不論他們出生的環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我不知道類似的問卷在中國會得到一個怎樣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美國夢,還是中國夢,它是有關國家的夢想,更是個人的夢想。而國家的價值,正在于提供一種相對公正的秩序,使身處其中的個人不必為上訪和躲避城管浪費時間甚至丟掉性命,而是專心于實現自己的夢想。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談中國夢,這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辭尖刻的言論,也是國家賴以上進的動力。
你是否實現了中國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個人還好,至于這個國家,讓我再想想……這是許多人的態度。至于這片土地未來怎樣,是即將到來的崩潰還是持久的繁榮,沒有誰準確地預言過。正如過去十幾年來我們所見證的,這個國家有太多的變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一日千里,有些方面千年不變。
也有人說,“我的中國夢就是在中國多賺點錢,能夠早日移民美國實現美國夢”。這不是簡單的自我解嘲,而是許多人的真實想法或者生活抉擇。伴隨著社會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不過,在國外我也遇到許多華人,他們苦于去留兩難:對異國若即若離,對故鄉藕斷絲連。就像韓素音在《瑰寶》里說的一樣:“我的一生將永遠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之間奔跑:離開愛,奔向愛;離開中國,奔向中國。”
這個社會會好嗎?無論是準備離開或回到中國的人,還是久居此地的人,都會經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里的水、空氣以及食品的質量問題,什么時候會有所改善?不受約束的權力,什么時候能夠被關進籠子里?中國會像過去一樣從終點又回到起點,在麥比烏斯圈上徒勞無功地打轉嗎?
光明與黑暗
這個社會會好嗎?
回望各國的發展歷程,以及它們曾經有過的腐朽與曲折,實在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將有一個光明的前途。
我不是為當下中國不好的l18tDtIOeBHlOmH4ySAdrVcU7iR6rB0q0bmHRE2Cfgc=一面辯護,只是從時間與人性的角度看到了歷史的演進與文明的共性。英國出現過羊吃人運動,美國出現過食品危機,日本發生過水俁病,但只要對癥下藥,建立起相應的規則,這些時代的混亂就一一落幕了。問題只在于,那些與正義和秩序相關的規則將在什么時候得以確立。
2012年底,我到美國考察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在投票之前的若干天里,我在美國東中部的幾個城市里問了不少人,他們幾乎都準備將選票投給奧巴馬。理由也差不多,奧巴馬代表公正。然而為什么幾個月來美國的媒體和民調機構都在告訴我另一個事實,奧巴馬與羅姆尼的票數可能一半對一半,甚至有可能會重演十二年前布什對陣戈爾時各勝一籌的尷尬局面,即羅姆尼贏了民眾票,而奧巴馬贏了選舉人票。
這個現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支持羅姆尼的人哪里去了?為什么我很少遇到?當然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抽樣有偏差,因為那些天我接觸更多的是美國社會的底層,是少數族裔。事實也是如此,投票日的出口民調結果表明,超過九成的非裔、七成以上的西班牙裔美國人都投了奧巴馬。
我沒有預測錯大選的結果,奧巴馬的確獲得了連任。但是上面的這個細節在不經意間解開了我關于中國的另一個疑團。
過去幾年間,我在中國接觸了許多人,記者、知識分子、官員、律師、商人、學生以及義工,等等。問題是,為什么中國有這么多人希望朝著一個開闊的地方去,可是相關改革卻舉步維艱?只是因為利益集團作祟,或者有理想的人沒有組織起來嗎?
前面說了,我的抽樣有點小問題。所謂人以群分,如果我僅以眼前接觸的人來判斷中國的未來,以為90%的人想的都和我一樣,那可真是大錯特錯了。一方面,有太多的做著黑暗勾當的人我從來沒有接觸到;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我所遇到的人,在他們身上所呈現出來的光明形象也未必是其精神全貌。不是嗎?一個反感香港人罵內地人是“蝗蟲”的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也有可能為了一己之私而大罵那些爭取異地高考權利的人是“蝗蟲”。
關于人性中的幽暗,美國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在其著作《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中有過精彩論述。是的,人類社會不乏光明之子,但是這些人總是把社會變革想得太過簡單,甚至以為只要像他們這樣的人多做點犧牲,世界就一定會朝著好的方向走。
理論上當然是這樣,但在現實生活中,還有無以計數的黑暗之子,他們看重的是現實利益。如果時候到了,他們會滑向光明之子一邊,如果時候沒到,他們只會死守自己的一城一池,甚至與光明之子勢不兩立。
意識到這一點,就知道社會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可能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鼓掌的人
今天的美國,華盛頓的雕塑隨處可見。以華盛頓為首的美國國父們,對美國獨立及憲政的落實無疑居功至偉。但是,偉大的華盛頓并未成就一切,他雖有能力拒受王冠,卻沒有能力解放黑奴。兩百年后,奧巴馬有朝一日能夠問鼎美國總統,得益于其間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他們是林肯、道格拉斯、羅莎·帕克斯、馬丁·路德·金,還有數以萬計的無名氏。
格萊美獲獎黑人歌手Jay- Z曾這樣深情地說道:“羅莎·帕克斯坐下來了,所以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奧巴馬可以奔跑;奧巴馬奔跑了,所以我們可以飛。”
1955年,黑人婦女羅莎·帕克斯因為占用公交車的“白人專座”而被逮捕。隨后,為了反抗惡法,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發起了罷乘運動。
荷爾普斯有言,“推動世界這部水車運轉的水浪,發源于人跡罕至的地方。”羅莎·帕克斯不會想到,那一天筋疲力盡的她,會以坐下去的方式讓美國黑人站起來。2012年的一天,當奧巴馬在亨利·福特博物館里坐上羅莎·帕克斯坐過的編號為2857的公交車,他作何感想?曾幾何時,那位黑人母親,只因為要在這個座位坐下去,竟然會被逮捕。而現在,有著相同膚色的他,當選了美國總統。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羅莎·帕克斯拒絕讓座的前幾年,有位黑人牧師在公交車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機勒令下車,當他號召車上其他人一同下車以示抗議時,卻無人響應。然而這件事在羅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樣了,許多人參與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來,拒乘公交車。從12月5日起,蒙哥馬利市的4萬黑人開始用各種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走20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車。381天的堅持,不僅改變了美國黑人的地位,也改變了盛行種族主義的美國。
我時常聽人感嘆中國沒有華盛頓,其實沒有又如何?過去沒有不意味著將來沒有。別人不做不意味著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華盛頓,你還可以做馬丁·路德·金。做不了馬丁·路德·金,你還可以做羅莎·帕克斯。做不了羅莎·帕克斯,你還可以做一個為他們鼓掌的人。
如果你連這也做不了,沒關系,你還可以回歸動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婭·奈特所做的那樣,舉起手中的攝像機,保衛自己的孩子。
身處轉型時期,對公平與正義的謀求,正因為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的持久的參與。
假自由泛濫,真責任缺失

荷馬說,“當一個人成為奴隸時,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對此,阿諾德補充說,“當他想擺脫這種奴隸狀態時,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時候會失去自己的美德,人爭取解放的時候也會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針見血的對比著實讓人贊嘆。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個人在被壓迫時卑躬屈膝,喪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時,又變得飛揚跋扈,傷及同類?
從概念上說,它關系到對自由與權利的理解。
托克維爾曾經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嘲笑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為仇恨大于自由,法國大革命最終血流成河。反抗與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種普遍權利,真正的革命不是為了奴役別人,更不是為了殺戮,而是為了建立起一種持久的秩序,以便讓所有人能夠在這種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從歷史上說,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劇終”的革命或者反抗。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當革命因對暴力的迷信而沖出應有的邊界,否定人的意義本身,革命不僅毀壞了過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來的方向。
簡而言之,轉型期的中國,有關自由的思考并未完成。這也是為什么在過去的講座中我多次談到,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就在于假自由泛濫、真責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現為權力大而責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權;在社會方面,則表現為各種底線的缺失,對于可能到來的時代巨變,社會也沒有做好充足的觀念或者心理上的準備。
美國著名心理醫生弗蘭克爾曾經建議美國人不能只在東海岸建一座自由女神像,還應該在西海岸建一座責任女神像。一個從納粹集中營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說最珍視的就是自由,但為什么他還要強調僅有自由是不夠的?因為他知道,與自由對應的還有責任,沒有責任也不會有自由。責任女神像的價值就在于喚起人們的責任感。
所謂美好社會的密碼,無外乎人人能為真自由擔起責任。
我的人生,我的土地
從改革開放,到開放改革,尤其伴隨著全球化的到來,中國的變革少不了外部力量的卷入。前不久,讀到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如果德國的民主受到了威脅,他還會以老邁之軀沖上街壘揮舞拐杖,但如果將民主引進一個發展中國家,他是一點力氣也不愿出的。
我不想將施密特的這段話簡單歸類為國外政客的勢利或者犬儒主義,積極一點說,我更愿意視其為忠告,即不要渴望別人來幫你多做什么,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當務之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而這也正是我寫作這本書的緣起之一。近幾年來,我之所以在各地做有關“這個社會會好嗎”的同題演講或者講座,除了探討當下中國的一些緊要問題,更多的是著眼于將來的建設,希望自己能為這個社會的轉型播下一些種子。雖然力所不逮,憂思之心卻是赤誠的。
相較于講堂前的麥克風,我更喜歡的是書齋里的文字。我不是一個喜歡爭強好勝的人,甚至也不是一個好爭論的人,就像羅曼·羅蘭筆下的奧里維一樣,只希望自己能夠保持目光明亮。奧里維之所以不愿斗爭,并非害怕失敗,而是由于對勝利漠然視之。那個時代,誰反對仇恨,誰就被打成叛徒,謹慎的人被稱為膽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稱為軟弱的人。
今日中國話語暴力與仇恨情緒同樣盛行。這里不僅缺少底線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說的“思想上的英雄主義”;這里不僅缺少中產階級,也缺少中間意見階層。在各種“主張的沖突”中,底線派與中間意見階層往往也是遭受各方誤解和傷害最多的,因為他們離開戰壕,手無寸鐵地走到了槍林彈雨的中央,走到左派與右派、政府與民眾等各方火力的交叉點。
那又能怎樣呢?被民眾圍攻、被朋友孤立,甚至被權力嫉恨,本來就是獨立思想者應受的。客觀上說,這也是其價值所在。
在收筆之前,還是讓我回到故鄉。因為演講的關系,去年底我回了一趟九江,并且再上廬山。這里曾是抗日戰爭時期的重要戰場,遺憾的是,當年廬山孤軍浴血奮戰的故事,漸漸被無知、無情地淡忘。不過,山間有文字的地方總還是免不了讓我感到慰藉與著迷。這里不僅有刻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墓,在東林寺的藏經樓外我還看到這樣一副對聯- - -“自修自持莫道此間非彼岸,即心即佛須知東土是西天。”而且,我立刻喜歡上了這副對聯。
實話實說,我在外地演講的時候曾經借花獻佛,把它贈給了所有在場的聽眾。現在,借著這本書的機緣我也把它獻給所有的讀者。
當時有人問我這副對聯是什么意思,我便自作主張,將它翻譯成了幾句大白話:我將用心于此生此地,這是我的人生,我必讓它圓滿;這是我的土地,我必讓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