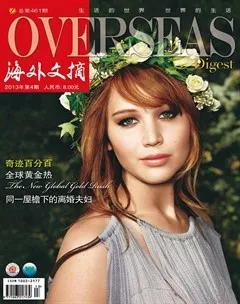同性伴侶的領養之路

和其他孩子聊到自己的家庭時,13歲的小女孩安卡酷酷地說,她有三個媽媽,一個是她的生母,兩個是和她一起生活的媽媽,只是沒有爸爸。
這聽起來有點復雜,其實也很簡單。安卡出生于保加利亞,她的生母在生下她之后立即把她交給領養機構。四歲時,她被室內裝潢師克勞迪婭·佩特斯收養。克勞迪婭和婦科醫生康斯坦茨是同性伴侶。
然而,在法律上,康斯坦茨卻不是安卡的媽媽,她沒有成為安卡監護人的權利。在德國,不論性別、婚姻狀況和性取向,任何個人都可以領養孩子,但同性戀人領養同一個孩子是不被法律允許的。
到目前為止,法律規定保持不變:如果婚姻中的一人領養了一個孩子,另一個也就自然而然成為孩子的法定監護人,而登記注冊了的同性伴侶只和對方的親生孩子有法律關系,領養的孩子則排除在外。卡爾斯魯爾第一參議院必須決定,這種情況是否違憲。如果雙方對孩子都有同等權利,那么就能為同性伴侶有步驟地領養孩子鋪平道路。
幾年來,德國綠黨一直試圖做出改進。2010年在聯邦議會提出相應立法草案,遺憾的是,它直到今天都未成功通過。同年,各州司法部長的提案也被聯邦否決。這個主題涉及婚姻和同性伴侶之間法律平等的基本問題,也涉及更加根本的問題——什么是家庭,它可不可以由媽媽、媽媽、孩子組成?
一個周二,聯邦憲法法院審理康斯坦茨·佩特斯的國家強力侵害訴訟。同時進行的另一個訴訟來自漢堡的一對有著一個十二歲兒子的同性伴侶。他們也是兩人中的一人可以收養這個羅馬尼亞男孩,另一人不可以。
2003年第一次試圖領養孩子時,康斯坦茨和克勞迪婭·佩特斯從未想過她們可能改寫司法歷史。“那時我們都相對悲觀。”康斯坦茨說,“雖然難以接受單人領養,但是我們告訴自己,我們會盡力,其他的會水到渠成。”
58歲的克勞迪婭和53歲的康斯坦茨已經是20年的伴侶。她們連外貌看起來都很相似,都留著短發,帶著無邊框眼鏡。兩人都喜歡潘趣酒,手上帶著同樣的金戒指,只是克勞迪婭戴在右手,康斯坦茨戴在左手。她們于1996年戴上戒指,那時,注冊的伴侶關系還不可能。不久,兩人就希望領養一個孩子。
在明斯特青年福利局,她們得到了必要的文件。2003年早夏,她們第一次驅車來到保加利亞的一個孤兒院,克勞迪婭是領養志愿者,康斯坦茨只是作為給建議的朋友“陪同前來”。她們小心地取下了戒指。兩人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到三歲的小安卡的時刻,“我們馬上就知道,就是她了”。領養成功是在很多次探訪和互相了解情況之后。2004年七月,康斯坦茨和克洛里亞可以帶她們的女兒安卡回德國。
在德國,有領養意愿的伴侶明顯多于可以被領養的孩子數量。因此,青年福利局對領養人給出了嚴格的標準。對個人來說,基本只有在國外領養的可能。
安卡離開孤兒院的時候,還不怎么會說話。她很少在大自然中自由玩耍,而現在她已經是足球協會的守門員。兩位媽媽照顧這個小女孩,周一和周四克勞迪婭負責,周二和周三康斯坦茨負責,其他幾天她們一起負責。女兒管她們倆都叫“媽媽”。
對于康斯坦茨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法律規定得不是特別清楚。而經濟上來說,作為非法律意義上的母親,她和克勞迪婭的權限也有區別,例如她不能獲得子女照料免稅金。雖然萬一克勞迪婭出了什么事,康斯坦茨可能成為安卡的監護人。
“康斯坦茨也能夠領養安卡對我們三人來說有著重要意義”,克勞迪婭說,“我也從來不想一個人對安卡負責。”2005年,她們登記為同性伴侶,進一步創造了領養的前提。但是,不出所料,法院拒絕了這一步。基本養育模式仍然是由父親、母親和孩子組成的家庭給予的兒童教育,哈姆最高法院于2009年底作出了這樣的判決。這證明,同性伴侶和異性夫妻在領養問題上仍然被區別對待。
一年后漢堡最高法院的判決已然不盡相同,一對男同伴侶的類似案件擺在了聯邦憲法法院的決案席上。立法者許可了其中一人對另一人親生孩子的領養權,理由是這“大大改善了孩子的權利”。漢堡最高法院認為,這個理由顯然和“親生孩子”還是“領養的孩子”沒有關系,所以兩宗案件應該有同樣的處理方式。
幾年來,德國聯邦憲法一直在改善同性伴侶的權利。2001年起,同性伴侶可以登記為同性伴侶。2009年強調,對婚姻的憲法特別保護,“不能成為和傳統婚姻不同的共同生活方式享有較少權利的緣由”。2011年2月起,和一個女人登記結婚的柏林法律教授蘇珊娜·巴爾甚至成為判決委員會的一員。
孩子的幸福也不該成為不平等對待的理由。在每次領養中,這一點都該得到審查。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同性伴侶撫養長大的孩子,會受到傷害。相反,聯邦司法部的一份“同性伴侶孩子的生活情況”的研究于2009年得出結論,在同性戀家庭生活的孩子和其他家庭形式的孩子一樣能夠健康地成長。女同律師麗塔·克依倫說,在同性關系中,被其中一人領養的孩子,生活在真實存在的家庭羈絆中,而這種羈絆能夠“通過允許共同領養得到進一步加強”。
克勞迪婭說,這是她們提出“憲法訴訟的主要動力”。和其他孩子相比,安卡受到了歧視,因為她只能擁有雙親中的一個。康斯坦茨強調:“不管憲法是怎樣規定的,我們以前是一個家庭,以后也是。”
[譯自德國《明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