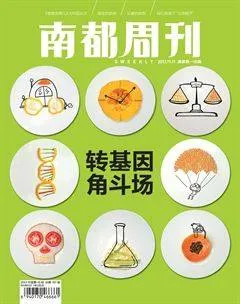怎樣沖擊諾貝爾
廖偉棠
香港作家、詩人。曾出版詩集《野蠻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錦夜行》。
舉國體制,人海戰術,在我國除了足球項目,好像屢試不爽,最近聽說該戰術將投入一個偉大的事業:萬人遴選百人沖擊諾貝爾獎,簡稱“萬人計劃”。
據說這“沖擊”也包括哲學社科甚至文學方面的尖端陣線,我不懂數理化,只知道中國離諾貝爾最近的就是文學——文學得過獎,而且,都和舉國體制無關。就拿莫言來說吧,如果不是“計劃生育”深入外國人人心,《蛙》這部小說應該不會得到那么大的重視,但即使莫言,這樣一個官方色彩濃厚的作家,實際上也是靠個人奮斗得獎。曾有謠傳說,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莫言,是歐洲經濟危機仰賴中國救助,不得不進行的一個諂媚之舉,這真是荒其大謬,且不說歐盟及瑞典是否這么可憐叫花子,以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一貫的獨立精神,他們的評判標準是不會以一時一地的“急難”而傾斜的。
在寄望未來的諾貝爾獎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倒是可以看看什么是真正“有效”的“舉國體制”。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前,我曾預言莫言不可能獲獎,但不幸言錯。針對那些堅持說要從純文學角度看莫言價值的評論者,我的反駁是諾貝爾文學獎從來沒說自己是純文學的,相反它強調的是理想主義。博爾赫斯在1936年阿根廷《家庭》雜志的專欄上,寫到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金·奧尼爾時,對諾貝爾文學獎有此判斷:“諾貝爾獎的規定有這么一條……應該不考慮作者的國籍,給予最出色的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最后一個條件是最沒有辦法的,天底下沒有哪一本書不可以被稱作‘理想主義’的。”
莫言恰恰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龐大寫作只符合博爾赫斯對“理想主義書寫”的定義:博爾赫斯指的是,每個作家當他想要創造一個文本世界的時候,他都是懷著一種理想主義去行事的;而對于諾貝爾獎評審委員們,理想主義往往被單純理解為文學內容中一種對世界的信心,甚至樂觀主義精神,對世界的一種“好”的影響。
是莫言的作品而不是莫言讓西方讀者誤讀了中國人的中庸和犬儒是樂觀主義;是莫言而不是莫言的作品更令一個中國讀者驚嘆而反思自身,這自身自動成為了一個塑造國民共性的“舉國體制”的一部分。莫言,是他那一代中國人的典型、集大成者,包括其老實與圓滑,其忍辱與耍潑,其充沛與虛無,其應聲與沉默,其謹小慎微與磅礴——這一切在他自身和作品身上混雜而生,并且唇亡齒寒地互生。
莫言是一個裝睡的人,但他比別的裝睡者感覺良好之處在于,他更會做夢。于是他的一切都可以用講故事這一曖昧的方式來帶過。這種曖昧有著純文學的名義,卻是最“媚俗”的、回避政治的純文學。
莫言得獎后曾說: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那是他對政治的誤讀。且不說《尚書·畢命》有“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之正義,孫中山用“政治”對譯Politics,亦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同是諾貝爾獲獎者的赫塔·米勒,她的政治性絲毫沒有抵消文學的美。她在獲獎演說里也講了關于媽媽的樸素故事,但仍然是關于尊嚴的,是福克納、聶魯達、艾略特、布洛茨基等無數獲獎者在獲獎演說都強調的:寫作者的尊嚴,人的尊嚴。
舉國體制,恰恰與人性無關,且看舉國體制沖擊體育金牌的背面那些失敗者、過時者的辛酸,就可以得知,與其傾一國之力催谷一百個高端人才,不如在普及教育上注入比現在可憐的預算更大的力量——不妨以三百萬計劃取代萬人計劃:中國現在學齡少年兒童有三億多人,按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提供的失學兒童比例計算,失學兒童約有三百萬人,誰敢說這三百萬如果能得到教育,里面沒有一個可能是未來的諾貝爾得主?這三億人要是能得到更充足的教育,那更是不得了。
國家不幸詩人幸,現在中國的許多毛病正是當年一個個另類的舉國體制“運動”的殘留物,它們給今天的文學家提供了大量苦難的素材,照這樣下去,中國不久再出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絕非不可能。但作為一個中國人,還是不希望再有更多以苦難兌換回來的榮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