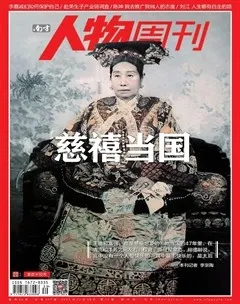馬友友 走出殿堂,遠游世界
暌違一年,馬友友再次來中國演出,演奏的是全新作品《度》。這部大提琴與笙雙協奏曲秉承了馬友友“絲綢之路樂團”作品的主題和神韻,與馬友友搭檔的是中國音樂人、笙演奏家吳彤。2000年,吳彤在美國結識馬友友,并成為絲綢之路樂團創團成員之一。11月6日晚,馬友友、吳彤以及《度》聯合委約方之一廣州交響樂團,在星海音樂廳共同完成了這部極具宗教色彩的跨界之作。
《度》取材于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由作曲家趙麟在研讀該書一年后創作完成。整部作品由《相》、《喜》、《悟》3個樂章構成,大提琴詮釋的是人性,笙作為古時的廟堂樂器,則代表了神性的部分。人性和神性時而交替、時而相融,慢慢牽出一條通往信仰的求索之路。
早已躋身頂尖大提琴演奏家的馬友友,近年來的音樂實踐似乎也在向世界傳達他個人的某種愿望,即通過音樂促成人類更大范圍的溝通與對話。如果說早年演奏經典作品讓馬友友享譽國際樂壇,那么這些年的跨界實驗則使他在更大范圍內獲得了影響力。
不知道馬友友本人是否會將這些跨界之作視為在音樂上的朝圣之旅,但他卻無可爭議地被人們稱為“音樂界的馬可·波羅”。他曾經為生活在卡拉哈利沙漠灌木叢里的人演奏,也曾跟來自伊朗、蒙古、韓國、中國和阿塞拜疆的民族藝術家同臺演出。與他一起錄制過專輯的,包括阿巴拉契亞山脈的提琴手、阿根廷探戈吉他手和印度塔不拉鼓鼓手。若干年前,美國《行列》周刊的蓋利·赫西這樣描述馬友友,“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離開過古典音樂:他錄制了五十多張專輯,獲得過16個格萊美獎。但與此同時,在過去的40年中,強烈的好奇心和音樂使命感驅使他走出古典音樂殿堂,遠游世界。”
“9·11”事件發生一個月后,馬友友和搭檔們接到去敘利亞演出的邀請。由于資金、簽證的問題,馬友友曾考慮過放棄,但最后還是堅持了下來。音樂會一場接一場地辦,他形容每天都要重下決心,反復問自己要不要堅持。
最后,馬友友找到了堅持的理由。他告訴蓋利·赫西,與他共事的音樂人里有位來自蒙古的唱長調的女歌唱家,曲風嘹亮而又動聽。她是家中老大,底下還有很多兄弟姐妹。有一年,蒙古大旱,死了一百萬頭牲畜。令馬友友難忘的是,即使在生活幾乎陷入絕境的時候,女歌唱家仍然沒有放棄音樂,照樣和他們一起旅行,一起演出。
在廣州站演出的最后,觀眾的掌聲久久沒有平息。忽然,坐在我右邊的一位歐洲女觀眾站了起來,從觀眾席跑到臺前,將一束小花遞向馬友友。也許,這樣的小花束也會成為他遠游世界、傳播音樂種子的力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