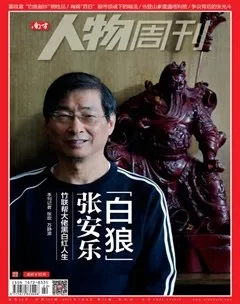葡萄幾時能熟透?
不管你承不承認,眼下影視話題的風頭都屬于《小時代》們。在它們強勢攻占網絡內外大小陣地后,同期亮相的其他作品的確很難抓住眼球。就像渾不吝的倔強主人公王葡萄一樣,電視劇《第九個寡婦》在這個當口,登陸衛視上星播出了。
數年前,當作家嚴歌苓的“新移民寫作”陷入瓶頸時,在父親的提醒下,她果斷選擇了更加突出白描和人物形象的寫作嘗試。2006年3月,轉型之作《第九個寡婦》正式發表,她稱其為“最看重的一部作品”。7年后,同名電視劇面世,演員葉璇用這部自己一讀便放不下的小說開始了職業轉型,首次出任制片人。
一問世便斬獲當年《中華讀書報》“年度優秀長篇小說”獎的原著,誠如葉璇所言,“具備一切熱播改編元素”。嚴歌苓筆下的王葡萄,既是一個從不知恐懼為何物、只知道要活下去的“生胚子”(嚴歌苓語),也是一個輾轉在時代洪流,和幾個男人發生愛恨情仇的鄉村尤物。這段葡萄用紅薯窖保護公公近半個世紀的生命傳奇,脫胎于嚴歌苓當年在河南的生活經歷,因而既奇情又真切。畫面感極強的文字勾勒,幾乎已經讓中原大地的人間煙火呼之欲出。
當然,對包括葉璇在內的任何一個影視人來說,《第九個寡婦》都是難啃的骨頭。當年獲得“最受網友喜歡”的原著,在沖突密集、張力充沛的敘事背后,還深藏了作家拷問歷史以及對男女秩序和傳統倫理的深刻追問。
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電視劇版沒有像原著那樣,將時間軸橫跨抗戰到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而是在解放之后迅速止筆。同樣的原因,電視改編也大幅收緊了情欲描寫的尺度。壓縮歷史跨度之后,在王葡萄感情世界里登場的男人很難像原著那樣多達數位,國產劇的主流收視人群顯然也不會接受主人公在這方面的膽大和率性。
作為原著的一個局部展示,電視劇版做得最成功的地方,是基本忠實還原了孫懷清和王葡萄這兩個最重要的人物:一個符合大眾想象,精明強干、堅韌善良且勇于擔當的民間傳統男性角色,和一個身懷巨大生命能量卻渾然不知的傳奇女性形象。一個別無選擇淪為歷史的人質,另一個始終用自己的活法,沉默不覺地頑強對抗。
初膺制片大任的葉璇,將剪紙、染坊、浣紗、中原小吃、時令節氣等民俗展示納于劇中,也在影視城外景之外,選擇山清水秀的瀑布實景,讓電視劇版在提供視覺展示的同時,盡可能接近原著里緊緊植根大地的鄉土氣息。
作為制片界新人葉璇領銜的第一部長篇作品,《第九個寡婦》在制作上當然不乏稚嫩和精進之處,但它最可貴的價值,是在游戲化和無深度日漸獨霸電視的當下,在接受收視為王的游戲規則之后,力圖重振國產劇幾近絕跡的文學精神和人文情懷。很遺憾,她和團隊初生牛犢般的付出,在播出版粗暴的刪減之下大打折扣。如果說賬房先生上一場戲剛剛喪子下一場就笑呵呵登門拜年只是讓人哭笑不得的話,播出版中很多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銜接就徹底匪夷所思了。
“把該做的,變成喜歡做的。”葉璇應該是借劇中葡萄這句臺詞直抒胸臆。原本觀眾可以吃一些熟得更好的葡萄,只是在相親、選秀和雷劇當道的今天,嚴肅創作舉步維艱,佳作誕生的可能越來越聽天由命。真不知道,那些葡萄幾時能熟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