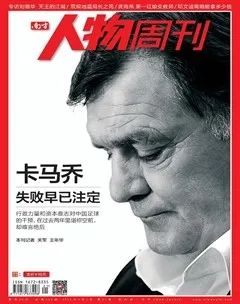季琦 每個企業背后都有哲學

我又回來了
四年不見,季琦臉上的線條硬了一些,眼神柔了一些。那件黑色絲質恤衫的肩部有一個別致的設計,配有一粒小扣子,很容易吸引目光;那條暗紅色的長圍巾和改良中式外套,都是加分搭配——從前專注的Timber-land已讓位于“上下”,這讓他周身有了一種人到中年的從容文雅。
2009年,43歲的季琦辭去CEO。2010年漢庭在紐約納斯達克上市。2011年,漢庭新開酒店201家,如家和7天分別是301、376家。2012年初,季琦重新出任CEO,開始“蛻變”的一年。訪談便從“季琦歸來”說起。
我又回來了。原來一直以為自己適合創業,而做大、做規范了之后,可能要找職業經理人來打理公司。上市以后,大概有兩年時間吧,我基本都不參與公司的日常管理。
從管理來說,我們的前任CEO做得不錯的,但總感覺這個企業過早進入了成熟期。就像從前Andrew Grove(注:英特爾公司前首席執行官)說英特爾是“10倍速”增長的企業,我們這個行業幾乎也是,所以不能過快地進入規范、成熟、中年或是老化的過程。看同行,都在不斷創新,不斷突破自我,很積極。相對而言,前幾年我們就過早地步入中年了。我覺得這個不對,慢慢開始介入日常事務,就會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而且我發現這個不是小敲小打就能夠解決問題的。要從根本上來調整,我就必須回到CEO的位子上。
企業需要每一個高管都是發動機,而不是傳聲筒。我請來解云航擔任新COO,神州數碼的總經理,他早年在聯想,是柳傳志團隊培養的這么一個人。許多企業找人兩個趨向:一類是創業階段的草莽,很多人大學剛畢業或者在外面做點小生意,沒有在大公司干過;另一類是在外企。其實還有一類企業的人才,可能更適合。像華為、聯想這一類優秀民企。這些企業相對生存的時間比較長,而且有很強的企業文化,它們培養的人蠻適合我們這些本土成長的企業。
很多企業都有老人的問題,通用有,華為也有。我和他們看企業的角度不一樣,沒有對和錯,只是立場不一樣。
季琦悟到的第二條是,如果想開百年老店,創始人不能離開公司,不能脫離公司實際事務。
創始人必須“趴那兒干活”
做成了三家上市公司,有人問我要不要做第四個,我說有什么意義呢?把企業做大做強做持久,做成一個有長期競爭力的品牌,這才是對我的真正挑戰。很多人可能覺得,上市完成,股份賣出,賺錢了,OK了。我現在不會這么想。要長久發展,沒有大股東主導或創始人在公司,是比較困難的。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國際上前十的酒店集團,凡是沒有破產、被兼并、收購過的,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創始人的長期投入或穩定的單一大股東,純粹依賴職業經理人,順利的很少。洲際、雅高、萬豪、希爾頓、Starwood……我們這個行業實踐性太強,太具體了,必須有大股東在,必須有個創始人很辛苦很累地趴那兒干活。譬如說選址,你得去現場看,在電腦上看圖片,都跟藝術照一樣,但根據圖片來判斷,經常會出錯,更不用說工程改造和產品設計了,包括對顧客和員工的理解,你也得始終在一線。
比方我回來之后,就想統計一下客戶的年齡比例。出乎意料,其實也在意料之中——50%以上都是80后或者是90后。但10年前,我剛剛做酒店的時候,客戶群的大部分是60后和70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80、90后沒有商務、旅游、休閑的明顯區分,他們都是混搭,出差的時候順便玩一玩,玩的時候也順便把正事給辦了。他們的旅游、度假、郊游要比我們60、70后開放、自由很多。
既然客戶群不一樣了,溝通方式和產品設計也就不一樣了。回來之后,我做了很多這樣的決策,比如說不能再擴大呼叫中心了,現在都是智能手機,沒有APP、Wifi,你還跟他搞啥。所以我馬上就把APP收回來自己開發,不再外包。以前我們的產品設計比較穩健、商務一些,現在也在改變。
跟馬云“趁著頭腦還清醒,趕緊退休”的認識不同,季琦認定創始人必須“趴那兒干活”。他每年有一兩個月在飛行,到一個城市,出了機場,看火車站在哪里,商圈、新區在哪里;看主要的顧客,也看物業。他去了丹東,于是那里的布點很成功,盈利也非常好。喀什沒人敢去,他去了,于是清真寺旁邊就將有漢庭……創業、守業,以及人,都是活的,沒有金科玉律可以套用,一切定律也只是在一段時空內才算得上恒定。


根據理解去豐富需求
在季琦的博客上,有一篇《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是根據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整理、引申的。他在文中寫道:“中國的社會階層從組成結構上看,肯定不是一個橄欖形,也不是金字塔……我倒覺得有點像不倒翁,雖說不容易保持平衡,但也不可能完全傾倒。而最有效的作用點在上部,給很小的力,這個不倒翁就會晃得很厲害。”這可以解釋這位企業家多年來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理解,以及他的決策。
我看得清楚,中國的經濟型酒店市場未來是非常巨大的,全球最大,數量上最大。還可以看清楚,這兩年大家出差也好,出門也好,都想往好了住。這個就是對社會的感覺和敏銳程度,當然每個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有些同行還拼命往三線四線城市去,我可能就不往那兒去,因為我沒有相應的能力去覆蓋三四線的城市,那是多大的工程啊,馬云那個配送網絡將來可能會做到,我覺得我們很難做到。
我老家就是屬于我們定義的四線城市。在那兒找房子,怎么可能找得過當地人啊,一個鎮上的人,抬頭不見低頭見,不是同學、親戚,就是同事、朋友。人家(租金)八毛,我可能就要一塊。辦各種證照,估計我們的效率也要比當地人低。縣城的市場容量有限,我們開一家到兩家,要花這么大的成本去做,那么我就只能放棄三線和四線城市的直營,而將這些市場讓給當地的合作伙伴……做企業,離不開對社會、對國家、對政策的理解,但這里面是有差異的。我根據自己的理解去捕捉機會需求,調整產品,調整戰略。
看中國近五年?很清晰:城市化,造新城,老城空心化,新區興起;80后90后成為消費者主體;消費升級。
這十多年來,酒店業是兩頭熱中間冷,上面是外資的高檔、豪華酒店,下面是經濟型酒店,中間的價格上不去,住宿率也上不來,很慘。很多人說這是個魔咒,覺得中檔酒店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但我回來以后,覺得消費在變。像60后、70后還在住酒店的,想住好一點,就碰到問題,不知道住什么樣的。現有中檔酒店品質不一,這時候需要好的品牌來突破。我也對60-70年代的客戶群相對了解,他們要什么,哪些是關鍵,我容易與他們共鳴。
我花很大力氣打造全季,一開始有些人覺得是經濟型酒店的升級版,但我希望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裝修品質上,比如說用墻紙不用涂料,家具用實木而不是板材,公共區域開始有品位了,包括大樓也很漂亮。審美上沿用我的喜好,簡潔,帶點禪意,因為現代人太累、太復雜了。那么干干凈凈、安安靜靜、好好睡個覺。大家有機會可以到我們上海的伊犁路全季去看看,體驗一下,跟經濟型酒店完全是不一樣的概念。
再過10年、15年,這家公司靠什么來掙錢?這是我必須想的。集團更名(漢庭改為華住),因為人家已經記住漢庭是一個經濟型酒店,如果繼續用這個名字,往上走會非常累。我至少還要往上走兩步,投入“全季”,試水“禧玥”(華住集團旗下的兩個中高檔品牌),未來可能再新創或收購一個豪華品牌,我們必須在中高檔酒店市場布局。希望未來我們的中檔酒店和雅高的諾富特、萬豪的萬怡一樣,占整個公司盈利的1/3以上。
學習為了求真
離開校園之后,季琦仍然保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像許多企業家一樣,他看書很雜,從王陽明到熊彼特到霍金,從“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到“顛覆性創新”。他說,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都是他的養分。他說,學習是為了求真,知道是怎么回事,進而盡善、至美。不久前,從麗江返回,他開始向公司員工講真善美的哲學——在這樣一個時代,說出這三個字,需要有點勇氣。
這四五年,我的心態就慢慢平靜了很多。原來是騎馬打天下,擴張擴張,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現在,我已經有了足夠的安全感,不用跟人斗智斗勇,眼睛里也不是只有“成功”。人到了這個年紀,可以靜下來看看自己的內心:我要什么,要成為什么;從哪兒來,要到哪里去;我要什么樣的生活。
人到了這個年紀,也不再拘泥于那些口才啊,技巧啊。我覺得這個宇宙、這個世界自有規律。我的哲學里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叢林法則”。很多人以為“叢林法則”僅僅是你死我活,弱肉強食,他們忽視了“叢林法則”的另一面——“共生法則”:就是大樹會和苔蘚、小草、灌木叢、鮮花一起生長。沒有這些,大樹的營養就沒法來;這些東西沒有大樹的庇護,也沒法存活。一顆參天大樹,在成長的過程中,跟同類爭奪陽光、雨露,失敗者只能萎縮、折斷、腐朽。最后,在大樹的周圍形成一個多姿多彩、繁榮和諧的共生世界。一個社會你往廣了看,那就是一個多彩的共生叢林。要做一個偉大的企業,就必須會和社會各態共生,自私自利、唯我獨尊是不行的。
你剛剛問怎么樣去說服、打動“資源人”,我覺得就是共生共贏啊。每一個交往、交易、相處,都是共生原則的試驗場。夫妻、父子、戀人、公司企業之間,都是共生關系。學會共生,這個世界才會和諧。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合作,就會心平氣和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