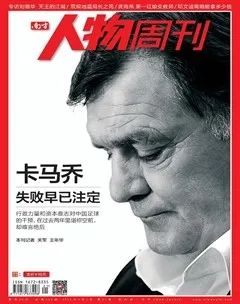路過鄧文迪

她不是徐州人,“從來也不提自己是徐州人”。1968年出生于山東外婆家,父親東莞人,徐州時天真爛漫的鄧文迪,名叫“鄧文革”。
童年師友對她只字不提徐州心懷芥蒂,轉瞬又意識到:“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好壞都是別人的事。”每個人都想說點什么,又都欲言又止拿捏著“兩個世界”的分寸。
鄧文迪路過徐州,三三兩兩的師友路過她,打個照面各自走散。在這座男人們自稱“女性強勢”的“漢城”,說到她,有人就說起呂雉。
一個時空
紅色墻磚爬滿黑色灰塵,顯眼處幾行橫七豎八的標語:“不要亂丟垃圾”、“偷衣服的人變態(tài)”……樓前雜草叢生,樓內傳出炒菜的市井之聲,小區(qū)樓宇間,兩排蔬菜攤一字排開——這座70年代的3層小樓里藏著鄧文迪貌不驚人的童年。
3單元201,徐小燕印象中不過50平方米,住著鄧家6口人。“獨立衛(wèi)生間的房子在七八十年代是罕見的,多少人還得半夜跑出門上旱廁呢!”這棟當時專為當?shù)亍爸R分子家庭建起來的房子”,如今成了一片高樓之間的洼地。
這是一戶“書香之家”,父母均為工程師,“家里有別家沒有的書柜,她姐姐那時就學拉小提琴了。”
直到鄧文迪進入徐州市第一中學后,鄧家搬入6層的徐州市工程機械廠宿舍樓,三室一廳的居室才顯得寬敞起來。
這兩處住宅,在兩年前鄧文迪“挺身護夫”后已經(jīng)被當?shù)孛襟w踏破門檻。當?shù)貎杉叶际袌蟊俪鰺峋€尋找鄧的師友,連載追蹤多期。師友們并不熱情,“隊友同學老師不愿詳談鄧文迪”成為報章標題。
兩位年老退休的排球教練,反倒坦然許多。1981年,鄧文迪進入徐州青少年業(yè)余體校學習排球。這一年,中國女排在第三屆世界杯中首次獲得冠軍,隨后幾年,“五連冠”將中國在體育比賽中的榮譽推向頂峰。而鄧文迪和另外15名女孩也一起被列入體校“省助重點班”。
高一,1.74米的身高讓鄧文迪在同齡人中顯得扎眼。徐州市第一中學的排球教練蔣立模覺得她有排球基礎,將其選入校排球隊。
“她學動作快,課后會單獨來找我問,其他隊員不會。”很快,鄧進入前排扣殺進攻的主力位置。“十六七人,上場僅有6人,一般都是不停輪換,她就有辦法長時間留在場上。就是讓你沒什么可挑剔的。”球隊很快獲得徐州市第一名,參加江蘇省比賽奪得第二名。
在徐州青少年業(yè)余體校,“她是2號位,副攻”。王重生保留了鄧文迪當年零散的學習檔案:1982年,鄧文迪領的鞋子是39碼;1983年,鄧文迪的身高1.74米,英語成績最好。1983年2月,王重生家訪鄧文迪,她的英語期末考試得了91.5分。
每個姑娘都懷揣著“鐵榔頭”的夢想,早上5:30帶一個裝著早飯的保溫杯出門訓練,7:00結束后吃早飯;下午兩節(jié)課后繼續(xù)訓練。
鄧文迪比排球隊的其他隊員年長,“總是很老練,也比其他隊員有心機”。蔣立模常常故意找地上有臟水的位置扣殺,“別的隊員會怕臟不救球,她不會。”
蔣立模從電視里看到鄧兩年前起身護夫的一巴掌,“那就是一個排球的扣殺動作啊!”
幾年前,學校百年校慶,讓蔣立模請鄧回校,他沒有請她。事實上,鄧大學畢業(yè)后,便沒再與他聯(lián)系。“大學時還會寫信來說說情況,說她在學生會體育部,還讓我給她寫證明,申請獎學金。”
缺席校慶,讓學校老師對她耿耿于懷:“她從來不提徐州一中,校慶也沒有來。”同樣的微詞也出席在她的大學——廣州醫(yī)學院。
高二,鄧家隨父親工作調動舉家搬遷至廣州,為完成學業(yè),鄧文迪一個人留在徐州。搬家時,她把家中栽的幾盆花移送給了蔣立模。廣州醫(yī)學院的履歷,鄧文迪同樣緘口不提,讓大學輔導員難以理解。
此后中學和大學的師生都不愿再提她,在報紙上匿名留言稱:“她不提,我們也不愿提起她。”
老師記憶里,鄧的成績都不差,“一中是她自己考的,沒有照顧。惟一有下降是在業(yè)余體校住校訓練時。權衡再三,她決定放棄排球,專心準備高考。”在這座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學校門口,如今站滿分發(fā)雅思托福材料的培訓機構人員,出國成為鄧文迪中學校友的時尚。
十多年前,鄧文迪惟一一次回徐州,此時她已赴美8年。隊友蔡靜波向當?shù)孛襟w稱:“大家發(fā)現(xiàn),眼前的鄧文迪變了。見面后不是握手,而是和外國人一樣擁抱。”
兩個世界
隊友曹方平不愿談鄧,雖然與鄧的交往一直持續(xù)到她離開李寧公司。“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過我眼前平淡的生活。”她和大多數(shù)鄧早年朋友一樣,生怕被說“想與她攀關系”。
同處“這個世界”的徐小燕是鄧在旭光小區(qū)的玩伴。一起玩的還有患小兒麻痹癥的陳雅敏。相互等著一同上學、放學,完成作業(yè)后在院子里丟沙包、斗樹葉。“她就是好強啊,什么都要最好的。跳皮筋她都要最好的。”同學之間偶爾抱怨一句:“考試好難!”鄧總像小大人一樣回應:“那也必須考好啊!”
在旭光小區(qū),鄧家并不與人接觸,父親和善不多話,母親有些清高,兩個姐姐文靜,弟弟身體孱弱,要姐姐背著上學。惟獨鄧文迪“很潑辣,爭強好勝,凡事都要隨她”。
雖然比鄧文迪大一歲,徐小燕常常跟不上她的步伐,鄧常沖她喊:“你不走,我先往前去看看啦。”
那年夏天,兩個女孩在小區(qū)附近的民兵訓練基地玩,在一個池子邊,鄧伸手晃幾下水,問:“敢不敢往下跳!”徐小燕恐懼地搖搖頭,還來不及反應,鄧文迪已拉她趔趄著蹦入池子。“我完全不知道池子有多深,池子里也常有蛇和螞蝗。”徐小燕嚇懵了,愣神半天才發(fā)現(xiàn)水只淹到膝蓋,鄧文迪卻笑開了。
2004年,鄧文迪通過科技手段獲得第一個女兒時,徐小燕陪在孤獨癥的兒子身邊已經(jīng)10年。
“就是一個定時炸彈,他沒有語言表達,家里一切能摔的東西都是他表達情緒的中介。”家中的一切容器都是鋁合金或者塑料,包括紙巾、杯碗在內的器具都被徐小燕塞入柜中鎖起來,“免得被他砸”。
“雖然沒有表達,孩子能敏感地獲知身邊的氛圍。”當徐小燕在電視中看著鄧文迪穿梭在上流社會的慈善晚宴時,冷不丁的砰砰聲卻令她習以為常;鄧文迪與“虎媽”暢談育兒經(jīng)的事,徐小燕是從報上獲知的,她想到自己辭去會計工作在家中照顧19歲的兒子,像“鼠媽”一樣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怕稍有差錯就刺激了兒子”。為了讓兒子感受蹦跳的感覺,每日兩次,徐小燕將1.80米的他拖上蹦床,“扶著他一起蹦。他甚至不會大小便,家里長期處于無序狀態(tài)。他連高興,都是突然間的大笑,聽起來挺恐怖的。”
徐小燕把登有鄧文迪的報紙收藏起來,“就像關注某個明星一樣,但那都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