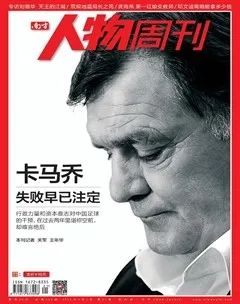無君無父的英雄

幾年前,全球影迷集體接受了一場“重塑美漫英雄”的洗禮:從克里斯托弗·諾蘭掌鏡的新蝙蝠俠身上,我們看到了童年陰影、無父無母、掙扎無助、人性顛覆、自我追溯等要素,這些普世化的人格特質讓影迷對高高在上的英雄從此刮目相看,不由得在“新英雄主義”的魅惑里欲仙欲死。2012年,《蝙蝠俠》系列宣布收官,華納緊鑼密鼓地將“新超人”提上日程,依舊邀約諾蘭掌舵制作人,而后者則選擇以視覺化著稱的扎克·施耐德擔任導演。這個制導組合可謂商業電影內涵與審美的巔峰結合,也讓《超人:鋼鐵之軀》飆升為今夏最期待大片之一。
如果這部電影是個新生兒,它的確繼承了監制諾蘭的深沉、儀式感和施耐德的電玩式視覺美學,但雙方優點卻并未讓電影的“五官”顯得和諧,反而讓這場新超人的危機與贊美詩略顯躊躇、斷裂和不適。
亨利·卡維爾飾演的新超人依然名喚克拉克,依舊五官端正、身形矯健、救人水火、溫情英俊。不過他如蝙蝠俠一樣,充分體現了諾蘭的人物趣味:成年超人出場時如流浪游俠,穿著破敗、滿面胡須,他的狀態空茫無序、憂心忡忡、不知所蹤,因苦于不明身世而游走世界。諾蘭用鐘愛的記憶碎片剪輯法通過幾場閃回講述了童年、少年超人備受身份與能力的困擾,他想大隱于市卻總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又為自己的格格不入而猶豫糾結。電影更增強了現實主義,讓超人身陷社交網絡和信息時代,不再像過去那樣戴個眼鏡就能在普通人與超人間自動切換,被露易絲用幾招記者觀察就曝了光。
影片的前一小時像是一位“諾蘭人物”的困惑與養成,后一小時則進入了扎克·施耐德的狂轟亂炸,這位在《守望者》《美少女特攻隊》中用超華麗的慢鏡頭與電玩感激燃銀幕的導演,此回在與諾蘭的交融中顯得捉襟見肘,一面描摹拳拳到肉的寫實,一面強調空戰戲的炫目,眼花繚亂的城市毀滅、大樓坍塌配上漢斯·季默張力十足的配音,的確讓影院里充斥了鏗鏘有力的聲音,但施耐德的輕盈中和了諾蘭的重拙,讓電影的動作場面毫無獨特感,既不寫意也不寫實,像是《變形金剛》《末日之戰》《黑暗騎士》的雷同混剪版。
《鋼鐵之軀》并非標準意義上的好電影,但也不算陷入淺薄無序的漩渦,它實際上是部反映人們潛意識的表象作品,貫徹了年輕人對酷的信仰法則,又融入了宿命的悲觀——“英雄總歸無君無父”。
父親的死亡對男孩是一種成長教育,新超人遭遇父母雙亡,少年時期受困于超能力帶來的焦灼選擇,是像養父所期望的那樣大隱于市、安穩度日,還是冒著被質疑、圍觀甚至傷害的危險,挺身而出拯救城市與人民?為此,《鋼鐵之軀》安排了養父之死,為遵從養父期望,超人沒有在眾目睽睽下去救他,而是眼睜睜看他淹沒在龍卷風中,之后痛苦哀嚎,此為無父。結尾處,超人親手擰斷了佐德將軍的脖子,他殺死了反派,卻跪在原地再次發出絕望的痛苦哀嚎,盡管佐德將軍為光復母星不擇手段,但他卻是超人不多的同胞之一。因而他的死勉強可以解讀為無君。
無君無父的英雄——這樣的故事讓超人勵志和完美主義的成分逐漸稀釋,更像解構現實。新超人或者說新英雄主義總是在訴說一種孤立無助的焦慮,而最終,無助感總會變成卓爾不群的驕傲,孤獨成就了魅力,也讓他們立起了獨來獨往的價值觀,映襯沒名沒姓的時代,恰如其分。
《薩米大冒險2》
上映日期:6月28日
導演:本·斯塔森
主演:帕特·卡洛爾
伊莎貝拉·弗爾曼
海龜森美與朋友阿威升級做了爺爺,卻不小心被人類捉住。被困監倉的他們認識了很多有趣的海洋朋友,大家各出奇謀,誓要重拾自由。
《初戀未滿》
上映日期:7月4日
導演:劉娟
主演:張含韻 冉超
6個即將面臨高考的中學生,憧憬著各自的未來。因為一首歌及一次意外,董啾啾與夏靜寒產生了交集,也讓好友關系發生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