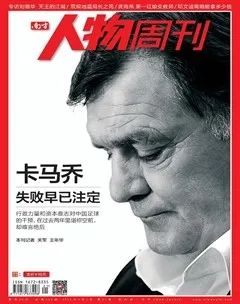“鳴笛示警”的意義
英國經典政治小說《Yes, Minister》中有句名言:“《官方機密法》不是用來保護機密,它只是用來保護官方而已。”所謂保護國家機密安全,很多時候只是政權的遮羞布。
近日,大爆美國政府如何監(jiān)控國民通訊、入侵別國計算機黑幕的前中央情報局人員、國防承包商雇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選擇香港這個他所稱的言論自由之地,作為揭秘基地。雇員泄密這種行為的正當性,在香港引發(fā)議論,有人視他為英雄,也有人視他為叛徒,甚至是賣國賊。
員工對機構內的不道德、濫權、瀆職,甚至違法行為看不過眼,為讓公眾利益得到伸張,不惜觸犯內部紀律和保密原則,向外界(如媒體、監(jiān)管機構、國會等)泄露風聲,揭發(fā)劣行,阻撓相關行為,以防問題變本加厲,英文稱之為“whistle blowing”,有人譯作“鳴笛示警”,更傳神的譯為“泄密揭發(fā)劣行”,香港人則習慣稱之為“爆料”。它源于英式社會,人們見到罪案發(fā)生,便會鳴笛,警示執(zhí)法者及公眾,犯罪行為正在發(fā)生,對社會構成危害。
在美國,為了公眾利益而泄密以揭發(fā)劣行,最著名的例K18ymQ81sLhO0HibQTcroPlDr2gxGgPYZ7hm0wKSAq4=子,是《五角大廈文件》案。
1967年,美國國防部組織了一群專家學者,秘密編寫有關美國卷入越戰(zhàn)的來龍去脈,以供決策者參考。Daniel Ellsberg是其中一位參與者,他發(fā)現美國政府其實是因決策錯誤,才墮入越戰(zhàn)泥沼。為掩飾失誤,政府向國民說了大量謊話。嘗試其他方法無效后,為制止謊言,早日結束越戰(zhàn),他把有關文件——后來被美國人稱為《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交給記者,期望相關信息曝光后,可以喚醒公眾,繼而向政府施壓,結束這場錯誤的戰(zhàn)爭。
1971年6月,《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先后轉載了這些文件,引起尼克松政府恐慌,立即申請禁制令,官司最后鬧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6月30日作出判決,以6比3宣判政府敗訴,并撤銷了禁制令。這便是美國歷史上有名的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案件。
最高法院認為任何類似形式的禁制,都有違反憲法賦予新聞自由的嫌疑,因此須特別謹慎,必須由政府負起繁重的舉證責任,提供強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其必要性。但在此案件中,政府明顯達不到這個嚴格要求,它不能證明有關報道為國家安全帶來“一個清晰并且迫在眉睫的危險”。
最高法院法官Potter Stewart在其個人判詞中指出,問題是否出于政府已習慣把太多事情列為機密?當政府漸漸把鑄有機密字樣的圖章習慣性蓋在所有文件上時,難道不是荒謬嗎?特別是當政府官員包括總統(tǒng)自己,常選擇性向外界泄露這些所謂機密資料,以博取政治分數時,這不是進一步顯示了制度的荒謬嗎?
另一位法官Byron White持相同意見:“當所有事情都是機密的時候,那么就再沒什么事情真的是機密了。”
法官Douglas也指出:“政府的所謂機密,往往都是反民主的,只是用來持續(xù)官僚的錯誤。因此公開的討論對國家的健康發(fā)展是必須的。”
時間證明,《五角大廈文件》的公開,對國家安全構成的危害,可說是微乎其微。18年后,尼克松政府的首席檢察官終于良心發(fā)現,承認當時他們過慮了,他甚至說,很多把資料列入機密范圍的官員,通常不是真的為國家安全考慮,而是為避免政府部門的尷尬和難堪。
就在尼克松執(zhí)政期間,發(fā)生了“水門事件”。當時,《華盛頓郵報》記者在政府內部一位“線人”供料情況下,展開深入調查,最終揭發(fā)了水門丑聞,讓尼克松下臺,幕僚長H. Haldeman及總統(tǒng)顧問J. Ehrlichman甚至因此入獄。
《華盛頓郵報》管理層給泄密者一個代號“深喉”(Deep Throat)。“深喉”的真正身份一直諱莫如深,是美國政壇和新聞界最大的謎團,三十多年后,兩位記者終于證實,“深喉”的真正身份就是聯(lián)邦調查局前副局長W. Felt。
時間往往證明政府的過慮。揭密和報道,對國家安全影響微乎其微,國家機密往往只是官員的遮丑布,掩飾其決策及行為失當,甚至貪污舞弊。如果沒有一些大無畏的員工,基于公益而揭發(fā)劣行,內幕將永遠無法曝光,社會將欠缺健康的討論,劣行到今天仍有可能還是積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