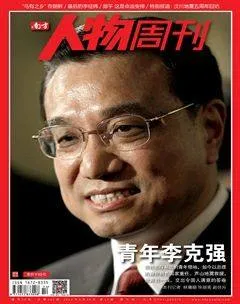仰起的臉和傲氣的眼
十八九歲時有段時間,沒上學也沒工作,留在家里每天讀書寫作,過著“零負擔”的日子。
白天家里沒人,父親出門上班,母親出外打牌,黃昏來臨前,家中客廳變成我的“書房”,臥躺沙發,翹起雙腿,愛翻什么書翻什么書,看累了便不知不覺間睡去。有時拿起望遠鏡偷窺對街住戶,隔窗看女孩子換衣或洗浴:形而上與形而下合為一體,是生命中最快樂的歲月。
睡覺難免做夢,夢中常現各式人物。我是個多夢的孩子,小時候經常夢游,跟不知名的人打麻雀、下跳橫(注:跳棋),啥事情都做過。到了青春期,夢中場景更為多樣,能說不能說的都有,但已沒有夢游了,只有腦海影像而沒有肢體動作,省下不少力氣。
那時候迷上臺灣作家的書,故常入夢,作家們現身夢里跟我談笑論事,夢過白先勇王文興李歐梵林文月,也夢過朱天文朱天心以及張大春。不太記得跟誰做過什么了,只見過夢中的隱約臉容及歡喜心情,如粉絲見偶像,不,不是“如”,真的是粉絲見到了偶像,影像是假的,強烈的感覺卻千真萬確。
a17ef83561cb27448d94216ceaddfe32bb6dfa960b30f980175c075667729f6b還有一張臉,是張愛玲的。那仰起的臉、傲氣的眼、淺淺的笑,仍然記得。或因當時看過她的照片所以夢見,日后也常見到相同的照片,故把照片和夢中人合而為一。
閱讀張愛玲的起點是《心經》。在灣仔的藝術中心看過榮念曾改編的舞臺劇,沒有劇情,只是照例非常榮念曾式的有一群人在舞臺上緩慢地從左邊走到右邊,再從右邊走回左邊。有音樂,有投影,沒有太多對白,卻有浪漫而哀傷的力量。離場后我緩慢地走回家,平日很短的一段路,忽然覺得好長好長。
看完《心經》,理所當然往《半生緣》《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探索過去,從此在張小姐的文字花園里千轉百蕩,不肯走出,并由文字迷上面容,由現實迷到夢境,好多回于午睡的恍惚里見到她。她朝我笑,我很緊張,每回都很緊張,然后通常醒轉過來。再看對街住戶,再誘人的胴體也已變成庸脂俗粉,不屑一顧。
那時候買的張愛玲的書多年以來一直在我身邊,加上后來的,家里書架有了一個“張愛玲專柜”。她寫的、寫她的,都有。10年前在香港的一趟飯局遇見幾位臺灣來客,說正在籌備張愛玲電視劇,我一時慷慨,把幾本難得的參考材料借給他們,對方答應要還,過了兩三年卻未見消息。我忍不住厚著臉皮托臺灣朋友追討,終于討回部分,心始釋然,盡管并未全部釋然。此乃老子生平首次亦是惟一一次把書借出去了卻仍主動索還并且是隔山越海地索還,只因跟張愛玲有關,不可失、不應失。
曾有一段日子我在地理雜志擔任記者,專駐東南亞,在泰國寮國緬甸越南等國家間游走,飛機于我如巴士,并且常要坐在候機樓內作漫長等待。隨身行李必有一本張愛玲小說集。耐看,不必擔心看不下去,不必擔心很快看完,隨手翻開一頁都可讀之再讀,如見熟悉的朋友,如有朋友作伴,心情頓然寧靜沉著,或可用舒服二字形容。像游走得累了,回到家里、見到親人,最強烈的感受總是舒服。
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說某回在旅途中遇見女子,她約我晚上見面,我心動了,卻沒去,夜里獨躺在酒店床上,不無后悔與遺憾。那是不可救藥的濫情與浪漫,卻又是惋惜于某種技藝之浪費,如同《紅玫瑰與白玫瑰》里那位嬌蕊,她與振保坐在陽臺,喝茶、調情——
嬌蕊道:“說真的,你把你從前的事講點我聽聽。”振保道:“什么事?”嬌蕊把一條腿橫掃過去,踢得他差一點潑翻手中的茶,她笑道:“裝佯!我都知道了。”振保道:“知道了還問?倒是你把你的事說點給我聽罷。”嬌蕊道:“我么?”她偏著頭,把下頦在肩膀上挨來挨去,好一會,低低地道:“我的一生,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了。”

半晌,振保催道:“那么,你說呀。”嬌蕊卻又不作聲,定睛思索。振保道:“你跟士洪是怎樣認識的?”嬌蕊道:“也很平常。學生會在倫敦開會,我是代表,他也是代表。”振保道:“你是在倫敦大學?”嬌蕊道:“我家里送我到英國讀書,無非是為了嫁人,好挑個好的。去的時候年紀小著呢,根本也不想結婚,不過借著找人的名義在外面玩。玩了幾年,名聲漸漸不大好了,這才手忙腳亂地抓了個士洪。”
振保踢了她椅子一下:“你還沒玩夠?”嬌蕊道:“并不是夠不夠的問題。一個人,學會了一樣本事,總舍不得放著不用。”
我于惘惘遺憾之中睡去。但那夜出現在夢中的不是張愛玲,而是一位遠在花蓮的臺灣女子。